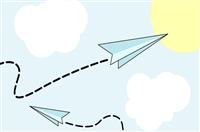“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是陶渊明《咏荆柯》中的最后两句,也可以说是两千年来人们读完荆柯故事(包括《战国策》《史记》《淮南子》中关于荆柯的种种记载)后的共同感受。古今游侠刺客,可谓众矣,而人们对荆柯这个不成功者却情有独钟,谁说中国人只以成败论英雄呢?秦汉之间就出现了两位古今传颂不衰的失败的英雄,一是项羽,一是荆柯。不难理解,两人获得千古同情有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反对秦朝的。短暂的秦朝在历史上不是“大一统”的象征,而是暴政的象征。
平心而论,如果拿秦王赢政(后来的秦始皇)与历代皇帝相比,并非属于下下,然而他所受的批评与否定却远远超过比他更为暴虐凶残的皇帝和与他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不成材的腐败皇帝。这也许是不公平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赢政目标大,许多具有正面价值或负面价值的事,在历史上,他都是始作俑者。具有正面价值的,多离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十分遥远。如统一天下,对于秦始皇本人来说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快事;而平民百姓的感受未必如此。诸侯之间消除了“热战”,人民可以不必死于战乱了,这是好事!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无尽无休的摇役、兵役,多如牛毛的苛细的律令,繁重的剥削与沉重的压迫。平民所遭受的苦难未必就小于诸侯之间的战争。如果天下分裂,诸侯对峙,百姓还可以用逃亡来躲避。可是当秦统一之后,“君臣之谊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们只有忍受,无法再像春秋以前那样“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诗经•硕鼠》。另外,战国七雄交锋时,有可能统一中国的有秦、齐、楚三国。齐、楚两国的经济文化皆比秦国发达(近年有人著文谈论如果齐或楚统一中国,中国发展走向的问题,其结论是两者皆比秦统一为佳。)秦统一后不仅不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反而消除百家文化的影响,焚书坑儒灭绝百家之言,以吏为师,只把文化限于耕、战二途。因此,这种统一,无论是从当时平民百姓的感受,还是从历史发展来看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进步意义,不宜估计过高。
至于那些负面意义,则大多与平民百姓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例如秦统一中国后立即上马的四大工程(长城、驰道、骊山墓、阿房宫)所动用的劳动力有300万之众,如果再加上零散的徭役与谪戍人员,总共在450万以上。这样大规模地征发百姓服役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2100万,这种超级规模的征发劳力对人民意味着什么,我想不必由动辄以进步或反动划线来评论历史人物的史学家来证明,何况在征发摇役的过程中伴随着残酷虐待与严刑峻法。用汉代政论家晃错的话来说,被征的役夫是“有万死之害,而亡株两之报”(《汉书•晃错传》)。这使得平民百姓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陈涉就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既然怎么都是死,还不如武装起义,或许还会有条生路。天下的役夫们都抱着这种想法,那么秦王朝的垮台不是指日可待吗?
最为万世唾骂的是焚书坑儒。我们且不说焚民间书,其目的是愚化百姓,与民为仇,也不说杀一无辜,也属残暴,就从秦始皇首开风气的文化专制的示范效应来看也是极其恶劣的。后世的专制帝王都在明里暗里学习秦始皇的一套。2000年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与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示范作用不是毫无关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战国时期六国士人多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它统一中国后,马上就向被统治者展示了其锯齿利爪。最初还只是对“贫人贱民”,继而扩大到“富人吏家”,最终连“宗室大臣”也不能幸免。真如汉政论家贾谊所形容的“执敲扑以鞭答天下”,公然与天下为敌。始皇曾幻想千秋万世永传其帝业,结果是二世而亡,从而显示出被压迫者的力量、正义的力量。
上述就是“刺客”荆柯悲壮行为的背景。荆柯行为的意义早已超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范畴,更不在于“尽反诸侯之侵地”;而在于抗暴,在于为伸张正义去赴汤蹈火。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吹始皇为“千古一帝”,是法家代表人物,是促进历史前进的英雄。那么,荆柯只能是反派角色了,所以,那时把(易水歌)改为“小丑一去兮不复还”,可惜未能如样板戏唱得那么红火。历史虽说是人写的,但公道自在人心。2000年来的良知不是一下子就能涂得漆黑的。一个孟姜女的传说(当时也考证出是为反动分子所编造)使秦始皇的“伟大”减色;同样,一个荆柯的故事也使秦王失去许多光辉。
当然,感情的向背与理性的评价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南辕北辙),也没有人为拔高荆柯的必要,行刺暗杀从来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燕太子丹想通过两个刺客劫持秦王,与其订立契约,使其放弃侵略计划更是极其可笑的。田光、樊於期、荆柯、高渐离等人前后赴死的献身精神,其中虽有对暴政的痛恨,但主要的还是出于那曾长期存在而又即将消失的武士精神。荆柯等人都是“士”。顾领刚先生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樱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身份,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史林杂识初编》)他们自幼在“库、序、学、扩之中受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他们还要“养勇”(见《孟子》)以尽武士的职责、维护武士尊严。社会的尊重、人们的仰望使武士养成了尊礼重信的阶级道德。春秋中期以后,士阶层虽然逐渐分为文士、武士(武士流落民间者则为侠),但世世代代所养成的行为规范尚未完全沦丧。读西方与日本史籍,对中世纪骑士、日本的武士,常因一言不和仗剑相斗,或为了些许小事拔刀自裁,感到不可理解。其实,他们在主观上都是在维护武士的尊严与荣誉,否则生不如死。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这类记载也很多,只是我们没有重视或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罢了。如晏婴的“二桃杀三士”,过去读者嘲笑“三士”的愚蠢,其实“三士”之自杀是由于他们感到在分桃问题上无论是争还是让,皆有损于武士的荣誉。《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所写的刺客、游侠,《信陵君列传》中的侯威等都表现出轻生死、重然诺的侠士风范。无论是侯赢的“临风刻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还是荆柯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都给后世为正义而奋斗的人们极大的鼓舞,而在侯底、荆柯们看来,这是极平常的,他们只是在履行传统的武士道德规范罢了。
荆柯的故事之所以影响深远,还在于《战国策》与《史记》对其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作者运用白描、供托、对比等多种手法,展示荆柯性格的各个侧面,从而使一位深谋远虑、善于克制、明大义、重然诺的古代侠士栩栩如生地立在读者面前。文中重点描写了易水送别与秦庭行刺两个场景。行刺是故事的高潮,作者通过对荆柯一系列行为动作与表情神态的描写(以此与秦王的狼狈不堪作对比)完成其形象的塑造。然而在文学史上流传更为广泛的却是易水送别一场。送别者“白衣冠”、高渐离击筑、荆柯慷慨悲歌所造成的悲剧性氛围深深地印在后世读者的心中,因此,人们便认定“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人们也把易水送别视为古今最悲壮的离别,辛弃疾在一首《贺新郎》中曾写道:“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这就是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