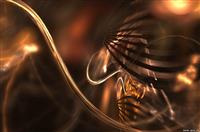
——一种试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解释视角
吉登斯社会时空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地位,既是其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其社会理论中的基本方法论。吉登斯的社会时空思想是涵盖于其“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视域之下的。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主要体现在其“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系列著作,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一卷 权力、财富与国家)》这部书中。吉登斯表明,“我称这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但我的意图并不是全盘的批判与解构,与马克思不同,我想为另一种历史解释模式提供某些要素。”[1]3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源于对这样一个主题的关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产生的。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用通过生产力的进步性扩展的方式加以理解,但这是错误的观念,而且已到了最终放弃它的时候。”[1]1因为这种观点带有历史进化论的色彩。他认为经典的社会历史理论,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水平了,面对各种新兴社会理论提供的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历史解释模式需要被超越,这正是吉登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而社会时空思想正是他独辟蹊径分析社会结构与人的活动、乃至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
吉登斯认为,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说明,必须关注“社会结构”和“人的行动”两类现象。对这两类现象的不同侧重,构成了社会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强结构而弱行动”,把社会结构视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客观力量,强调社会结构对人的行动的制约作用,将社会结构的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另一种主张“强行动而弱结构”,把社会结构视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产物,强调人类社会行为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性,把人类行为研究置于社会学研究的首要位置。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因而具有“强结构而弱行动”的倾向。对这两种倾向他都不赞同,并提出“结构二重性”理论加以调和。所谓“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结构既是人类行动的结果,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人类在行动过程中既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为条件而展开,但同时其行动的结果又改变着社会结构,并且,社会结构并非如建筑物一般是一种实体性结构,而只是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特征”〔2〕40。社会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这种结构性特征与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作出说明,而社会时空正是说明两者间关系的关键所在。为此,吉登斯清理了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有关时空问题的主要观点,并在批判和吸收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时空思想。
吉登斯反对把时间看成是社会活动的外部因素,认为“时间其实是社会活动的构成形式”[3]157,是社会活动的一个维度,它与社会活动本身的特定性质密切相联;吉登斯也反对把社会时间看成是一个有方向的、不可逆的线性序列,他认为在由严格的时间规则支配的文化中,社会活动是可重复的,时间也是可逆的。吉登斯把社会生活的时间性归结为三种形式,即日常生活时段、个体寿命期限和制度时段[3]158。这三个时间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制度时段与行动的“例行化”有关,即社会互动在时间的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固定行为模式,这种固定行为模式超越了个体寿命期限,具有了结构性特征,进而构建起社会系统的结构模式。吉登斯也区分了社会空间的三个方面,分别是形体的空间性、共同在场和区域化。三者都与行动在物理空间中定位有关,而区域化涉及空间的分化。区域化的社会活动有着一定的边界,当行动者进入某一边界时,他的行动也不可避免的带有相应的情境性。从吉登斯对时空的划分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时空的社会意义实质上是时空环境与行动的关系:时空环境与行动本身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前者既是后者的结果,又是后者的条件。
在社会时空中,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为社会的结构化奠定了基础。这种结构化的具体体现就是社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吉登斯划分了三种社会形态,即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与阶级社会。一个社会在时空中展开活动的总体能力,在吉登斯看来就是“时空伸延(time-distanciation)”水平,即社会系统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扩展程度。部落社会的时空伸延水平最低,社会行动局限在“共现在场”条件下,其支配资源和存储资源的能力都比较低,权威性资源中的传统、宗教和亲族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要素。阶级社会的时空伸延水平最高,社会活动可以脱离当时当地而在更广阔的社会时空中展开,其支配资源和存储资源的能力都是最高的,配置性资源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阶级分化社会的时空伸延水平则居于这两种社会之间。
三、“时空分离”与“脱域”——吉登斯对现代性扩张的探索
吉登斯之所以要探寻一种超越经典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解释模式,最终目的就是想要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要能够说明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发展。吉登斯认为当前人类正处在现代性高度扩张的时代。现代性为何会激进扩张?或者说现代性扩张的动力在哪里?这是社会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与包含在时—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4]14在前现代社会,时间需要利用空间(地点)来表达。人们往往利用地方性的自然特征来标记时间。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时钟的发明使标准化时间成为可能。通过标准化时间,社会活动可以穿越共同在场,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得以安排。在晚期现代性社会,随着时间规则的国际标准化,时间与地点的分离达到了最高水平。时间与地点的分离使得全球范围的协作成为可能,也使得全球范围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要素具有了在时空中伸延的能力,共同在场的行动者所进行的活动往往由远离当地的社会因素所决定。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条件下的时空分离正是现代性激进扩张的动力源之一,因为:第一,时空分离为社会关系的“脱域”创造了条件。第二,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提供了运行机制。第三,时空的分离和重组使现代社会具有了“历史性”特征。
吉登斯对社会时空的关注为研究人类社会的规律,特别是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不过,吉登斯试图通过从社会时空的视角入手,找到一种可以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这种努力是不会成功的。社会时空是人类活动的展开方式,但是形式不能代替内容,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依然要落到人类社会的核心内容——人的活动上来,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活动的根本形式就是劳动实践。吉登斯所谓的“权力”、支配和存储资源的能力从本质上体现的还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人类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吉登斯对社会形态类型的划分并没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大社会形态”的划分,我们可以找到两种划分的某种对应关系,而且在划分标准方面,吉登斯复杂的划分标准还是可以还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另外,在说明社会变迁方面,吉登斯提出的晦涩的“时空伸延”概念,实际上反映的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决定着一个社会在时空中展开活动范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吉登斯的这种“超越”努力并没有得到他的预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