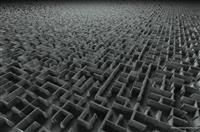一、往事和公共记忆
公共记忆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重视,可以从2008年《南方周末》的书籍评选看出一些端倪。2008年初,《南方周末》提名的5部非虚构类的“年度致敬”著作,全都与历史记忆有关。这5部著作分别是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张贤亮、杨宪益、徐友渔等合著的《亲历历史》、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和我本人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这5部书所关心的都可以说是一种与现在相关的过去或历史,也就是“记忆”。哲学家柏格森说,现实是在与过去相区分、相联系中才显现出来的,我们感知的现实每时每刻都铭刻着公共记忆。读者关心记忆问题,这是他们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记忆的原则是“真实”,在记忆不自由的环境下,记忆的真实便成为一种记忆者的道德行为。对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评选者缪哲是这样说的:“唐代的刘知几,对修史的人有三个要求:曰‘才’,曰‘学’,曰‘识’。清代的章学诚又不满其义,于三者外,又标‘史德”。所谓‘史德”,按章的解释,就是作者的‘心术’。心术的斜正,总不是无缘而发的。如生活于当今,却称桀纣好,道尧舜非,那一定是傻子。图什么?但于杀士钳口之际,竟说‘焚书事业费商量’,‘文字狱有利于稳定’,就不是傻子的所为,而是心术的倚侧。……从这角度说,《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与《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就是两部很有史德的书。”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写作说真话难,常常不得不说假话,又何必称赞历史写作者的“史德”呢?
胡文辉读陈寅恪的诗,则是以揭示陈寅恪的隐秘写作为目的。列奥·施特劳斯说,在危险的思想环境中,写作者会把要说的意思隐蔽起来,于是,便有了隐秘的写作。破解过去的隐秘写作,必须重新记忆这一写作当时的现实环境。1980年代初,余英时在海外发表文章,认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里存在着一套“暗码”系统(即借助诗的古典与今典,表达诗人的心曲),此论一出,堪称石破天惊。不过,正如有论者指出,余英时的解说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他解读的只是陈寅恪晚年的部分诗作。胡文辉的这部大著,“解陈诗一句不遗,旁征之博,考订之精,发覆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读后方知陈诗率多‘当代史论’,令人大开眼界”。
许多人关心陈寅恪,看重他的“晚年心境”。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当作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痛苦灵魂之声。记忆不断在提醒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多么悲惨地丧失了独立的知识人格。如梁治平所说:“历史上士大夫阶级中的个人还比较容易保持住一己之独立人格的话,那么在现代,随着社会格局的变换和此社会价值解释权的移转,知识阶级中的个人要保持其独立品格则是愈来愈困难了。为要求得绝对的思想一致,政治冠冕堂皇地干预乃至统制学术,其结果,不仅是造成了学术的荒漠,而且产生出普遍的虚伪和堕落。”
过去与现在之间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联系方式,但最根本的联系有两种。一种是从过去汲取智慧、启发和美好、纯真的理想,如人们之对待古希腊雅典的公共生活、启蒙主义时期的人文理想、美国建国时期的共和政治理念,等等。另一种是从过去汲取灾祸教训,以避免再发生过去的那些暴行、残害和人寰悲剧,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国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
第一种记忆和第二种记忆有时可以混合在一起,如美国的蓄奴与反蓄奴运动历史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斯皮尔勃格导演的《断锁怒潮》(Amistad)所运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混合记忆,既有美国黑暗的蓄奴历史,又有高尚的反蓄奴历史人物和正义行动。特别有意思的是,反蓄奴的正义行动(亚当斯为黑奴辩护)正是以高尚记忆(美国的《独立宣言》)来获得胜利的。
《断锁怒潮》的往事大致是这样的,1839年夏,关着53名非洲黑人的西班牙运奴船“阿米斯塔德号”(友谊号)行驶到距古巴海岸不远处,遇上狂风暴雨。黑奴首领辛凯带头造反,以武力控制了全船。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返回家园。“阿米斯塔德号”在美洲东海岸漂流两个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海岸被美国海军拦截。53名非洲人以谋杀船员的罪名被起诉。废奴运动的积极分子请来青年律师罗杰·鲍德温,证明这些黑人来自非洲。根据当时走私黑奴为非法行为的美国法律,这些黑人在法院获判无罪。
这一案件虽然在地方法院获判无罪,但因牵涉美国南北方的分裂与对立,当时的美国总统范伯伦(MartinVanBuren,1837-1841年任美国总统)为了讨好南方保守派势力,避免引发美国内战,直接干预此案审理,由司法部出面将此案送到最高法院进行上诉,而9名陪审团成员中7名为大奴隶主,判决结果预料会对黑奴不利。此时,前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亲自出马,以75岁高龄之弱体,免费为这些黑人担任义务辩护律师。在法庭,他陈述自由、平等、的美国立国之本,为本已处于劣势的黑奴们赢到了与所有白人一样具有的人类天赋权利——自由!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许都能记得亚当斯在法庭上回忆和陈述美国建国理念的场面。这个电影故事是“文学性”的,因为它有相当大的虚构成分。亚当斯1841年2月24和3月1日为黑人辩护,发言长达8个半小时,这个辩护词已经成为“维权”辩护的经典。在电影中,亚当斯的辩护只有几分钟,他提醒所有在场的人,美国的《独立宣言》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快结束辩护的时候,只见亚当斯慢慢走过法庭旁侧陈放的一排白色大理石雕像,每走过一尊雕像便说出一个名字:詹姆士·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乔治·华盛顿。他最后停在一尊雕像前,说,约翰·亚当斯,那就是他的父亲。亚当斯对这些雕像自言自语道:“我们已经很久不愿意向你们请求指导,我们是害怕告诉自己,我们并不只是存在于今天,我们是害怕,回顾过去会让我们显得软弱,但是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事情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终于知道,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
亚当斯在法庭上唤起人们对美国立国精神的公共记忆,斯皮尔勃格又在电影中以亚当斯1841年的辩护唤起今天美国观众对美国国精神、废奴运动、道德理想以及社会公正的公共记忆。影片中的亚当斯看似赢弱,与他毫不妥协的反蓄奴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每一个字都透出果断和坚定:“如果这会导致南北战争,那就开战好了,这将会是美国革命战争的最后一役。”
亚当斯维护的不仅是黑奴的权利,而且也是真正的美国精神。林肯在南北战争后发表的《葛底斯堡演说》,同样也是用记忆美国革命的开国理念开篇:“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她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来平等的信条。”林肯引述的同样也是美国《独立宣告》的伟大理想。亚当斯曾是美国第6任总统,他认识美国“建国之父”辈的前5位总统(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门罗),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1847-1848),他担任参议员的时候,林肯正担任众议员,所以他成为美国建国之父们和林肯之间的“美国精神”象征桥梁。《断锁怒潮》用亚当斯保存美国精神历史和道德记忆的目的非常明显,诚如导演斯皮尔伯格自己所说:“这部影片将永远跟随着我们…我觉得我拍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故事,每个国家每个种族都应该知道这个故事。”
二、公共记忆在中国
在自由、平等和人性价值的历史资源上,美国人是幸运的,他们建国时期的文献中充满了至今仍在启发和鼓舞美国人的共和自由精神。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缺少的就是这样丰沛的共和理想资源。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宪政,该从哪个历史时刻去获得一代又一代能够反复记忆的价值理想和目标呢?当然,这样的历史资源也并非完全没有。看过《走向共和》的人都会记得这个连续剧的最后一集。在这一集中,孙中山用中山装的三个袖扣和五个口袋,解说他的共和三民主义和权力制衡的理想。可惜,正是这一集,在《走向共和》重播时被删除掉了。
也就是这个例子,它告诉我们,在当今的中国,记忆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哪些是可以记忆的?哪些不可以记忆?以什么方式记忆?在什么限度中记忆?都不在记忆者个人的掌控之中。在种种现实限制下,还是有人会想方设法坚持真实的回忆,将回忆用文字或其它形式记录和保存下来。他们的写作行为于是成为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公共行为,那便是“见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卡耐提(EliasCanetti)写过一本书,叫《卡夫卡的另一个审判》(Kafka"sOtherTrial),在书中,他谈到自己阅读卡夫卡书信时的体会,“我觉得这些书信比我在过去许多年中读过的任何书都令人深思,扣人心弦。卡夫卡的书信与卡夫卡本人从中摄取精神营养的回忆录、自传和书信集属于同一性质。他生前就……反复地阅读克莱斯特(HeinrichvonKleist,1777-1811,德国小说家、剧作家)、福楼拜(1821-1880,法国小说家)和赫伯尔(ChristianFriedrichHebbel,1813-1863,诗人、剧作家)的书信。如果称卡夫卡的书信为‘文献’,那就是太低估了它们的价值。”卡耐提认为,应该把这些书信称作为“生命见证”(life-testimony)才对。评论家费尔曼(ShoshanaFelman)解释说,“生命见证”不只是对某个人个人生活的见证,而且是对一个更大群体生命的见证。陈寅恪就是这样一个对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见证,许多“‘右派’文学”中知识分子个体遭遇也都是这种性质的见证。
在讨论“‘右派’文学”时,黄勇就曾特别提到《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这本书为一个更大的群体生命作见证的公共作用:“作为一个极富天赋与声誉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束星北在1949年之后的新环境中不仅鲜有成绩,更是历尽坎坷磨难。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正当盛年的束星北失去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尊严,失去了从事物理研究和教学的权利。《束星北档案》一书,不仅记述束星北后半生的经历,更折射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束星北等科学家(包括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不能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环境和形势,与社会、时代的矛盾渐次累进的过程”。这也是《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自己要强调的“右派”记忆公共目的:“这是一个人,一个优秀的人不断被阉割扭曲为另类的历史”,“是一个英雄‘落败’的历程,也是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悲剧”,这样一段“不知被发掘扬筛了多少遍”的历史,“束星北档案,让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见黄勇:《“右派”文学中的自然科学家》,《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月号)
束星北所经历的苦难不是由束星北自己叙述的,而是由作家刘海军叙述的。这样的作品在“右派”文学中还有许多别的例子,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告知夹边沟》,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赵旭的《风雪夹边沟》、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等等。我们把这一类的作品该称作什么呢?黄勇把它们称作为“‘右派’文学”,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它们所叙述的故事,原始材料可能很零碎,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叙述结构,作家对那些零碎的原始材料进行选择、安排,为之设计一个它们原本所缺乏的完整传记、记实小说或其它叙述形式,因而成为一种“文学”。它们的共同特征也许可以说是尽量真实地保留过去生活原有的事件、人物或环境细节,尽量避免虚构。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样的写作需要写作者具有很大的道德勇气、社会正义感以及独立思想和价值判断的能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作品具有的只是一种间接而非直接的真实性,是一种间接而不是直接意义上的见证。
直接或真正的见证,如犹太哲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Margalit)所说,应当是苦难亲历者自己的见证。这种可能的见证者在中国人数极多,但确有的见证写作却相当少见。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真正的见证往往表现出记忆零碎、不清、遭压抑等原始形态特征,很难有机会以写作的形式出现在“文字”或“文学”的传媒空间中。第二,它们往往形成对迫害性权力的直接控诉,由于没有“文学创作”这道审美挡箭牌,所以更容易遭到封杀。第三,即便个人的遭遇被一一叙述出来,
公众也会觉得大同小异,未必会对此有兴趣,不容易有广泛的关注。这三个原因中,第一个涉及记忆的内容本身,第二个涉及记忆的政治环境,第三个涉及记忆者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
在“直接”的右派见证中,我们也许可以用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为例子。这个文集中讲述的是高尔泰自己如何变成“右派”,以及他在夹边沟劳改营的经历。高尔泰的这部书稿,写了十多年,朋友们为之出版也奔波了四、五年。出版的艰辛历经艰辛本身便说明了中国“反右”记忆的环境。至于哪些文字有删改,删改到什么程度,便不是直接可以从现有的文字中看出来的了。
就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寻找家园》,如评论者一平先生说的,“这部书可以传予后人,固然它还有所散简,但在中国未来的文明中,其必是一束永久的记忆--不仅仅是见证,也是焚毁、苦难中人性之光。”高尔泰的记忆是对一种死亡生活状态的见证,“高先生的文字即是毁灭后废墟上斑斑遗迹。我似乎看到那些文字由夹边沟连连骨骸和灰烬间冉冉升起、汇集,如同铭刻于夜空的碑文。酒泉,神往之名,中国古远诗情;可怎么就尸横恶臭呢?而仅仅十年,那几十万苍生白骨、冤魂鬼魅便在无尽风沙中掩埋得了无痕迹。历史不残酷吗?残酷得使残酷没有痕迹。”
《寻找家园》这个题目就蕴含着作者做见证的目的和用意:寻找人的家园。还在劳改的时候,高尔泰就曾在小纸片上用芝麻大的字写道:“苦难在我的心灵中践踏出一片荒凉的地域,我心灵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枯萎了,死了,再也唤不起我的一点激情。由于没有这些东西,我早已感到自己不再有灵魂和生命,不再是一个活人。但是曾几何时,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竟奇迹般地长出了一些小小的新苗。”对高尔泰来说,见证是一种连接和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写作:“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他的见证不只是为他自己,也是为那些未能走出夹边沟,未能迈过1976年那道历史门槛的难友:“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赤裸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
直接见证者和主张直接见证的人们容易对间接见证和它的“虚构”成分持否定的态度。结果直接见证被当成了非直接见证“虚构性”的对立面。例如,一平先生在赞美高尔泰真实见证的同时,就对小说中的文革记忆表示失望:“高先生……这一代人历经磨难,生命七零八落。如此一生,何谈完整?读过不少文革小说,每每失望。艺术有其局限。如果小说是虚构,那么真实何在?将奥斯维辛纳入虚构,即失去其意义。真实只有意义相对不足时,才需要虚构。如果它沉重得将你坠入地狱,它就是你的生命,你必须穿透才能自救。重要的是,它是你亲身所历。虚构、非虚构,是一个界线。”其实,纪实见证和小说表现都可以具有真实性,只有它们是不实和谎言历史的对立面。
直接见证者与间接见证之间的关联,包括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是见证写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西方的犹太人大屠杀写作研究中也屡屡出现。例如,1978年美国三大商业电视台之一的NBC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大屠杀》,收视观众达1亿2千万,是美国人口的一半。NBC在1979年重播此剧后估计,在美国和欧洲的观众有2亿2千万之多。就在第一次放映三星期后,卡特总统宣布成立一个准备在美国建立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的委员会。70年代后期在德国正在兴起一阵“希特勒热”,1979年初《大屠杀》在德国播放后,“希特勒热”消失在公众舆论的谴责之下。从此,在公众语言中,“最终解决”这样的中性词被“大屠杀”这个带有道德谴责的词取代了。[注9]但是,身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的见证文学作家威塞尔(ElieWiesel)就曾猛烈批评这个连续剧,称它“把一个人本体事件(ontologicalevent)变成了一部肥皂剧,”“全然虚构不实,”因为“大屠杀是超越历史的,大屠杀既不可能解释,也不可以视觉化。”蓝兹曼(ClaudeLanzman)对电影《辛格勒的名单》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说,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周围有一道火墙,“虚构就是侵范性的越界。”他坚持,“有的事情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来扮演的。”这种批评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课题。它涉及一系列有关灾难“经验”和“再现”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在“不可言说”和“必须言说”,在“难以再现”和“应该再现”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把直接见证与间接见证对立起来。直接见证与间接见证都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act),而不只是一种陈述。直接见证也好,间接见证也罢,都属于一种苦难文学,它们都是象牙塔文学、风花雪月文学、闲情逸致文学、宫廷故事文学、情色文学、只有风景没有人文景观的旅游文学、紧跟主旋律的歌功颂德文学的对立面。作为“言语行为”,见证是一种承诺,一种决心,一种誓言。在这一点上,直接见证和间接见证的公共行为意义是相同的。
直接见证和间接见证都坚持把真实的人和事当作历史的证物保存下来。当一个社会的真实出现了问题时,才特别需要见证。见证是在真实被隐蔽、真相被扭曲、真情被歪曲时才成为必不可少的。过去的苦难发生了,却一直因为真实的蒙蔽而迟迟不能申张。这时候,见证便有了分善恶、辨黑白的公共伦理作用。孤独无助的人们往往期待因果报应帮助自己申张他们遭受到的非正义伤害。这种孤独的等待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定势,演化为一种稳定的被动期盼。见证不接受这样一种心理定势和被动期盼。见证是积极的、反抗的,它拒绝孤独,也拒绝顺从。见证不是消极地等待自然发生的德报恩酬、怨释仇雪;而是积极地争取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见证不是私人心理上的一架情感天平,而是公共认知的一个道德法庭。在这个法庭上,不仅苦难经历者作见证,而且整个正义社会也都是列席的证人,见证者以全社会和全体人类的名义呼唤正义,为的是不让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灾害再次发生到任何别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