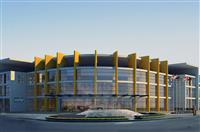
不管是作为小说家,还是赛车手,甚至是他时尚的个人形象,韩寒仿佛都更加适合“小资”消费。但他本人绝不是一个小资,他与小资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与小资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系统。小资看世界,事先准备一本书或几本书,一部电影或几部电影,他们需要在别人的引导之下,才能够看见和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需要抱一块石头才能沉到水里。
韩寒也读书也看碟,但是他的知识系统,不是朝向已有的符号体系,而是直接朝向这个世界,是他本人在这个世界上(裸奔)的观察而来。他拥有对于世界以及对于自身少有的直接性,那种无庇护也无遮拦的裸视,冲锋陷阵、盲打误撞,他的知识是他用他自己的血肉而换取。他将自己“试错”的点点滴滴,编织成了自己的意义系统,他要自己称呼这个世界,搬弄这个世界,这形成了他的小说。
当他独自一人站到地平线上,无以依靠,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力量,体验到了自己身上模糊而沉睡的多种潜能。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座有待开放的富矿。(也许我们每人如此,只是没有坚决意识得到。)独立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精力充沛。一个不受羁绊的人需要速度。赛车的速度也是他思想的速度;向远方的道路进军,也是向自己体内的极限进军。
当他立足于自身,扎根于自身,他的世界朝向四面八方而延展开来。海子二十年前的那句诗,到了他这里才获得了一个活生生的认证:“躺在大地上,朝向四面八方疯长”(大意)。他办杂志、写“时评”,他仿佛不知道自己的界限,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下自己的步伐。
不,他在摸索和扩大这种界限。所谓“时评”这种东西,应该比小说更加难写。小说的读者相对来说是固定的,而时评却要对完全不认识的人们说话,说的又是他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如何说得让人心服口服,如何在普遍失去尺度的前提下,描绘出理解一件事情的基本框架,这是一桩真正的挑战,如同在深渊中行走,从虚无中升起,体现了这个人的想象力。
朝向现世、追求完美、多才多艺、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潜能,就这些方面而言,韩寒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很像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不说达芬奇那些人,说说比如阿尔伯蒂(1404——1472)。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别人找不出他的缺点:走路、骑马和说话。他热爱音乐,喜欢饲养马匹,最顽劣的马在他胯下也会战栗。他的传记中历数了他的各种才能——骑马、写诗、作曲,绘画、演说,以及向各类工匠(包括补鞋匠)学来的本领,却忘记了他在建筑学方面的贡献。他敞开的心灵还表现为——当他有病时,不止一次因为看到美丽的景色而痊愈。
一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人,一个全方位生长和发展的人,在我们的环境中,是多么难得啊。这样的发展,同时希望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阻止他身上的这种势如破竹的进展,阻止由他代表的新的地平线的升起。因而,他从私人的完美,走向了一种公共精神——即使某些倒霉的事情还没有落到他身上,即使他看起来还是自由自在,但是某种东西阻止了他有可能与别人一道发展的天地,剥夺了他有可能与同胞一道享受的丰富空间,因而也阻止了他这个人弹跳的高度。这个被拿走的深度和广度,是他所不知道的,但他也许意识到了这种缺乏。
因而,他的慷慨,拥有一个个人的比例、个人的深度。同时,他的节制,又拥有一个广阔的视野——以他人同在。一般人的口头禅或许是“这是我的权利”,而韩寒或许会说:“我不需要一个主人”。一般人的座右铭或许是“这关我什么鸟事”,韩寒却力图表明,“一个自己的主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在一切状态中,屈从的奴隶状态是他最不能忍受的。
比较起rights(权利)的版本,韩寒是一个power(权力)的版本。当他体验到自身的力量(power),也希望这个世界能够体验到他的力量(power)。他的努力远非从这个世界拿走什么,而同时是给她带来什么,为她增添什么。
2010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