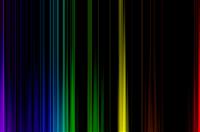
看过一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里没出现一头牛,起这个名字,有点不知其妙,大概寓意是那班学生如散养的牛一般,不受拘束,吊儿郎当,不学无术,野性十足。电影写的是音乐家克莱门特到了外号叫“塘低”的男子寄宿学校当教师,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改善现状,用音乐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最终这群孩子成人成才。这给从事教育的人很多有益的启示。
我曾是一个放牛娃。
历史倒转几十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我上不了。家里上学的孩子多,经济条件不允许,等到经济状况好转我才能去上学。那时候根本不问孩子是否到了上学年龄,可以七岁去上学,也可以十岁去上学,都随家长的意愿。我九岁了还上不了。我们村里很多孩子不去上学,也没有人过问。哥哥姐姐背着书包欢快上学去了,我只能搬个板凳坐在家门口,看着一群群小朋友蹦跳着向着学校方向进发。我托着下巴,翘起二郎腿,宽大的鞋子从脚脖子上滑落下来,好像蛇身从脚面上慢慢游过,我一下惊醒过来。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好像在嘲笑我的发呆。我拾起泥团砸向小鸟,小鸟叽叽喳喳从我头顶上空经过,一阵风儿飞走了。我使劲踹了树几脚,可树纹丝不动,真是“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跑到路上,那些上学的孩子们早没了身影,一条大路弯弯曲曲伸向东方(小学校就在东方)。
很多时候,我都这么呆呆地望着,我不知道上学是干什么的,可对我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家里终于找了件让我不再发呆的事,把生产队的小牛牵来让我去放。那时候还是大集体,田地是集体的,农用牲口是集体的,粮食是集体的,好像一切都是集体的,只是孩子是每个家庭的。放牛也没有工分,不发补助,纯粹是帮忙,留给生产队长好印象,积攒好名声。这牛还不能称一头,它是水牛的后裔,浑身的黄毛还没褪尽,牛角还没长齐整,半个月亮型。我不情愿地牵着小牛走到有草的田埂边,小牛可没我这么不情愿,一见到新鲜的草,伸出小舌头,卷起长草,一口衔住好多,一使劲,库擦一声,草尖全进了嘴里,小牛抬起头,吧嗒吧嗒咀嚼起来。这样反反复复,一顿饭工夫,草饱肚圆。小牛饮过水后,我把它栓到一棵树上,回家找吃的去了。牛吃草,它可以吃饱,我干啥?眼瞅着它狼吞虎咽,我肚子饥肠辘辘,我没得吃!牛越吃越得劲,我站在它旁边,越看,自己越没气力。我肚子饿,牛不知道,可我明白啊。后来,我破烂的口袋里装着些山芋干、花生。牛吃绿色植物,我吃绿色产品。我再也不感到饥饿了。
我与小牛相伴了一段时间,牛角长全了,身体也增高了,我可以骑在它身上了。只要我站在它面前,小牛就低下头,我双手抓紧它脖颈的毛,把脚放在它头上一抖,小牛就脖子一紧缩,头一抬,就把我送到牛脊梁背上,我就可以舒服地骑在它的身上。牛真是通人性又聪明的动物,教不了几回,它就条件反射般学会了。我骑在牛身上,一下子好像增高了很多,似乎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其实,农村除了庄稼,就是野草,有什么好看的景象?绿油油的一大片,没边没际。可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我信牛由缰,只要小牛不吃庄稼,上哪儿都随牛意。那时野草存活能力真强。不用浇水施肥,吃过的地方仿佛一夜之间,恢复了原状。我由此认识了很多野草野菜:车前草、蒲公英、苣荬菜、灰灰菜、马齿苋、猪毛菜、曼陀罗、刺儿菜、牛筋草、泥胡菜、马塘、稗子、小马泡等等。那时不知道这名字,只晓得它们的土名,字我写不出来。有的,牛喜欢吃,如牛筋草、马塘、灰灰菜、田旋花;有的,牛坚决不吃,如泥胡菜、刺儿菜,性苦;有的猪喜欢吃:马齿苋、猪毛菜;一看到小马泡(类似现在的小番茄,青色,我们叫它马皮瓜),我就会摘上几个,用手揉软它,使劲一捏,“啪”的一声,喷出里面的五脏六腑,能窜得老远,很刺激。那时农村的孩子就喜欢这么玩。
后来,我终于上学了。早晨上学很迟,八点去也不算迟,即便迟到了,老师也不批评。那时老师大部分是临代教师,大多善良,不怎么处理学生。我早晨一起床,就去放牛,牛吃饱了,再去上学。中午、下午放学,如果牛还饿着肚子,我书包一扔,骑上小牛,一溜烟就到了中心堆边,小牛如同放风的囚徒,饿了很久,大快朵颐。
要是到了放假的日子,我成天和小牛耗在一起。骑在小牛身上,缰绳一拉,一声唿哨,出发了。等到了一个大人看不到的地方,有草有水就行。我就把牛绳绕在牛角上别好,任它逍遥了。我躺在一棵大树下,要么睡大觉,要么自娱自乐。在路上挖个大点的坑,上面用树枝支撑着,撒上土掩盖成原状,自己躲在树后,看到有人一脚踩进去,吓得一惊一跳,我有说不出快乐,超高的成就感。有时天气热了,我就泡在水里,狗刨、仰泳、蝶泳,都会。那时一个人也不怕溺水,孩子多的家庭,少一个,父母难过一段时间后,也就恢复正常了。我看到过不少孩子溺水而亡,父母哭的死去活来。等不了多久,生活又恢复往常的样子。死去的可惜,活下来的珍惜,就这么简单。穷苦日子里,生命算什么?活着就是幸福,活着就是本钱。
小牛成了我生活中的玩伴,我一闲下来,就去用水刷刷它的身子,好让它干净地驮着我。如果我逮到一条黄鳝,我会把它塞到牛嘴里,小牛很拒绝,我就把黄鳝从它鼻孔里塞进去,并把它头高高抬起,这样黄鳝就进了肚子里,那时我就是这么给牛吃无鳞动物的。其实,牛是食草动物,根本不吃荤。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小牛“吃”几次过后,也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我就这么放牛。过了几年,我上了初中。突然分田到户了。集体的东西都要分到各家各户。那些不好分的就卖掉。很不幸,我的已经长大的“小牛”,不好分,几家合养一头牛,矛盾重重,很不现实,只有卖掉。
一天放学回来,听父亲说,我的“小牛”被卖了,卖到了较远的一户人家,他家从来没养过牛。我一听,陡然一惊。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牛”了?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牛角,长长的能驱赶蚊蝇的耳朵,光滑的身子,阔阔的脊梁背,甩来甩去的尾巴……我心里像翻了五味瓶。
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听父亲讲,牛到了那家不久就生病了,不吃不喝,那主人害怕折了本,就把牛卖给了牛贩子,没几日,牛就被杀了。听到此,我仿佛掉进了冰窟,眼泪在眼睛里转。如果说没有感情,那不可能。相伴了几年,即便是猫、狗离开也会心疼,何况是那么一头身材庞大,颇通人性的水牛!它长大后是犁地的一把好手。套上架辕,拖起铁铧犁,鞭儿一甩,得儿驾,快速前进。它从不偷懒,也不来脾气,“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
我的“小牛”从这个世上消失了,我再也看不到它,它再也见不到我。我弄不明白,我放养它的几年,它怎么没病?离开不久就生病,是相思成疾还是水土不服?我弄不清楚。它大概过惯了在我家的日子。它习惯了野草的味道,习惯了我的气味。尤其是空闲的日子,它可以下河游泳,可以卧在树荫里反刍,可以驮着我到处游荡,可以在田埂上漫卷野草喜欲狂。它过的虽不是锦衣玉食的日子,可也衣食无忧啊。有我专门为它服务,守护着它。它身上如果有吸它血的牛蜢蜢,我会揸开手掌,狠狠地拍死这些家伙。天气热的时候,我会把小牛赶到水塘里,或者让它滚一身泥,这样,吸血鬼们就无处插嘴,小牛就没有皮肉之痛了。
我的“小牛”在我上学的时候被卖掉的,如果我没去上学,我是不是就能留下它?如果我家有足够的钱买下它,那它就不会那么快被杀,它依然可以活在我的生活里,供我骑,帮我家犁地。它哞哞地叫上几声,我知道,它一叫表示饿了,只要我一站到它跟前,他就会立马从地上爬起来,把头低下,叫我骑到它身上,放它去吃草。
这样的日子数也数不清。
以后的日子,我再也无牛可放了,我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哞哞声,小牛已不在人世,化为虚无。它不是肉牛,是用来犁地的,拉货的,是水牛,花力气耕地,赢得主人信任,养活了自己。可它生病后,被当成了肉牛,逃不脱被宰杀的命运,被分解成若干块,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一想到这,我肚内翻江倒海般,五脏俱焚。如今,看到《动物世界》里的水牛被食肉、食腐动物饕餮时,我都为水牛难过难受。
如果我的“小牛”还活着(水牛的寿命一般12岁,这是我的一厢情愿),它该是牛中的老者了,也该儿孙满堂了。它看透了岁月和人情世故,立世不惊了。可惜,它没有遇到一位让它能长寿的救世主,刚活到自己的青壮年,就戛然而止,实在让我可惜,叫我心疼。
我始终难以忘怀那一只陪伴我很长一段寂寞日子的“小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