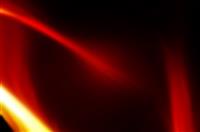不管是北风凛冽,或者雾霭沉沉,每天早晨的余暇,我总是读读你的文章。你以人类的身份,面对苍穹和大地的说话,审视着爱慕着,怜悯着我们最为本质的存在,在街头的咖啡馆,在陋巷的理发间,在职员办公室的窗前,雕刻着我们的思想和灵魂,吟哦着我们的悲伤和沉静。
如此,让我常常不能自已。掩卷深思,看到涌动的浪潮和人群;举头惆怅,看到寂寞的星空和人生。远远地眺望,那滚滚人流汩汩车流的人群,像两岸的山谷和峭壁,一叶扁舟,荡行着一个人的身影;不,是那苍穹之央,唯你独步,从而引人悠情随唱-------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阿。
轻轻的与你挥手暂别,在另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元月初三的早晨,见一个人,比他的妻儿妻姐要早一步起床,在万声俱寂的节日之晨,不动声色的轻声洗漱,用清凉的水涤净眼镜的积垢,在左边银亮的墙镜上,看那张脸是否泛红------那可是心脏不好的征兆。然后,他走出来,走进一个叫做厨房的大盒子,拧开一条黄色管道上的阀门,点亮蓝色的夹杂着桔红的火火焰焰。
火焰燃烧的一侧,那一瞬间,不用去想,顺手而为,自然而然,把叫做牛的奶乳倒进一件金属的器皿,让火燃烧。那些火焰在炫耀,不,是在器皿的底部跳跃舞蹈。好啦,那些能量在白色的液体内部,向外萌发,一个个气泡的蓓蕾,此起彼伏,绽放怒放;再把另一种动物的卵体,那称为鸡蛋的卵体,磕破褐色的外壳,放进去,一同加热,让火燃烧。
火焰微响的厨房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亲属一个个起床。他回头轻言轻语,你们洗吧,早饭快好啦。他用另一种金属,把这些液状的热量分成三份,热烟冉冉地端到另一个较大的空间,再加调味的另外食品,一碟红色的,一碟绿色的。然后,告诉朦胧着走动的儿子:可以就餐;又微微面对出来的妻子和妻姐,微笑微言:开始吃饭。
其时,外面仍然没有声音,所有的车辆,都伏在浅浅的雪地上,没有一丝的风,没有一片的人影,甚至没有爆竹的声响,旷野一样。唯听到厨房的水,从管道里流出的声响,幽谷中的小溪淙淙一样。他抬起头,看到母亲,在雪白的墙壁上,仍然一副哀戚的模样,凄然打量着这个平和的家庭,这初三的早晨。
母亲,你有什么不高兴?你在这样的照片里,在这样的窗口,是否可以动心,是否可以动容?你从你那悲苦的人世里摆脱,俯瞰这下界,这一代人这一家人健康的活着,生活着;俯视着他们像火一样烈烈燃燃,节日的早晨一样静静寂寂。母亲,我的母亲,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哎,你走的太远,你把福分留给了我们!
母亲,在夜的深处,能否给我一个讯息,看我的思考和叙述是否抵达人类的根本?是否是万户千家亦如此吉祥安康?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可以和更高级的思考和写作比肩同行?母亲,在夜的深处,能否给我一个启示,看我是否顾及家庭之余,还可以顾及其他的同类,肩起道义,负人他责?
母亲啊,远在欧洲的葡萄牙,他常常以人类的身份,面对苍穹和大地说话,审视着爱慕着、怜悯着我们最为本质的存在;在里斯本街头的咖啡馆,在第四街陋巷的理发间,在他供职会计所的窗前,雕刻着他自己,也是我们的思想和灵魂;吟哦着他的生命,也是我们的悲伤和沉静。元月初三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