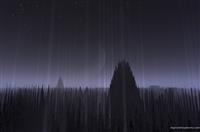9
对常人来说,二00五年正月初三的北川市并没有什么异样,刚被从城南戒毒所接出来的夏茜却有一种陌生感,其实被送进戒毒所就发生在一个月前。像初来者一样,她东张西望着,一切都那么新鲜,都让她好奇。母亲和父亲一左一右地陪着,他们之间没有语言交流,就那么心情沉重地走着。在一个月前,父亲夏波还是这个城市赫赫有名的人物,统领着有关部门,掌管着有关国家机器,而现在退居二线了,曾经掌管的国家机器落在了别人手里,所以开始用脚走城市的水泥路,呼吸被一定程度污染了的空气。
尾随着的那个男人是笔夫。他们一出戒毒所的门,他就在相距一百米远处静悄悄地跟随着。他们拐弯,他也跟着拐弯,没有笑容,而是一脸的凝重。右手牵着的,是他十二岁的女儿,和父亲一样,她一脸的深沉,目不转睛地看着前面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小女孩右侧,那位年轻漂亮姑娘显得要轻松些,但她内心有不小震惊,这来自于最前面的那三个人。
从南城到市中心的政府家属院大约不足二公里路程,但两拨人却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上午十时许,前面那三个人才走进了市政府家属院,这时,他们加快了脚步,像害怕被人看见一样,用近乎小跑的速度,向一个二层楼房的家走去。那个家的二楼阳台上,有一对男女等在那里,见着这三个人快步地走来,便不约而同地下到一楼,打开大门,将三个人迎了进去。
“姐。”女孩叫了一声夏茜,但又不知该说什么,便冲进了一个房间,扑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夏茜跟没事人似的,走进妹妹的房间,劝慰道:“小颖,别哭,我的好妹妹。你哥哥和外侄女回来了,该高兴,明白吗?还有,你哥哥的女朋友、外侄女的新妈妈也来了。”
“姐?!”夏颖转过身来,一把抱住姐姐,泪眼婆娑地说,“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哇?这一切都该是你的,而不是那个苏小姐的,明白吗?”
“妹妹,不该我的,真不是我的,包括你的外侄女也不该属于我。他们都不是我的,是他们自己的。”夏茜忍不住地流出了泪水,“妹妹,你们还在闹离婚吗?别离了,好吗?姐姐求你,真的求你。”
“孩子,收拾一下吧,他们就快到了,你爸已经打了电话。”母亲心情沉重地走进房间,对姐妹俩吩咐道,“无论如何得高兴点,啊?我们一家子也算团员了,团员了啊,团圆……”母亲絮叨着出去后,姐妹俩才停止了哭诉,开始装扮起来。
“叮铃,叮铃,叮铃。”差一刻钟到中午十二点时,夏波家的门铃响了。
“来啦来啦,来啦!”夏颖轻快的声音,从屋内传到了门外人的耳朵里。开门后,她高兴地冲门外的男子叫唤道:“姐夫,来啦?姐姐回来啦,爸爸妈妈都在屋里等着你们哩。”继而,她牵着跟随而来的小女孩,领着三个人上二楼。
“幺姨,姨父来了吗?”小女孩儿问夏颖道。夏颖回过头,用饱含责备的眼光看了一眼笔夫。
“幺姨,你回答呀?”小姑娘追问道,“幺姨父为什么不来,你们离婚了?那我弟弟跟谁,是幺姨父么?”
夏颖停了下来,蹲下身去,抱住小姑娘的头,心情沉重地说:“今天你别提这事,行吗?幺姨求求你。好好陪陪妈妈、外婆、外爷和幺姨,好不好?我们真的很想你和你爸爸。”
“苏阿姨呢?”小姑娘迷惑的眼光看着幺姨,“不欢迎她么?我很喜欢她,爸爸也一样?”
夏颖眼光复杂地看了看苏小姐,然后又落在小姑娘的眼窝里:“欢迎,我们都欢迎。”站起来,她把手伸向苏小姐,难为情地说:“妹妹,不,姐姐。唉,还是叫苏小姐吧。苏小姐,刚才没有给你打招呼,请原谅。因为,一时间,我的确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
“没关系,夏小姐。”苏小姐笑容可掬地回答,“从眼光里,我看出了难为情。不好意思,今天,我不来才是最合适的,但你爸爸和妈妈又一再邀请,所以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小颖,能给你提个小小的请求么?”笔夫插话道,“别再叫我姐夫,好么?这样不合适,而且还会带来不快,能够理解我的心思?”
“那我怎么称呼?”夏颖问,“笔秘书?”
“哥吧,好不好?”笔夫说。
“别扭。”夏颖反对,“一直都这么称呼你,突然间像陌生人那样叫,我难受。姐夫,就允许这样称呼你吧,从前你是我姐夫,又不是假的,有什么呀。”继而,把眼光转向苏小姐,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我想苏小姐不会介意吧?”
“随便吧。”苏小姐表态道,“能够理解,真的不计较。”她抓着笔夫的胳膊,摇了摇,委屈道:“老公,别拿我当小心眼的女人看,好么?”
“谢谢。”夏颖掉下了眼泪,一时间,她接受不了苏小姐拿自己从前的姐夫称老公。
笔夫熟悉夏家,一一打过招呼,并将苏小姐介绍给夏家人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与夏波和夏母拉起了家常。苏小姐却对这个家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在频频地环视着。夏茜看出了她的心思,于是,主动搭讪道:“能邀请你到我的房间里看看么?”
苏小姐欣然接受了邀请,站起来,在夏茜的引领下,走进了她的房间。这个十五平方米的房间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与门对面的墙上挂着夏茜和笔夫的单人照片,两个镜框并排着。在苏小姐眼里,夏茜的瓜子型脸蛋与自己是一种类型,不同的是夏茜脸型稍长,自己属于苹果型的瓜子脸。肤色上,夏茜和自己几乎没什么区别,白净中透着红色,笑容甜甜的,使人很容易想到“娇翠欲滴”这个成语。夏茜的眼光似乎缺少力度,显得有些黯淡,甚至可以说是凄清,尽管如此魅力仍然投射出来。如果不是因为眼光中的悲苦神情,她定会是个对男人们产生极强吸引力的女人。再看看眼前这个现实的女人,尽管经过一番精心的装扮,但与她三十五岁的年龄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再也见不到照片里的神韵,额上生长了许多的皱纹,与此时瘦削的脸相匹配。
与现实相比,照片中的笔夫多了些稚嫩。端详了照片后,苏小姐下意识地把头转到客厅,看了一眼正在与夏波夫妇拉家常的笔夫。她觉得,目前,他脸色更加白净了,更叫人能够品出成熟男人的味道来,而且显得年轻,有活力。尽管,额头上也生出了一些皱纹,但一双敏锐的目光传递出了不太安分的内力,此时他和夏茜的反差实在太大,叫人有些难以置信他俩从前是一对极为般配的夫妻。
“为什么经历那么多坎坷后,笔夫的容貌并没有较大变化,反而还流溢出一种对女性十分强烈的魅力?”苏小姐感到不可思议,暗叹,“女人真的就容易被磨难击倒,而男人就会在磨难中成熟?”她蹙起了眉毛,一排洁白的上牙咬住下嘴唇。
“坐吧,苏小姐。”夏茜揣摩到了苏小姐的内心世界,心情更加沉重了。在招呼苏小姐后,自己先在床上坐了下来,似乎想诉说些什么。
这时,小姑娘进来了,她没有称呼夏茜妈眯,而是从身上掏出一张银行卡来,递给苏小姐:“苏阿姨……”说到这儿,她准备转身出去,却被抓住了一只手。
也许是顾及什么,苏小姐关上房门后,对小姑娘说:“尧尧,怎么不叫妈妈?叫妈妈,啊?”
小姑娘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夏茜,嘴唇蠕动了半天,才别扭地吐出了“妈妈”两个字。夏茜的眼泪喷薄而出了,但她尽力克制着,不让哭声大到能够被客厅里的人听见。她一边哭,一边掏早已准备好的纸巾。
这一幕感染了苏小姐,眼泪不由自主地滚了出来,更让她伤心的是小姑娘没有为妈妈擦眼泪,而是关切她。小姑娘问道:“苏阿姨,你干嘛哭了?”
夏茜再也控制不住了,扑倒在床上,伤心欲绝。苏小姐茫然无措了,拉着小姑娘的小手,走到房间唯一的一扇窗前,轻轻地打开窗户,眺望着远方的建筑物,想平息自己的情绪。当转过身来时,夏颖已经进入了房间,把姐姐扶了起来,姐妹俩相依为命地搂抱着肩背坐在床上,两双湿润的眼睛显示着她们哭过,而且还在继续哭着。她也全然不知小姑娘什么时候挣脱的,转过身来时,她已经偎依在夏颖的旁边,但仍然远离着自己的妈妈夏茜。她想: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多么残酷啊!
苏小姐走过去,挨着夏茜座下,把小姑娘刚才递给她的一直拿在手上的那张银行卡交给夏茜。她说:“你是尧尧的妈妈,这是她今年的压岁钱,应该你保管,收下吧?”
夏茜看着女儿,女儿却把头低下了。此时,女儿也在扑簌簌地掉眼泪。“是笔夫说的。”苏小姐觉得应该再解释一下,于是,补充道,“放心吧,尧尧,我们会带好的,会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每年都会回来看你们,今后会照管你的。”
“笔夫是个好人,是我们对不起他,无论如何都不怪他。他又要走,是吗?”夏茜开口说话了。
“嗯,调总行工作。”苏小姐点头道,“春节后就走。”
“把这钱给他吧,到了北京,需要买房,置家,女儿读书也要钱。你不了解,他吃过很多的苦,但我当时又不能帮助他,所以,他爸爸妈妈一直恨我,不要我进家门,他也不回去。唉,他会给你说的,我了解他的性格。”夏茜半自言自语地说,并把银行卡往苏小姐手中塞,拒绝接受。
“你需要。”苏小姐说,“我们有钱,他家的公司很大了,我们家也有个山庄,都能挣钱,不缺。算我求你,收下,好吗?这是尧尧的,该你保管和支配。”
“姐,你就拿着吧,啊?”见两个人来来回回地推诿着,夏颖解围道,“不然,姐夫又会不高兴。不是说好今天要高兴点吗?外侄女和姐夫可是将近八年才回家呀,你不是一直盼望着他们回来吗?一切都过去了,大家高兴地吃一顿饭吧。等会儿,你们不是还要回自己的家去看看吗?昨天晚上,已经收拾好了。”
夏茜收下了那张银行卡,她对苏小姐说道:“谢谢你,苏小姐。”
“谢你女儿和笔夫吧,是他们的心意。”苏小姐回答。
“笔夫是好人,我知道。苏小姐,你也是好人,我记着。就拜托你把女儿管好吧,她本来就不是我的,是你们的。”
“姐——?”夏颖反对道,“你说什么呢?外侄女这么漂亮,你不要,我要。”接着,她用祈求的眼光看着小姑娘:“叫妈妈呀,你?”
小姑娘下了很大决心才叫出了一声:“妈妈——!”夏茜笑了,她很想抱抱几乎和自己一样高的女儿,但女儿迟迟没有站起来……
一九九二年的元旦节,是夏茜披上洁白的婚纱,走进了婚姻殿堂的日子。然而,这天,无论怎么努力,她和笔夫都未真正品尝到新婚的快乐。结婚日前,笔夫多次带着夏茜回家,下跪,请求父母在结婚那天一定到场,不留下遗憾,更不想让副市长夏波难堪,但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偎暖父母的心。他们的态度很坚决:笔夫不能和夏茜结为夫妻,夏茜不能成为笔家的儿媳!他们心目中只装着一个合格的儿媳那就是于红。除了于红,笔家父母谁都不认同,不仅不让他们进家门,而且也拒绝参加婚礼,更别奢望他们抄办婚事。理由很简单,于红在家里住了三年,对父母也孝顺,就是好儿媳,就是称职的儿媳!尤为重要的是,于红还是笔家的功臣,当初,没有她,笔夫就不会有今天,这是笔家父母一直无法解开的疙瘩,所以夏茜和笔夫多次回笔家都被恶骂一顿,而且还一无所获。每一次,笔夫都抱着莫大希望回去,但最终只能痛哭着离开。
结婚典礼来临的前一天傍晚,在联系妥婚纱后,笔夫和夏茜提着两瓶酒回到了家里。父亲一听是笔夫和夏茜在叫门,便不开,还故意在屋里咂东西。母亲生怕出事,一个劲儿地在屋里给儿子求情让他们走开,别再打扰。他们只好把酒放在门外,冲屋里的父母说道:“爸,妈,把这两瓶酒拿进去吧,我们走了。明天,要来就来吧,不来也不会怪你们。”说完,便哭着离开了。从此,笔夫再也没有流过眼泪了,也不再提回家的事了。和妻子夏茜一块儿,住在市税务局的家属院里,过起了几乎与父母断绝往来的生活。
与父母对婚姻的阻饶相反,夏家对笔夫的关爱有加。为了女婿能够像自己一样,今后走上官场,成为北川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夏波多次暗示北川银行行长要重用笔夫。笔夫因此遭到了非议。同事们不信任他的能力,一些依靠岳父上爬的议论之词,像纸片一样,频频飞进他的耳朵里。他感觉到了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不是一个人,或者说正在丧失一个人的尊严。更为要命的是,他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正在成为一些人竞相拉拢夏波的工具,因此,慢慢地作为夏家女婿的优越感消失了,而且还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从前,尽管于红恨自己背叛,但她没有攻击笔夫,现在不同了,在众口铄金的舆论背景下,也开始攻击了。
一天,笔夫参加完市政府一个重要会议后,在政府招待所就餐时,于红端着酒杯过来了,她向笔夫敬了一杯酒。笔夫让服务员添了点酒,举杯回敬道:“感谢政府部门对蓉城银行北川支行信贷工作的支持。来,干杯吧?!”
没想,于红拒绝喝酒。她朝在场的夏波副市长驽了一下嘴,挖苦道:“该感谢的是他,他才是你最大的恩人。我一个小秘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官位,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对吧,笔科长。”奚落完,她转身就离开了。
笔夫难堪极了,“滋溜”一响,喝了那杯酒,将酒杯扔在饭桌上,离开了酒席。没想,于红一路吼叫着追了出来:“喂,喂,喂喂——笔科长——!”
他停下来,转过头去,恼羞成怒地问:“奚落了一顿还不够,要继续才解心头之恨,对吧?好啊,你来吧,用罪恶毒的语言继续挖苦吧。被其他人误会和奚落我不难过,你也加入到了其中我非常失望,真后悔曾经爱上你!不过,我不害怕,我不是谁的寄生虫,我是我自己!你给我记住,我叫笔夫,曾经爱过你的人。你更应该明白你自己是谁,你叫于红,现在和其他人一样,正在无端的奚落你曾经的爱情。要让我成为落汤鸡,或者落水狗,是吗?我不怕,我不会害怕!来吧,你!?”
发泄完,他头也没回就离开了。到办公室后,他越想越生气,万万没料到于红也这样对待自己,而于红又是他父母认为最好的儿媳。尽管已经有女儿了,父母还是不肯原谅自己,他们不仅不肯接受妻子夏茜,就是女儿也不喜欢。女儿都快满一岁了,除了母亲偷偷来看过之外,父亲至今还没有去看一眼。更为伤心的是,偶尔抱着女儿碰见父母时,父亲总是像遇到不共戴天的仇人似的,拽着母亲打老远就另寻一条路离开了。如果说自己和妻子有错不该原谅的话,那么可爱的小生命有什么错?作为儿子和儿媳已经为过去的错误承受了巨大的代价,难道非得要女儿也去为自己承受代价吗?
回想起婚姻里所发生的一切,笔夫感到非常的困惑,更叫他困惑的是父母心中的好儿媳于红也开始奚落自己。他似乎觉得自己该改变人生方式了,这种改变从哪儿开始呢?他知道要摆脱目前的困窘,必需要摆脱夏波的阴影,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男人!但是命运却不按照他的方式发展,夏波再一次给他送来了好消息。女儿的一岁生日庆典,按照妻子事前的安排放在了夏家。夏家将孙女的一岁生日庆典办得极为隆重,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都被邀请到了,其中最显眼的人物是组织部长。晚会上,笔夫获得了一个信息,组织部即将考虑他的升迁问题,言下之意是不久就会荣升为副行长。他把组织部长拍到一边,问:“定了?”
“板上钉钉的事。”组织部长说,“放心吧,老弟,我办事夏副市长最放心,不会有闪失。”
“不是那意思,相反,我希望有闪失。”笔夫强调,“我不需要这种恩赐。”
“喂,老弟,你喝多了。”组织部长唐塞道,“你不能再喝酒了。”
“我没喝多。”笔夫申辩。组织部长不想再与他讨论了,匆匆忙忙地吃完饭,离开了夏家。他害怕笔夫闹出点事情来,影响自己的形象。
“来,儿子。”当笔夫正在暗中嘲笑那位胆小如鼠的组织部长鬼鬼祟祟的行为时,夏波招呼他道,“这是王伯伯,在市委分管组织工作,给他敬一杯酒,恳求他今后多多关照。”
笔夫只好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走过去给分管组织工作的王副书记敬了一杯,并违心地说:“王伯伯,今后,请多多关照。”笔夫本来就厌恶权力交易,但偏偏肮脏交易的组织者是岳父,时间是自己女儿的生日晚会,他感到非常恼火。想起于红的奚落、父母的鄙视、同事们的篾视,他觉得自己非常孤独,正在脱离一种正常人的真实,走向高处不胜寒的窘境。这不是他所希望的,迫切地需要回归到真实中,于是,那晚,在回家的路上,他闷闷不乐。
“喂,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夏茜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问,“生日晚会办得不好么?”
“没有。”笔夫回答,“很好,好得我有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得真实,找不着北了。”
见丈夫话里有话,夏茜更是一头迷雾:“你发神经啦?人家可是羡慕死了,你倒不以为然,啥意思嘛,你?!”
“喂。”笔夫放大了声音,“今后,你能不能不这样?我们没有家,非得要到你娘家去办?要明白,这是我们的女儿过生日,女儿是我们的,我们的?”
“那到你家办行了吧?”夏茜也生气了,“你爸妈让进屋吗?我也想到你家,可是不让进屋,我怎么办?有本事,做通工作,回你家呀?神经病!”她抱着女儿,气冲冲地往家里走。
不久,夏波明显感觉到了笔夫的情绪低落了。他分析认为问题出在外孙女生日晚会上的表态迟迟没有兑现,于是,找来组织部长,询问新一轮干部考察工作的进展。当听完组织部长汇报后,发现没有笔夫的任职考察情况报告,便不高兴地拉长了脸。
“噢,夏市长,有一个情况需要向你汇报。”组织部长补充道。
“什么情况?”夏波知道要谈自己女婿的事了,便问。
“关于蓉城银行北川支行笔夫同志的任职问题。据反应,这位同志思想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水平极强,符合条件。”组织部长首先汇报了单位的态度,接着汇报笔夫个人的想法,他说,“不过,这次没有形成材料,因为,笔夫他……”
“为什么?”夏波锁紧了眉头,“这么好的同志,为什么不积极推荐?”
“关键是笔夫同志自己不同意。”组织部长难为情地汇报道,“据考察的两位同志讲,他说自己还需要锻炼,今后有机会,便推介了另外一位同志。考察的同志都为他这种高风亮节所感动。由于他本人不愿意,所以,在材料准备上,就有些不太配合。”
“这更是好同志嘛。”夏波内心里对笔夫表示愤慨,“他不配合,当然是因为谦让,但作为组织干部,就该做做工作嘛。几乎每一位谦让名利的人都是这样,这时组织部门就应该尽量做通思想工作,总不能因为本人谦让,就让好干部落选吧?”
“好的。”组织部长急忙回答,“我们尽量做工作。”
组织部长走出办公室后,夏波心头的怨气就表露了出来,他把拿在手上的一支笔扔在办公桌上,“嚯”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走向一扇窗户,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笔夫要主动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决定劝劝女婿,让他转变思想观念。于是,转过身来,走近办公桌,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不几秒钟便有人接,他说:“我是市政府夏波,请找一下夏茜接电话。”没等几分钟,他又冲电话里说道:“小茜吗?我是爸爸。孩子还好吧?晚上你们回来一趟,爸爸有话要交代,必须得回来啊?晚饭就在这边吃,我和你妈也好久没看见孙女了,挺想的。顺便问一下,最近,笔夫是不是情绪有些变化?对你们母女怎么样?那就对,就怕那小子发牛脾气。好吧,早点回家,爸爸等着。”
夏波把女婿想了一遍,觉得这小子太书生气了。也正因为如此,觉得该好好给他上一课,早日洗掉书生气让他成熟起来,但他也明白笔夫不会心甘情愿地称臣。他的骨子里有一股傲气,不采取合适的方法难以驯服。夏波认为,目前,由于他还很不成熟,才没有爆发出他生命里所聚集的能量,当务之急是让自己女婿的能量早日爆发出来,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去建立政治王国。他想:一个男人只有在政治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才能够算是成功。同时,一旦在政治上建立起了王国,就不会轻易去背叛自己的糟糠之妻,因为,每一个玩政治的男人都非常清楚,男女关系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损害有多么厉害,闹出风流故事的人的政治生命是短暂的。笔夫一旦喜欢上了政治,就会对自己的女儿忠诚。其实,政治的好处在于它无形中把家庭关系也纳入了衡量一个人政治上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从而对玩政治的人也是一种欲望的约束。只要在乎政治权力,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就必须努力去营造一个至少表面和谐的夫妻关系,给人们一个好的印象。否则,就会给人们留下政治上不成熟的坏印象。对大多数政治上风光的人来说,即便夫妻关系再不和谐,双方都会努力地让婚姻苟延残喘着,绝不会闹翻天,葬送政治生命。一阵电话铃声,将夏波从一种梦幻般的精神家园里拉回到了现实,他拿起电话道:“喂,我是夏波。”发现电话是妻子打来的,忙说:“噢,马上回家。小茜他们来了吗?”放下电话后,他胡乱地收拾一下桌上的东西,便熄灭了办公室里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