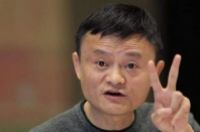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