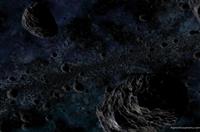作者:范芝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4月
中国的人口流动,是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教授范芝芬(Fan C.Cindy)的新著《流动中国:迁移、国家和家庭》对此进行了研究。
1.国家和家庭的视角
主流迁移理论大都认为迁移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与地区收入差距而忽视了国家在国内迁移中的作用。
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直观印象是春节前后满载大批返乡民工的列车与毕业季负荷大小行李,怀揣一纸证书,带着期待与焦灼的目光奔赴各地的莘莘学子。隐藏在上述两类显性群体背后的,是零零散散因婚姻、经商、工作调动等故产生的个体或家庭迁移。人口迁移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兴衰。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是社会活跃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二战后美国西北部地区“阳光地带”的迁移即是由东北五大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高科技的大量推广、生态环境变迁等一系列因素共同推动的国内迁移,对迁出及迁入城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加之国家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的双向驱动,中国人口流动性在不断加强的同时,迁移的流向和机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政策推动(如西部开发等)仍然持续,另一方面基于经济与个人利益衡量等相关因素在迁移过程中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大。种种变化引起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教授范芝芬的著作《流动中国:迁移、国家和家庭》一书值得关注。
在关于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中,不同理论视角导致研究取向上的差异。身份认同理论关注迁移人口在移入地的社会融入过程与身份建构;网络理论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迁移人口获得经济机会、更改迁移目的地等方面的作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不同迁移人口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并探寻背后的社会与制度性因素的根源。尽管在研究取向上存在差异,但主流迁移理论大都认为迁移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与地区收入差距而忽视了国家在国内迁移中的作用。(第2-3页)
在作者看来,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尽管引入市场逻辑,以发展为导向,通过对外开放、出口加工等政策措施构建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指导与规划作用未受影响。(第4页)当一个社会经历着快速变迁的时候,家庭策略显得尤为重要。(第9页)基于此,作者以国家和家庭为视角,选取农民工这一当代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生产的主要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如何重构,借此理解当代中国的迁移流动及其未来走向。
2.婚姻成为女性流动的重要途径
由于被排斥在城市婚姻市场之外,她们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男性适龄群体更感兴趣。
作者运用“四普”和“五普”数据,从宏观层面考察了近20年来中国的人口迁移量与迁移空间分布模式的变化。一方面,迁移多从中南与西南地区省份至沿海地区省份,从农村至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入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作用愈加重要,距离的阻碍趋于减弱。省际迁移的增长速度高于省内迁移。人口流动日益单向和集中。(第46页)迁移人口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善经济状况。经济动机与市场驱力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的人口迁移模式和迁移过程。(第88页)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口迁移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分层烙印。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国内人口迁移是一种包含永久迁移和临时迁移的二元迁移体制。永久迁移人口主要受国家批准且具有较高的技能和文化程度,临时迁移人口大都是自发的、受市场驱动,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第27页)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粮食、就业与福利三个方面强化和维持了城乡不平等,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分流器。尽管该制度饱受诟病,且人户分离的数量和比率与日俱增,但迄今为止的户籍改革主要在于促进国内劳动力流动,而非为了消弭城乡不平等差距。永久迁移人口主要通过政府计划或被教育机构录取这些制度机会来实现迁移,而临时迁移人口则主要通过市场或者说国家计划外的方式进行迁移。(第87页)城市的大门向有钱、有技术、高学历的精英群体敞开,却为大部分教育程度低、技术水平不高的农民工构筑了无法逾越的藩篱。
尽管农民工群体负担了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城市零售业的消费,但他们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享受城市公共资源与服务。国家既需要大量农民工进城从事相关行业,又不给其相应的城市居民身份,借此构建出一个迁移劳动体制,这个体制以极低的成本负担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飞速发展。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导致作者笔下的农民工群体在迁移过程中具有相当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他们能够灵活运用各种家庭策略。尽管“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策略强化了社会性别角色意识,但他们并不想在城市定居,成为永久的城市居民,而是通过循环迁移和汇款等方式与农村老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两地分隔与信息通讯的发达加速了农民工的流动,强化了他们的集体谈判能力,赋予他们选择工作与打工地点的权力。他们更愿意在农村老家和城市间以及不同打工地点间循环流动,并最终返乡,从而在城乡之间游刃有余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城市的外来者,这种身份认同感导致他们做个人决策时,短期收益的考虑成为主导,灵活穿梭于规章制度的缝隙之中。
对于农村女性而言,婚姻日益成为她们实现流动,迁往发达地区,追求个人幸福的重要途径。由于被排斥在城市婚姻市场之外,她们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男性适龄群体更感兴趣。
3.忽略了社会层面的分析
在看到农民工群体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一面的同时,不应忽视近年来被日益关注的“留守儿童”“孤寡老人”“临时夫妻”等直面道德底线的社会问题。
尽管作者综合运用了翔实的数据资料、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文本等多种资料,但得出的部分结论仍然值得商榷。作者一方面看到在国家体制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群体通过在城乡之间的循环流动与各种博弈策略达到利益最大化,展现出这个群体的主体性。顺此逻辑,似乎声势浩大的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没有输家,其结局是双赢的皆大欢喜。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整体利益,农民工群体尽管在城市受到不公对待,但他们在空间流动与制度缝隙中获得了局部利益。他们无意占据城市,他们的城市经历是其日后在乡土社会崛起的垫脚石。
至于城市本身,依然是高学历者、资本家等精英人士打拼的乐土。这样一种逻辑推导显然无法回答当前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生态恶化、圈地造城运动、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农民工的个人决策是以短期收益考虑为主导的观点,不仅将其置于道德低位,更易使农民工的声音沦为各种冠冕堂皇的“长远发展”决策的牺牲品。事实上,那些打着民众旗帜的“长远发展”决策背后往往是特定阶层赤裸裸的短期收益。
在笔者看来,作者之所以得出该结论,原因在于太过于注重经济层面的考量,而忽略了社会层面的分析。在看到农民工群体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一面的同时,不应忽视近年来被日益关注的“留守儿童”“孤寡老人”“临时夫妻”等直面道德底线的社会问题。倘或综合经济与社会的因素,笔者更愿意相信农民工的迁移流动是弊大于利的。那么农民工为什么仍然要发生迁移和流动?因为触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商品经济与各种具有明显价值导向性的城镇化政策的相继出台,让农民工群体已经无法从事传统“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为了生计,他们必须背井离乡。他们能够感受到城市并未向他们敞开接纳的胸怀,但他们也许意识不到他们当初看似主动选择的“进城”,其背后是被国家体制驱赶所至。
中共十八大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关于如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将农民变为市民,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里,将会有更大规模的迁移流动人口踟蹰行走在城市化的道路上。象征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能否给他们一个安居乐土,不再颠沛流离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