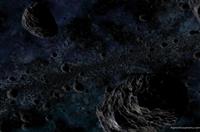
“一带一路”既是中国对外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进程的内在趋向。如果从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一带一路”与古代中国内外秩序关联极大,称之为中国的生命线也不为过,近代中国的衰落正是从丧失“一带一路”的主导权开始的。今日重倡“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不仅是对中国历史道路的回复,同时也是对此前时代的超越。中国历代侧重不同,汉唐元清重西北、宋明重东南,将西北与东南两线并举,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厚,本文拟从“一带一路”与古代中国的内外秩序的关系角度立论,即从国家建构的视角来探察“一带一路”之于古代中国的内在性,并以此延伸“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空间。
一、中亚地区与汉唐大一统之建构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得名于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riedrich Von Richthoen)的《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亚丝绸之路》一文[1]。此后,大量的研究都聚焦于“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学界进而形成一种特定范式,将“丝绸之路”看作是唐宋海上活动兴起之前“封闭”的中国通往世界的唯一通道。这些看法固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将“丝绸之路”仅仅看作是一条中国通往西方的通道,则遮蔽了该路沿线地区之于中国国家建构的意义。即使将“丝绸之路”看作是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通道,也绝不始自公元前2世纪,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这条道路就已经存在[2]。除了《吕氏春秋》《淮南子》《逸周书》等典籍中零星提到西域的物产之外,阿尔泰山地区断代为公元前5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群中出土的中国丝织品,也为此路的存在时间提供了物证[3]。汉兴之前,大月氏从河西地区迁往中亚,正是“丝绸之路”业已存在的依据。汉武帝在募人通使西域之前,就清楚地知道这条路的存在,其所担忧的只是“道必更匈奴中”,无法为汉朝所用而已(《汉书·张骞传》)。“丝绸之路”的得名与开辟时间,学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研究,现在的问题理应转向汉王朝构建大一统时,“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之于中国的国家建构之意义所在。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在中国正史中被称为“西域”。尽管不同史书记述的范围不同,但大略包括今日中亚全部、西亚和南亚大部、北非与欧洲一部[4]1。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西域”并非均质的概念。里海以东被汉、唐等王朝视作追求直接影响,甚至是直接控制的地理空间;里海以西直至欧洲,则主要是追求“徕远人”“致殊俗”的象征意义,其着眼点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皇权声威的宣示,如汉魏正史《西域传》之重视大秦、安息,两唐书《西域传》重视大食、波斯。汉唐王朝的这一地缘政治构想与当时族群的地理活动空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从欧亚大陆东端的兴安岭开始,沿着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一线以北,包括中国东北北部、蒙古、新疆、中亚、南俄罗斯、乌克兰直到多瑙河流域,这片广大的区域是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游牧地区。这片区域又以里海、乌拉尔河盆地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前的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游牧文明及其所有者斯基泰人最早发源于伏尔加河流域,但是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国际学界通常都承认游牧文明的中心是在阿尔泰、唐努乌梁海、蒙古西部及西伯利亚南部地区[5]。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是由欧亚大草原东部地区主导的,游牧族群在阿尔泰、唐努乌梁海、哈萨克草原一带形成后,向西迁徙成为通例[6]。公元前3世纪以后,出现在中国史籍上的北方游牧族群在地理空间上的迁徙也主要是从东向西,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往往是迁徙的第一站。大月氏、匈奴、嚈哒、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莫不如此。因此,中亚是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关的广义游牧地带的一部分,它与蒙古高原同属一个历史空间,在族群政治上具有密切的联动性。如果从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完成囊括农耕区与游牧区“内而不外”之大一统,必须有着明晰的中亚战略。换句话说,古代中国要建构可控制的地缘空间,中亚是其西北战略支柱。
中亚被纳入中国的历史空间,是从公元前3世纪与公元前2世纪之交大月氏西迁开始的。匈奴对大月氏的战争,推动了族群迁徙、改变了中亚草原的面貌。战败了的大月氏人从中国的敦煌、祁连间迁往中亚。一般认为,大月氏人是操印欧语族群最东一支的吐火罗人。最初,大月氏迁往伊犁河上游地区,赶走了原本居住在此的塞种人(斯基泰人),战败了的塞种人向南迁徙,受族群南迁的冲击,正处于国力下降轨道中的孔雀王朝更加衰落。
大月氏迁居伊犁河流域不久,匈奴支持乌孙击败了大月氏。于是,大月氏继续向西越过锡尔河,进入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然后,大月氏向南征服了大夏,即阿姆河到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这一地区古希腊人称为巴克特里亚。至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大月氏有户10万、人口40万、胜兵10万。大月氏分为5部,每部皆有翕侯(《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曾居住于中国河西地区的历史以及与匈奴之间的几次生死战,成为汉武帝开启中亚战略的历史认识基础。《汉书·张骞传》记载了这一缘起: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由此可见,中亚地区由于大月氏的迁居及其与匈奴的历史恩怨,在汉武帝建构大一统时被纳入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大月氏在协同汉朝发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中持消极态度,但是汉朝却依据张骞通西域获得的情报而制定了清晰的中亚战略: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史记·大宛列传》)
所谓“以赂遗设利朝”,颜师古的解释是:“施之以利,诱令入朝。”这是“丝绸之路”成为经济通道背后的政治考量,其最终目的是“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即建立起对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康居的统治权,将万里之地纳入汉朝的大一统之中。在上述各国中,汉武帝选择以大宛为推行其西域政策的核心区,这不仅是因为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以大宛为中转站、其向汉武帝汇报西域诸国情况皆以大宛为坐标,更是因为大宛对中亚诸国的人心向背有着指标性意义。《史记·大宛列传》云:
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
从上引可知,“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仍然是汉朝与匈奴角逐的区域,而大宛以西诸国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即不愿主动加入汉朝的天下秩序。之所以大宛具有风向标意义,是因为在经过大月氏侵略之后形成的中亚诸塞种国中,大宛距离汉朝最近。大宛与大夏皆为塞种四部之一的Tochari部,康居在锡尔河北岸,为塞种Sacarauli部,奄蔡分布于里海至于咸海之间,是塞种Asii部[4]140-141。大宛对汉朝的态度将会影响中亚诸国。不仅如此,大宛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的战略位置也极为重要,其处天山山脉西端以北,吉尔吉斯山以南、锡尔河上游,东、南、北三面环山,无论是中亚民族东进,还是北方民族西进河中地区,都要经过此地。对汉朝而言,出天山之后、进入中亚草原地带之前,费尔干纳盆地是极具战略价值的前沿冲击阵地,可以以此为据点威慑中亚各国。
为此,汉武帝以大宛之贰师城的城名设置“贰师将军”一职,令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征伐大宛,第二次更是“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大宛之战的结果是杀大宛王、郁成王,“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伐宛之威德”(《史记·大宛列传》)。正因大宛对于汉武帝实现中亚战略意图具有重要性,故而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以“大宛列传”为传名记述汉朝经略中亚地区的历史。
汉武帝经略大宛是着眼于中亚、经略中亚又是着眼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问题。大宛以西诸国最后“咸尊汉”,也须待到匈奴归附汉朝之后。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成为左右中亚认同汉朝的决定性因素(《汉书·西域传》)。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汉朝与匈奴之间恢复和亲。在包头等地出土的墓葬瓦当中,有“单于和亲”的汉文字样[7]。“汉匈一家”的局面已经为汉、匈双方所认同,中亚诸国作为蒙古高原势力的协同者,也被纳入汉朝的天下秩序中。在费尔干纳盆地发掘的公元1世纪以前的80多处500多座墓葬中,绝大多数都有汉式铜镜[8]。可见,汉朝已经在此稳固地发挥了影响力。汉武帝时代所致力的大一统到汉宣帝时得以实现,完成了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合一。
东汉前期,北匈奴与汉朝间烽火再起,中亚诸国在北匈奴与东汉之间摇摆不定。汉和帝永元年间,北匈奴与东汉之间进入决战阶段。永元二年(90年),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派遣副王率领7万军队跨越葱岭入侵汉朝,这一反常的军事行动表面上的理由是班超拒绝贵霜帝国和亲的要求,但实质上却是贵霜帝国借汉朝与北匈奴战争之际的一次军事冒险,试图挑战汉朝在中亚的统治秩序。班超采用坚壁清野的战略,待到贵霜食尽,派遣军士截杀贵霜帝国派往各地求援的使者与骑从,贵霜副王“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后汉书·班超传》)。次年,北匈奴单于被汉朝击败西逃。汉朝巩固了在中亚及蒙古高原上的统治秩序,可见中亚问题与蒙古高原游牧族群问题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古高原族群政治的变动仍旧影响着中亚。虽然游牧族群的主要迁徙方向是塞内,但是4世纪末柔然人的扩张带来了新一波的族群迁徙,致使中亚政权更迭频繁。因受到柔然人的攻击,原本居住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东的嚈哒人进入中亚,夺取了贵霜帝国的河中地区[9]。425年,嚈哒人进一步占领大夏;5世纪中叶南下彻底灭亡了贵霜帝国。嚈哒帝国的势力范围,北尽敕勒、西及波斯、东到于阗。此后,嚈哒帝国的兵锋主要指向伊朗高原的萨珊波斯,直到6世纪下半期嚈哒帝国灭亡。虽然北魏与柔然并未如汉朝与匈奴那样将争斗空间延至中亚,但双方在中亚均保持了影响力。嚈哒一方面与柔然通婚;另一方面从文成帝太安年间(455—459年)开始对北魏“每遣使朝贡”,直至孝武帝永熙(532—534年)年间北魏分裂为止(《魏书·西域传》)。
6世纪中叶,取代柔然在蒙古高原霸主地位的是兴起于阿尔泰山南部的突厥。在随后的30年里,突厥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其疆域从辽东湾直到里海,几乎将欧亚大草原的亚洲部分全部控制。于是,“突厥”一词便由原本的部族名称转化为对草原上铁勒诸部及其他族群的共称。对于构建大一统的隋唐王朝而言,将突厥纳入其统治秩序遂成的题中应有之义。隋朝创立不久,隋文帝便利用突厥内部的政治矛盾,于583年迫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突厥与西突厥以阿尔泰山为界,原本的最高统治者沙钵略可汗统辖东突厥。隋朝对东、西突厥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维系突厥内部各方势力的对立,使得突厥最高汗权始终无法建立,经常出现多个可汗并立的局面[10]。大业七年(611年)冬,隋炀帝迫使中亚的最高统治者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隋炀帝明确表示隋朝皇帝与西突厥可汗之间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
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隋书·突厥传》)
于是,次年元会,处罗可汗上寿将隋炀帝称为“圣人可汗”,强调“圣人可汗”皇权的至高性,“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隋书·突厥传》)西突厥可汗的入朝及其所上“圣人可汗”之号,对于隋朝而言,成为其大一统的象征。
隋唐之际,西突厥可汗将牙帐迁往中亚的石国,其疆域扩大为西到今伊朗、东至新疆、南达阿富汗北部、北接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此后,西突厥“十箭”(十姓部落)分为左、右两厢,以碎叶为界,后以伊犁河为界。西突厥东、西两部又处于战争之中。唐太宗时期,曾立乙毗射匱可汗为西突厥可汗。在唐太宗驾崩、政局不稳之时,唐朝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兼并西突厥各部,自称沙钵罗可汗。唐朝平定贺鲁之叛后,贺鲁自省请罪:
我破亡虏耳!先帝厚我,而我背之,今日之败,天怒我也。旧闻汉法,杀人皆于都市,至京杀我,请向昭陵,使得谢罪于先帝,是本愿也。(《旧唐书·突厥传下》)
贺鲁以“汉法”请罪凸显了唐朝在中亚的统治权威。唐朝随后在西突厥东部五部设昆陵都护府,西部五部设蒙池都护府,昆陵、蒙池都属于安西都护府。703年,唐朝增设北庭都护府统辖昆陵与蒙池,完善了其在中亚的行政体系[11]。
8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帝国逐步侵入中亚河外地区。河中地区是唐朝要确保的地区,阿拉伯帝国步步蚕食突厥领地、挤压突厥部落、觊觎河中地区,必然与唐朝发生冲突。751年,阿拉伯帝国将领伊本·哈里与高仙芝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因葛逻禄的背叛,唐军战败。随后因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原西突厥领地中,锡尔河以北仍然由西突厥各部占据,锡尔河以南则被阿拉伯控制[12]。
在随后的历史中,中亚经历了伊斯兰化、蒙古化、俄罗斯化的历程;与此同时,中原王朝的重心转向东南,尤其是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海上商路进入繁盛期,汉人逐次开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并移民东南亚。
二、明代的海洋经略与天下秩序之建构
15世纪开始,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从此分散的国别史、民族史开始整合为世界史。在这一过程中,明朝推行的政策却是海禁政策,即禁止中国商民出海贸易。这一政策严重限制了中国的海洋活动。但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推行海禁政策则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对这一问题必须做出历史的分析。
从元朝开始,中国沿海便面临着日本倭寇的侵扰。明朝建立后,北到辽东、山东,南到江浙、福建、广东都频繁遭到倭寇入侵。倭寇问题成为明朝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甚至丞相胡惟庸也是在里通倭寇的罪名下被处死的。为了解决倭寇侵扰问题,从洪武二年(1369年)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屡次派遣使者赴日本交涉。然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北朝征夷将军足利义满、还是南朝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另有良怀一说),都并没有遵照朱元璋的要求剿灭倭寇,于是,日本的北朝、南朝的进贡都遭到朱元璋的拒绝,朱元璋还给日本南北政府都发去咨文,对他们放纵倭寇进行斥责。咨文分见《明太祖实录》卷50“洪武三年三月戊午”条、卷138“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影印1962年版,987-988页、2174-2177页。然而,朱元璋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倭寇问题的努力终归是失败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再次下诏:“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影印1962年版,2197页。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位期间一共下过六次禁海令。这从反面说明朱元璋的禁海令效果不佳,只有不断有人下海贸易,朝廷才需要一再重申禁海令[13]。
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明朝要断绝与海外的联系,其真正目的是将获利丰厚的海外贸易由朝廷垄断。朱元璋规定,外国入贡使节须携带国书表文,验明身份后入贡,朝廷回赐。除了“贡”与“赐”的物品外,对于使节入贡船只所装载的欲与明朝交易的其他货物,朝廷经常予以免税。因此,如果某国需要与明朝进行贸易,它必须向明朝称臣、纳贡,只有获得明朝承认的朝贡身份者,才能与明朝官方贸易。
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便宣布了其对外政策:“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参见《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影印1962年版,1278页。在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祖训首章》中,朱元璋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分别是: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浡泥。朱元璋心目中的“不征之国”主要是指东北亚、东南亚的沿海国家,这些国家恰恰是明朝主要的贸易对象。虽然朱元璋不以军事征服这些海上国家,但是却巧妙地通过海外各国对明朝经济的依赖,以交易权为手段,建立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进而将经济权益扩大为政治权利,羁縻海外诸国。
正是在这一考量下,明朝才派郑和率领庞大水军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历时28年七下西洋,到达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前期海洋政策成功的标志,通过郑和的航海活动,明朝的朝贡体系得以进一步延展,朝廷所垄断的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巅峰。
郑和的舰队满载丝绸、瓷器、药材、铜钱、铁器等物品,每到一处即向当地国王或部族首领宣读明朝皇帝诏谕,接受贡品并回赐物品。在完成“贡”与“赐”的程序后,贸易才是合法的,双方再进行官方贸易。这其实是通过海洋联系,将“朝贡”“互市”等制度直接在海外施行。
根据《明会典·朝贡》等史籍的记载,明朝海外贸易的物品多达200多种。郑和舰队所带的都是稀缺品、奢侈品,受到当地的广泛欢迎。据埃及马木留克王朝时期的马格里兹《道程志》记载,当苏丹及麦加贵族听闻郑和舰队中有两艘船停留在也门时,苏丹下令邀请支那戎克(中国)人来航,并要求殷勤地接待他们[14]。
郑和的舰队还担负着建构并维护明朝所主导的海洋秩序的任务。郑和舰队有2万多人,大船200多艘,其中长44丈的宝船有62艘,是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巨无霸般的海上力量[15]。郑和舰队沿着航线扫荡各种阻碍势力。比如,郑和俘获海盗首领陈祖义、擒获劫掠往来贡使的锡兰山国王。同时,为了维系航线沿岸的和平,郑和还积极仲裁各国内部争端。比如,处置爪哇西王与东王间的军事冲突,调解暹罗与占城两国之间的冲突等。明朝以郑和的军事、政治活动为依托在南海推行积极的和平政策,受到沿岸国家的广泛欢迎,据不完全统计,曾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随着郑和的舰队亲自到明朝京师朝贡。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更是有16国使者共1 200人赴明朝朝贡。明朝因郑和下西洋而声威达到顶峰[16]。
所谓“下西洋”,特指出马六甲海峡后,进入印度洋[17]。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以海洋为纽带的贸易区主要有北海贸易区、地中海贸易区、西洋(印度洋)贸易区、东洋(南海、东海)贸易区,它们之间相对独立,郑和下西洋首先将西洋、东洋连为一体。正是在东洋、西洋整合为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贸易区之后,位于两大贸易区之间、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才成为航线的“咽喉”。郑和七次下西洋,都以满剌加为起点。由此,以满剌加为枢纽,形成联通东洋、西洋的国际贸易市场[18]。
明朝积极的航海行动激发了印度洋沿岸强国对海洋战略布局的谋划。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苏丹巴鲁士贝(1422—1438年在位)为增加从转口贸易税而来的财政收入,积极招徕明朝商船与印度商船。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可汗沙哈鲁于(1404—1447年在位)以忽鲁谟斯为中心,积极推行在印度洋的贸易政策[14]。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前,明朝的海洋战略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海洋贸易格局。
然而,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明前期建构的与国家秩序密切相关的海洋政策遭到了挑战。一方面,有贡期、贡使人数、船只数限制的明朝官方贸易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贸易双方的实际需要,高昂的海外贸易利润也刺激了走私贸易的盛行,航线的繁忙还滋生了以劫掠为生的海盗势力。另一方面,随着朝廷主导的大规模航海活动的结束,明朝越来越无力维系其所建构的海洋秩序。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欧洲人开辟了从欧洲通往印度的航路,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印度果阿。随即,葡萄牙人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逆向从西洋往东洋扩张,并于正德六年(1511年)攻占满剌加,驱逐满剌加国王。葡萄牙占领西洋、东洋的交通枢纽满剌加,对明朝朝贡贸易体系的破坏甚为严重,终致明朝的海路被截断。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舰队4艘军舰抵达广东屯门,杀掠居民,筑室立寨,要求朝觐皇帝。此时,朝廷已经接到满剌加国王的告难、求援奏章,知晓满剌加已经被葡萄牙人占据。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礼部奏请处置佛郎机(葡萄牙)“侵夺邻国,扰害地方”的罪责,兵部议请敕责佛郎机,令归满剌加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后明世宗皆准奏并驱逐佛郎机使臣。这一事件导致明朝更加严格执行朝贡贸易的程序,凡是不符合勘合者、非期而至者,皆不准其朝贡贸易[19]。其结果是使官方贸易通道趋于狭窄,通过官方渠道不易得的情形促使走私贸易趋于繁盛。而葡萄牙人加入倭寇的行列,则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使得明廷意识到海禁既无法禁止海外贸易,也无法禁止倭寇。于是,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放海禁,民间商船“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参见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400》,中华书局1962年版,4332页。这标志着明朝海洋政策的大转折[20]。
由于放弃了自己一手建立的海洋秩序之治理权,故在应对西方殖民者东来方面,明朝采用的是“以夷制夷”的方略,其着眼点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行贿守澳官王绰,经王绰代为申请、海道副使汪柏批准,葡萄牙人得以留居澳门。明神宗万历初年,葡萄牙所献贿金转为地租银,从制度层面确认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租赁居住性质。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在澳门北面设关,置官防守。万历十年(1582年),两广总督陈瑞召见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领袖,葡萄牙人表示愿为明朝皇帝顺民、接受明朝的管理,陈瑞代表朝廷表示允许他们留居澳门[21]。
当与葡萄牙间的商贸问题逐步获得解决的同时,西班牙人也来到明朝传统的朝贡贸易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此后,依赖中国商人提供的大量商品,西班牙建立起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的贸易网络。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西班牙人试图以葡萄牙人留居澳门为例,闯入广东。但澳门人不允许西班牙人进入。随后到来的是荷兰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2艘荷兰军舰来澳门活动受阻,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联合英国进攻澳门,又为葡萄牙人击败[22]。
西班牙、荷兰对华通商的失败,使得澳门联通中西的地位更加重要。后来居上的海上霸主英国采取了通过葡萄牙人与明朝通商的策略。崇祯九年(1636年),英国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船队来到澳门。但是葡萄牙人担心英国人夺走生意,故不予接纳。英国舰队又直接闯入广州虎门炮台,与守军发生战事。后来,明朝两广总督张镜心派遣海防同知到澳门,敦促葡萄牙人立即驱逐英国人[23]。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西欧殖民者沿着西洋通往东洋的航线来到东方,占据了这个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港口——澳门,并以国家力量推行贸易与殖民。在这一过程中,明朝虽然利用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垄断经营权,促使其与后继而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争斗,“以夷制夷”式的维系海疆策略获得一定的成功;但因其国家力量退缩到近海及大陆上,丧失了郑和下西洋所建构的朝贡贸易网络体系的治理权,使往来东、西洋的华商也因此饱受西欧殖民者劫掠之害。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历史命运
“一带一路”对于古代中国而言,不仅仅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交通道路,其作用也不止于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之于古代中国内外秩序之建立关系极大。如果从时间线索来看,古代中国的不同时段对“一带”与“一路”各有侧重。汉唐时期重西北的中亚地区,宋明时期重东南的海上秩序。汉唐王朝志在建构囊括塞内农耕区与塞北游牧区的大一统,中亚因与蒙古高原同属一个历史空间,在族群政治上具有密切的联动性,常常作为游牧地区统治权的局部问题区域出现,因此被汉唐王朝纳入大一统的步骤中。汉武帝以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为战略支持,隋唐追求在中亚树立最高统治权(“圣人可汗”)、建构完善的统治体系,莫不着眼于此。相应地,中亚问题的解决常常伴随着蒙古高原问题的解决。故而,成功地在中亚建立统治权或保持影响力,是汉唐大一统得以建构的重要原因,也是汉唐长治久安、得以实现盛世的重要原因。
中唐以后,中亚经历了伊斯兰化、蒙古化、俄罗斯化的历程,中原王朝的发展重心转向东南,尤其是南宋时期中国完成经济重心南移,海上商路进入繁盛期,汉人的经济活动也日益转向开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并移民东南亚。与汉唐经略中亚主要依靠国家力量不同,开发华南与东南亚,主要是汉族移民自发进行,待当地汉人社会建立以后,国家再跟进建立行政区划。可以想见的是,倘若没有西方殖民者东来,古代中国的国家边境或许会沿着汉人移民的行迹深入东南亚地区。
明代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将海洋活动整合到国家秩序中去。明朝自朱元璋立国便立下不以军事征服东北亚、东南亚海上诸国的国策。朱元璋推行禁海政策,固然有应对倭寇侵扰的现实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想由朝廷垄断获利丰厚的海外贸易,并以此借助海外各国对明朝的经济依赖,以交易权为手段,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进而将经济权益扩大为政治权力,羁縻海外诸国。故而,明朝初期定下的海洋政策与明朝天下秩序的建构密切相联。郑和下西洋即是将“朝贡”“互市”等制度直接在海外施行,设立朝贡贸易的网络,并以航海军事活动维系海上秩序,其结果是促使南海贸易区与印度洋贸易区实现整合,改变了业已存在的海洋贸易圈格局。
在16世纪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明世宗,面对先人一手创立的朝贡贸易网络,僵化地固守明初有特殊时代内涵的海禁政策、坚持官方贸易,却又放弃对朝贡贸易网络的治理权,同时无视民间海外贸易发展的不可阻挡之势,最终造成了中国在海洋竞争时代的被动。这不仅为倭寇之患提供了制度土壤,而且在应对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上显得被动。西方殖民者鸠占鹊巢式地将朝贡贸易网络纳为己用,为其全球殖民体系服务。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虽然占据了原来明朝朝贡国的领土,但是在明朝朝贡贸易网络中并没有西欧各国的位置,因而西欧各国与明朝的官方贸易无例可循。明朝对朝贡贸易有着细致的规定,涉及贡期、贡船数、贡品种类等诸多方面,并对暹罗、占城、满剌加、爪哇等15国颁发勘合文册,设置市舶提举司管理[24]。因此,明朝所允许的合法贸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西人东来后,在原本存在的朝贡贸易数量之外,又叠加了西欧殖民国家全球贸易网络的东方贸易量,因而明朝官方贸易的渠道变得相对狭小。在海外贸易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明初所设置的海外贸易配额与16世纪后的海外对华贸易需求之间存在着很大落差[25]。西欧殖民者为追逐利益,积极推动对华贸易,除了在初相接触时伪装成朝贡国而进入原先的朝贡贸易网络之外,更多的则是仗恃武力走私贸易、乃至夺地杀人,葡萄牙人加入倭寇行列,西班牙、荷兰、英国进犯广东、福建、台湾,皆是显例。西方殖民者的行径不仅扰乱东、西洋的海上贸易秩序,而且严重侵害中国的权益,故而中国与西方的初次接触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明朝虽然利用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垄断经营权,促使其与后继而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争斗,“以夷制夷”式地维系海疆并获得一定成功,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明朝的国力在西方之上。然而两百年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此类矛盾仍然存在,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国力的上升,同样是以战争的形式解决矛盾,这次的结果却是中国失败,从而被迫纳入西方的全球体系。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命运其实早在16世纪放弃维系海上秩序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1]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J].敦煌学辑刊,2015,(2).
[2]赵立人.汉代以前的对外贸易[J].国际经贸探索,1985,(2).
[3]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J].潘孟陶,译.考古学报,1957,(3).
[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郭物.欧亚草原考古研究概述[J].西域研究,2002,(1).
[6]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考古学报,2002,(4).
[7]奔骥.“单于和亲”瓦当小释[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5).
[8]扎德涅普罗夫斯基.中亚费尔干纳出土的汉式镜[J].白云翔,译.考古与文物,1998,(3).
[9]余太山. Αλχονο钱币和嚈哒的族属[J].中国史研究,2011,(1).
[10]赵云旗.论隋与突厥关系的发展进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
[11]薛宗正.庭州、北庭建置新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1).
[12]薛宗正.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4).
[13]万明.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J].学术月刊,1995,(3).
[14]郑家馨.郑和下西洋时代西亚形势及与中国的关系[J].西亚非洲,2005,(2).
[15]苏松柏.郑和出使宝船刍议[J].中国史研究,1985,(4).
[16]陈尚胜.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17]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J].南洋问题研究,2004,(4).
[18]万明.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7).
[19]胡代聪.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J].历史研究,1959,(3).
[20]张钰梅.略论隆庆时期的改革[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3).
[21]黄启臣.明至清前期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J].中国史研究,1993,(1).
[22]朱亚非.明末闽台沿海局势与明政府之对策[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3).
[23]姜秉正.16—19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争夺[J].人文杂志,1992,(3).
[24]和洪勇. 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J].云南社会科学,2003,(1).
[25]刘军. 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1368—1840)[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61-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