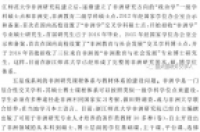根据最近的民调,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的大赢家将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讨厌欧洲联盟,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荷兰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和英国的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尽管欧洲右翼怀疑派可能无法赢得多数席位,但其汇总后的力量将给欧洲的统一制造严重掣肘。为何这一带着如此高的的期望始自二战后的工程会遭遇如此巨大的抵制?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成功不仅来自对欧盟的不满,也来自对自由派/左翼精英不满情绪的激增,后者被指为许多忧患的原因:移民问题、遭受挤压的经济、伊斯兰极端主义,当然还有被指主宰布鲁塞尔的“欧洲官僚体系”(Eurocracy)。正如美国的茶党(Tea Party)选民,一些欧洲人表示他们的国家已经从他们手上被夺走了。
面对着日益被大公司和身份不明的国际官僚所统治的世界,人们油然感受到一种政治无助感。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其宣称,如果我们能够再次主宰自己的地盘,一切都必然会变得更好。
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对欧洲机构的信心,还包括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自由派/左翼共识。1945年后,基督教和社会民主党有一个共同理想——和平、统一的欧洲,欧洲大陆团结论——对经济平等、福利国家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承诺——逐渐取代了民族主义。
这一意识形态堡垒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严重削弱,苏联帝国的解体不但让社会主义万劫不复,也让任何形式的集体理想主义成为明日黄花。新自由主义开始填补真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移民——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各大城市定居,导致了主流政党无力充分反应的社会冲突。
对种族主义或“仇外”的警告在经济衰落、不时爆发恐怖主义的氛围下不再被当回事。民粹主义煽动者趁机大行其道——他们承诺捍卫西方文明、抵抗伊斯兰教、与“布鲁塞尔”做斗争、从左派精英手中“夺回”祖国。
但这一反应根本不能让欧洲兴旺。要想与其他大陆崛起的势力竞争,共同的欧洲外交和防务政策显得日益重要。而共同货币——不管其概念如何漏洞百出——需要共同的金融机构,而若欧洲无法重新获得团结,就不可能建立和维持共同金融机构。
问题在于怎么办?比如,怎样才能说服相对较富的北欧人,特别是德国人,在危机期间,他们的税金应该用来帮助南欧人?
不幸的是,泛国家运动在培养共同归属感方面记录并不好。他们要么乱得一团糟(泛阿拉伯主义),要么太危险(泛日耳曼主义),要么既乱又危险(泛亚洲主义)。
泛欧洲机构的创始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如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让·莫内(Jean Monnet)。泛欧洲主义与天主教的渊源比新教更深,因为传统上他们在罗马教廷寻找归属感。罗马教廷通常代表着欧洲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1957年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但这不可能成为欧洲模式,欧洲公民几乎包括所有信仰的皈依者,此外还有大量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欲激发的前苏联帝国式的种族团结显然也不是欧洲的答案。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在二十世纪成了有毒政治战略,导致了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从这一后果可以感受到普京的做法有多么危险。无论如何,欧洲人从未在种族意义上统一过,今后也不会。
一些欧洲领导人,如前比利时首先盖伊·沃尔霍夫斯塔特(Guy Verhofstadt),梦想建立一个欧洲文化共同体。沃尔霍夫斯塔特说他爱法国葡萄酒、德国歌剧和英国和意大利文学。所有这些都有其吸引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们都不足以在政治或经济上统一欧洲。
因此,唯一剩下的可行之道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契约。欧洲公民不应该被诱惑放弃一定程度的宗教、文化或种族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他们也不应该被要求贡献出部分税收帮助其他不热爱和尊重欧洲国旗和国歌的国家。他们应该被说服,心甘情愿地做这些事。
国家领导人必须告诉人民,一些问题只有泛国家机构才能解决。他们能说服人民吗?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启蒙运动争论: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基于开明自利的社会契约论与大卫·休谟的“文化偏见是社会最重要粘合剂”说之争。
我支持前者。但历史表明也许后者更为有力。历史还表明,传统常常会被发明出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直是欧洲统一的问题:总有一些政治和官僚精英在铤而走险。普通人的观点很少得到关注。而如今,民粹主义正在从中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