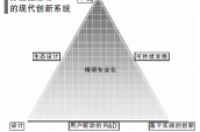
创新无疑是推动经济社会结构性转型的最原始动力。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后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发重视知识和创新在重塑地方经济、维持综合竞争力中发挥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并借此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欧盟的“精明专业化政策”(Smart Specialization),即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什么是精明专业化
最初,“精明专业化”由欧盟“知识驱动增长”(Knowledge for Growth, K4G)专家小组Foray等人于2009年提出,是一个面向区域创新的政策概念。经欧盟委员会研究商讨,2011年6月,该概念正式成为一项针对欧盟所有28个成员国的政策方案,即“面向精明专业化的研究和创新战略”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for Smart Specialization,RIS3)。
一方面,该政策致力于缩小自1995年以来欧美之间在创新和生产率上的差距,并应对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该政策也是对强调“精明”(Smart)、“可持续”(Sustainable) 和“包容性”(Inclusive) 增长的“欧盟2020战略”(Europe 2020 strategy) 和致力于缩小欧盟内部区域经济差异的 “欧洲融合政策”(EU cohesion policy)的一种延伸和细化。
“精明专业化政策”主要包含三层内容:一是鼓励区域进行事先的(ex-ante)、基于本地条件(特有的产业优势)的创新潜力评估;二是鼓励多方参与(政府、企业、大学及其他利益群体等)区域政策制定过程;三是欧盟根据地方上报的预先方案,有针对性地进行项目资助,其资助重点在于帮助申请区内的知识资源在产业间(内)得以顺利传播和重组,以此培育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推广市场。
该政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性指导方针:即不论何种类型的区域,不管其现有产业基础的强弱和科技含量的高低,均应致力于以下四个目标:
1. 发展一个具有地方性的面向增长的目标 (developing a vision for growth);
2. 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 (identifying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3. 选择战略性的优先资助产业 (selecting strategic industrial priorities);
4. 推行精明政策和行动 (making use of smart policies and actions);
“精明专业化政策”的“精明”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化的政策,而是一个基于本地实际条件(place-based)、自下而上的概念性方案,重在引导处于欧盟框架下的地方,科学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创新发展之路。
在现实的政策执行中,欧盟强调的是预先的政策规划,即由地方(作者注:这里的“地方”是指“欧盟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下的NUTS第三级行政区,大体类似中国的县级行政区)根据“精明专业化政策”方针,先拟定出富有地方特色、面向研究和创新的详细计划,而后自发申请加入该政策框架,以获得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资助。
具体操作程序为:首先,地方按照“精明专业化政策”的概念要求,对适应自身条件的创新和研究潜力,进行评估、分析和挖掘;其次,地方拟定具有扶持重点的优先政策,如列出优先扶持的产业、知识和技能等;最后,地方将具体的计划报送欧盟,经欧盟组织专家审议后,欧盟结构和投资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 ESIF),会根据相关计划的可行性进行有针对性的资助和扶持。这项资助的期限到2020年。
须指明的是,地方(NUTS3)所属的行政大区(NUTS2)和所在国家,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该申请地进行配套资金支持。所以,“精明专业化政策”没有统一的资金资助规模,欧盟需要衡量地方和地方所在成员国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资助。比如,芬兰和瑞典在国家层面对精明专业化政策计划比较支持,自身已拟定了资助地方的“精明专业化政策”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对地方的资助可能相对较少。
“精明专业化政策”的“专业化”,并非指“产业专业化”,而是强调依据地方特有的、专门的知识储备属性和经济结构特点,来推动地方知识溢出、互动和重组,促发潜在的创新行为。
“精明专业化政策”的目标,并非专门地追求创新——当然,“专门追求创新”本身就很不现实,创新必须与一系列条件联动。“精明专业化政策”,是为了推动“依赖地方特有情景”(place-specific context)的、能促进知识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多元化发展,即为“专门的多元化” (specialized diversification)。
更重要的是,尽管“精明专业化政策”属欧盟政策框架,但实际上,创新政策的制定权被完全下放于地方。该政策同时强调,在创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公共部门之间,应有充分互动和相互学习的过程。例如,政府应充分并广泛动员本土企业家、中小企业创业者、大学学者以及与本土产业相关的利益关系者等,以互动的方式共同探索和发现未来“产-学-研-政”合作的可能,充分理解符合本土制度、社会、文化土壤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和模式。
正如“精明专业化政策”的提出者Foray(2010)强调的那样,地方(创新)政策的制度过程,应该是一个“创业式的探索过程”(an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process), 应该是一个依赖区域内部多方参与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哪些资源可以得到利用和重组,从而得到创新成长的新空间。
要强调的是,虽然该政策概念的提出者,深知创新和技术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他们并不认为所有区域均应发展高科技产业,或要求所有区域都以科技创新来驱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是按照“精明专业化政策”的要求,来激励并启发欧盟成员国(各区域),理性找出适合自身地方经济发展条件的创新之道,帮助地方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创新源自哪里,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最大化孵化地方创新的可能性。
一方面,“精明专业化政策”在学术界总体得到了极高认可,因为该政策本身即源自学术圈。也有部分学者觉得,“精明专业化政策”概念对学术理论本身的贡献有限,这可能与推行时间短、有限的政策实践不足以反思理论有关。
另一方面,政策界对“精明专业化政策”理念的科学性比较支持,但对是否要参与以及参与后如何执行还有疑惑和顾虑。这是可能因为,部分成员国已拟定了相似的创新发展资助计划,担心新的欧盟政策会影响自身已有的政策实施节奏。
尽管在政策界有观望,也有批判,但可以明确的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一政策框架,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欧盟目前正在筹备精明专业化政策计划的地区(NUTS3)多达50余个。
精明专业化:理性科学的政策?
那么,欧盟到底为何推出这一政策框架?该政策是否与强调产学研互动的“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有冲突?是否为另一个“新瓶装旧酒式”的创新政策?它是否真的科学?
本文无法对以上所有问题给出彻底的解释,但首先可以从历史角度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将“精明专业化政策”本身理解为对以往欧盟“地方中性政策”(place neutral policy)的更正和改进。因为,无论“区域创新系统”,还是其他类似政策,均将区域有意无意看作平行的、无差异的个体,忽视地方特殊条件差异的客观存在。
比如,在大都市地区,由于组织机构比较密集,RIS的子系统相对较完备,如大学系统、产业系统、公共管理系统等,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容易组织,容易促发创新活动;而有些地方因缺乏大学等创新子系统,故而不易推行RIS政策。
而“精明专业化政策”则是一种更科学的、基于地方的指导性政策, 它不仅批判了过去忽视区域差异的“一刀切”(one-size-fits-all)政策,也回避了“挑选赢家式”(picking winners)的跨区政策学习(模仿照搬)手段。
其实,“精明专业化”和“区域创新系统”并不相互排斥。因为,以创新为导向的精明专业化政策并不反对“三螺旋式”(Triple Helix,即强调大学-产业-政府的互动)的创新发展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精明专业化政策”更尊重不同区域存在创新潜力差异的现实,并不一味鼓励所有地区均走“以研究引领技术突破式”的创新之路(research-based innovation)。而是尊重地方特有条件,允许创新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内容意义上的广泛性。
比如,精明专业化政策鼓励研究和创新的分离(即创新未必一定源自研究和知识创造),不局限于技术式的创新,面向新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制度/管理创新也可得到政策鼓励。可见,“精明专业化政策”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区域创新政策,是对创新形式和内容的一种理性解释,也是对以往“一刀切”政策失误(如区域创新系统和创新集群政策)的反思和改进。
由于受到欧洲最新的科学思维影响,特别是受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启发,从学术意义看,精明专业化政策具有极高的理论支撑。简单说,其理论背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 嵌入性(embeddedness),即认为有效的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基于地方特有条件,因地制宜。
2) 探索过程(a recovery process), 即强调创新政策的制定过程应依赖于一个多方参与的集体行为, 该过程可以帮助判读,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进行重组并开发运用于市场。许多人相信,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过程,甚至超越了创新本身的意义,因为该过程可将潜在的或以往不被认可的地方资源和潜力开发出来,从中可能产生新的增长点。
3) 关联性(relatedness),即突出“相关多样性”(related variety) 是地方探索过程中应遵循的根本逻辑。Boschma等人认为,产业创新的特征是新企业、新技术和新产业诞生,新产业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有密切技术联系(technologically related)的地方现有产业基础之上演化而来。“精明专业化政策”对这一点的认可,有助于相关人员在探索过程中,理性判读未来最可能出现哪些产业,以及应通过何种方式培育该产业(如促进技术相关企业互动和知识溢出)。正如 Foray所说:“精明专业化的目的是,在充分理解和利用本地现有生产结构和经济资产的基础上,助推一些新的潜在的产业创新系统的诞生和成长,以此逐步改善区域创新生态环境和经济表现。”
由此可见,精明专业化政策是一项有科学理论支撑的区域创新政策,有一定指导意义。
这里仍需强调,尽管精明专业化政策是一个以创新为最终导向的政策指导框架,但并非要求所有区域发展单一的STI(Science-Technology-Innovation)创新模式,即“从科学和技术到创新”。而是充分考虑经济基础的空间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并通过政策规范的方式,来指导其运用根植于地方的知识、研究和技术网络,来优先推动“可能的”创新活动,以此逐步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
例如,北欧地区基于实践而非基于研究的创新模式,即注重企业和用户的互动学习,以用户需求为目的,通过用户参与的产品设计和改进的过程,来推动创新,这种“从实践/运用/互动到创新”的DUI模式(Doing-Using-Interacting),与传统的STI的理念不大相同,却能在“精明专业化政策”的框架下得到有力的资助。
现实中的政策执行
截至2014年,已有14个欧盟成员国、共计150多个地区加入了RIS3政策平台。那么,地方参与者如何解读该框架?这项框架是否帮助参与者明确了未来区域创新发展的方向?这项政策在实际中是否被有效执行?在此,笔者专门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正反案例,试图说明该政策在地方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问题。
案例1: “精明专业化政策”在北欧行之有效——以芬兰拉赫蒂为例
北欧国家和地区常被学者视为研究区域创新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这得益于其政府机构透明高效、富于合作精神,也与其较早重视创新驱动区域发展的各种公共政策息息相关。过去十年间,北欧国家对创新环境的培育、对大学的投入,以及对新型市场的开发,在强度、范围和方式上,均走在欧洲前列。各种区域创新政策在北欧地区广泛实施,预先为精明专业化政策顺利推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深入的区域潜力分析。既有的区域创新政策十分注重对本地资源的挖掘和评价过程,不论各种区域集群战略、创新发展战略,还是针对创新和研究发展的投资项目,均是如此。不仅传统的SWOT分析(即优势、弱势、机会和威胁分析)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区域创新潜力分析,不同区域(国家)之间以开放合作的方式参与区域分析亦被重视。地方决策者十分提倡外部专家参与,以克服区域自身对本地的认知路径依赖和局限性。比如,丹麦和瑞典众多区域广泛建立了相互学习创新经验的正式(也含非正式)合作平台。平台首先推行的就是鼓励区外同行评议(external peer review)式的区域潜力分析过程,即不同区域的决策者和业内同行共同分析和挖掘特定区域的创新潜力。同时,北欧的区域潜力分析并非局限于“聚焦本地”,而是将地方放在一个跨区竞合的背景之下,明确特定区域在国家乃至全球中的比较优势,如分析地区相关产业在国家(际)创新生产网络中的所处地位,本地产业的市场容量和动态等。
2. 广泛的“三螺旋”产学政合作传统。北欧有较强的鼓励多方参与的区域创新合作传统。有不少北欧国家,早在2007年,就要求地方积极参与欧盟区域合作创新的“结构资助项目”(Structural Funds Programme, 2007-2013)。具体的政策项目有瑞典的三螺旋合作(VINNVAXT)项目,丹麦的增长论坛(Growth Fora),以及挪威的区域研究基金(Regional Research Funds),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政策帮助北欧各区域建立起良好的区域内(间)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传统,为今后实施精明专业化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对“创新”的开放性定义。传统的创新定义,大多聚焦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式的技术突破,这使许多创新政策制定者过分强调技术创新和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创新)投入,缺乏对创新本身的多元化理解。而在北欧地区,只要是有利于促进市场进步和增加劳动力就业的行为,均可视为创新。相比以往“以知识促创新”的观点,北欧人更注重“基于实践”(practice-based)的DUI式创新,包含用户参与(驱动)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公共服务创新等。这种广泛的共识,有利于区域更好地发现属于自身的创新潜力,开拓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视野。
基于以上三点,本文以芬兰拉赫蒂(Lahti)地区为例子,进一步说明“精明专业化政策”在北欧较成功的秘诀。
在上世纪90年代,拉赫蒂还是一个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严重缺乏创新活动的地区。过分面向传统产业的经济结构、缺乏大学等知识创造系统,使拉赫蒂一直处在芬兰区域综合竞争力的下游水平。而今,这个曾经“失落”的工业地区,已成为芬兰著名的创新之都,特别是在绿色清洁技术,设计和市场实践创新方面,已走在欧洲前列。
它的转型始于地方政府对拉赫蒂潜在优势的科学理解,以及对大学的重视。尽管拉赫蒂有明显的创新劣势(如没有大学、低R&D活动),但决策者反而将这些劣势视为一种机会,认为这种区域劣势反而有利于开创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比如,该地区1999年建立了以环境管理和设计为特色的拉赫蒂应用技术大学; 在充分理解产学研和跨区合作重要性的基础上,推动拉赫蒂与芬兰四所著名大学(赫尔辛基大学、阿尔托大学、坦佩雷理工大学和拉彭兰塔理工大学)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基于本地的创新项目。
这些项目充分考虑拉赫蒂自身条件,并非以研究为导向的技术创新,而是趋于改善地区生活质量和民众福利的“用户导向式创新”(user-driven innovation)。通过与这些大学相关部门紧密合作,政府和大学在基于市场实践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发展面向低碳生活和绿色建筑的环境技术,以及工业艺术设计等产业。
选择环境技术产业,是希望借助这四所芬兰顶级大学的相关雄厚科研能力。通过拉赫蒂政府的广泛合作,这四所大学在该地创立了一个基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联合研究中心。相比以往“服务于企业”的理念,拉赫蒂环境产业最初就定位于满足终端用户的需求,帮助普通人解决生活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如怎样节约能源、产生更少的污染物等。这使相关的设计产业得以蓬勃发展。
在这一基础上,拉赫蒂有针对性地在2009年运用了“精明专业化政策”。根据该政策框架,拉赫蒂制定了富有本地特色的“竞争力和商业战略”(Competitiveness and Business Strategy 2009-2015)。该地还组织了区内外专家参与的同行评议,以及以“企业家-政府人员-大学教授-利益相关者-用户”为核心的“区域优势再次探索过程”,从中确定了具体优先发展战略——即通过针对性的R&D投资和开放合作式创新来推动“环境技术、设计和用户体验”三位一体的现代创新生态系统 (见图)。
“精明专业化政策”的资助,被拉赫蒂当局重点用于两个领域,一是市场(用户)需求和趋势研究,以使创新产品能快速应用于市场。其中近500万欧元的项目,被投放到工业设计产业,这些资金用于设立专门面向客户需求的研究和创新活动(R&D),如鼓励用户参与的互动式交流,以此精确改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部分钱还用于鼓励大学参与并推动基于用户的实践创新,如拉彭兰塔理工大学在拉赫蒂启动了一个创新小组,通过和用户一起实践和体验,对工业设计产品的环境效益进行公共分析,以此推动“生态设计”产业,并与该大学的环境研究互补。
二是商业化模式的创新,即促进新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手段、过程和载体,以此加速新知识/技术普及的进度。拉赫蒂将大部分“精明专业化政策”的资金用于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现代创新生态系统,企业、大学和政府视客户和市场为创新驱动的主力,资金更多地扶持面向实践而非单纯研究的创新创意活动。同时,不光是设计产业,基于实践的相关产业,均面向环境考虑设计和创新,形成一种互助式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借助这种基于实践、面向市场的创新投资,拉赫蒂极大提升了地区竞争力和影响力,成为自“精明专业化政策”施行以来芬兰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实施不力的案例
当然,“精明专业化政策”并非区域创新的“万灵药”。截至目前,该政策实施过程中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里简单介绍来自英国和西班牙的两个典型案例。
案例2:依赖过往“创新集群”路径的英国威尔士(Welsh, UK)
威尔士是英国典型的老工业区,自1999年起就已成为欧盟经济扶持的重要对象。2002年,威尔士邀请集群(cluster)概念鼻祖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为其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战略指导。2005年,一系列针对产业部门(sector-based)的产业集群政策应运而生。在强烈的“集群”政策思维影响下,威尔士的创新政策也有强烈的集群色彩,如2010年威尔士议会政府制定的“经济更新计划”(Economic Renewal Program),其扶持重点仍是如何帮助现有产业集群提升创新能力。
一直以来,因为对“集群”概念的熟悉和推崇,威尔士政府的创新决策者,把“精明专业化政策”解读成另一种“创新集群政策”。由于本地制度和已有政策过多聚焦于以往的部门创新政策,决策者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在制定精明专业化政策时,简单将原有的“创新集群政策”纳入“精明专业化政策”计划中,缺乏多方真正参与的“探索过程”。
另一方面,威尔士长期依赖于传统(煤炭钢铁等)产业,缺乏其他产业资源和可能的创新要素。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先前筛选出来的“集群”就是威尔士最好的和唯一的发展方向。对现有本地创新资源匮乏的过分强调,降低了地方政策制定者探索新的创新潜力的动机。
最终,“精明专业化政策”在威尔士被解读成一种事后(ex-post)的政策,即在原来地方现有的政策结构上做“乘法”,加强原有的集群政策。
尽管该地获得了面向原有产业集群的创新资助,但根本上并未遵循“精明专业化政策”的意图和指导方向,只将其视为“申请-拿钱”的简单资助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威尔士自身放弃了重新评估本地创新资源和发现新的产业潜力的可能,人为降低了“精明专业化政策”在地的实际效用。
案例3: 受既有STI政策框架束缚的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Basque Country)
不同于“制度厚度”较薄的老工业区威尔士,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富裕自治区,不仅拥有良好的产业系统和大学公共设施,还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管辖权、各种面向创新的政策措施,以及比较密集且细化的政策制度单位。
然而,众多政策相互叠加的制度环境却给“精明专业化政策“在该地的具体实施带来阻力。许多官员在“精明专业化政策”正式推出之前,就提出巴斯克通过过去30年的创新扶持政策,已建立了类似精明专业化的战略框架。这种心态导致巴斯克政府在申请精明专业化政策资助之前,并未努力“探索”新的区域创新优势,而是在不改变本地原有管理和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将“精明专业化政策”刻意套用在本地已有的政策项目中,并冠以一个好听的项目名字——“科技和创新计划2015”(PCTI-2015)。
在该项目中,为满足“精明专业化政策”的要求,巴斯克地区确定了八大优先发展产业(生物科学、纳米科学、先进制造业、交通、数字技术、科学产业、健康产业和能源科技),但这些产业并不是经过专业的、广泛的探索过程精心筛选出的,而是在原有政策管理和组织架构上做了简单的“加法”。比如,在既有的158个科技创新组织(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科技园、研究中心和大学相关研究所等)的基础上,简单设立新的组织——增加了专门发展生物和纳米科学的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政策(Biobasque和Nanobasque);增设新的集群组织(CICs)和研究中心(BERCs); 在原来管理STI发展的部门(SPRI和EVE)上添加新的功能和任务等。这种“加法”不仅增加了科技创新组织管理的难度和复杂度,还将“精明专业化政策”按部就班安排在原来的STI 政策组织上,失去了该政策的本来意义。
虽然巴斯克和北欧相关地区一样,拥有良好的区域创新系统和产业基础,但其对待新政策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受制度因素的影响较大。
一方面,若面向STI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较厚,地区易陷入过于制度化(over- institutionalization)的陷阱,并产生一定的政治锁定(political lock-in)效应,使地方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精明专业化政策”时过分依赖过去的制度结构和利益,形成严重的“自增强式”(self-reinforcing)路径依赖,从而拒绝采取新的行动——因为可能损害现有的政策利益和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对创新内涵的理解较狭隘。这与过去巴斯克过分重视STI的科技创新,并具备众多基于相应政策建立的组织制度结构有关。他们普遍认为,创新必须依赖R&D, 依赖面向供应商的技术进步,或单纯认为创新仅是“企业或研究机构的事”,缺乏对面向终端用户需求创新的重视。这和北欧有明显差距。
巴斯克忽视了市场对创新的作用,同时也忽视了制度和管理创新对技术进步的反作用,使其本身可能有的创新潜力被埋没。这些原因综合起来,使巴斯克无法摆脱偏重STI政策的既定框架,不能寻找真正有潜力的创新空间,“精明专业化政策”在这里失去了实效。
结语和启示
总体而言,尽管“精明专业化”是较科学的创新政策,但多少面临着实施偏差等问题。
一个面向地方、尺度范围较大的政策框架,应避免一刀切;但无法回避“相对松散”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地方化,甚至被曲解误读。由此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普遍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欧洲。
英国威尔士和西班牙巴斯克的案例告诉我们,尽管“精明专业化政策”给出了有说服力的区域创新政策制订方案和过程,但该政策缺少了后续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这或许和政策出台时间较短有关,但更多地,是地方依据自身制度需求和原有政策架构去理解,在实践中产生了偏差。
这里列举的正反案例介绍,意在说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区域创新政策,特别是在跨国家、跨区域的大型框架内。这进一步说明,区域创新政策并非想推行就一定成功,正如“硅谷”无法在其他地方复制。
有效的宏观(区域)创新政策,其实是地方条件与政策相糅合的产物,这取决于地方如何根据自身条件合理解读政策。这种“配对”过程,表明上,可看作“新旧”政策的组合(互动)过程,但实质上,是依赖现有产业条件的地方制度,与政策组织架构的应对过程。比如,北欧各地区得以成功执行精明专业化政策,虽得益于过去(现在)政策制定者对创新的深入理解和广泛的政策扶持,但更在于地方(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上的优越性,如对跨区多点合作的重视,对超越理论的实践式创新的推崇,以及政府治理的先进性。
要指出的是,一些地方对该政策的错误解读,或与“精明专业化“的字面理解有关。一些欧盟地方官员以为,“专业化”是指产业的专业化。因为在区域发展的语境下,“专业化”往往被用以形容特定产业的技术(劳动力)专门化水平。而在“精明专业化政策”的解释中,其政策重点是通过创新来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而非“专门化”。政策名字和内容概念上的冲突和不明晰,产生误读空间,进而降低政策实施的效力。总之,该政策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相信欧盟在将来会付之于行动。
最后,笔者不否认好的区域创新政策应基于本地,因为地方的企业、政府和相关机构对本地最了解,知道如何利用本地资源营造创新可能。但同时,类似欧盟“精明专业化”这样更高层次的概念性政策纲领,其理念对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一是,其“基于地方”自下而上的弹性政策制定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让区域创新制定者趋于理性,可减少各种不符合本地实际条件、跟风式的创新扶持政策,如在一些明显缺乏人才资源的地方,建立各种名义的科技园区,专门发展IT/生物等所谓高科技产业。科技创新是区域发展的发动机,但未必适合所有区域,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定位应理性根植于地方自身的优势和潜力。
二是,它的“历史演化观”,可帮助地方政策者重视本地现有资产(如工业遗产)和经济要素资源,指导其在重新认识本地条件的基础上,发现并判定新产业诞生的可能路径和空间。这有利于地方政策制定者做出根植地方资源、文化背景、制度结构的创新政策,而非各种脱离本地历史背景、“空中楼阁式”的创新政策。
三是,它鼓励多方参与“创业式的探索过程”,让政策制定者明白,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并非局限于地方政府做出,而是需要本土企业家、学者、市民及其他社会机构人员广泛参与。地方政府可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和借鉴其他地区的做法,以选择适宜本地优先发展的产业,但更应注重基于“本地实践”的排他性过程,重视该过程可能产生的知识互动和合作,以及各种新奇(novelty)效应。当然,在本地人员探索的基础上,邀请第三方独立智囊团体参与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也有利于避免本土人员可能存在的思维上的“地方路径依赖”。
四是从国家层面,对区域创新给予理性解释。中央相关创新政策制定者,在给予地方自主宽松的创新路径选择的同时,也应给创新以多样化的解释和定义。应结合实际情况,在肯定技术创新重要性的同时,鼓励知识创新、管理创新、基于市场用户的产品创新等。创新不应只局限于高技术含量的活动,只要有利于改变或丰富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的活动,均应得到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