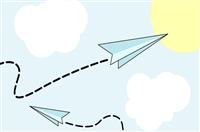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力量的消长引人注目,各种国际行为体围绕全球治理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在这场对未来世界格局具有深远影响的争夺战中,尽管传统大国仰仗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优越的国际地位和娴熟的国际规范掌控能力,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实力增强了的新兴大国在各种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地位也在稳步上升,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
新兴大国软实力偏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和影响力扩大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有关。
第一,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普遍放缓。过去几年,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世人印象深刻,但支撑这类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外条件具有特殊性和很大的偶然性,在相对大程度上也是不可复制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早在2011年,联合国在《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中,既肯定了中国、印度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优异表现,又不无忧虑地指出,由于面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升值、热钱流入等压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放缓的可能性。如果新兴大国不能很好地处理上述问题,特别是不能顺利和较快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速度放缓是必然的。上述判断已经为最近两年的一系列权威统计资料所确证。接下来的问题是,一旦新兴大国经济低速增长的时间过长,或者出现严重滞涨,它们崛起的势头肯定会放缓,某些国家崛起夭折也不是不可能。
第二,新兴大国的软实力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改观。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表明,国家行为体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应当是力量的整体性增长、地位和影响力的全方位提升,而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单方面增长,以及经济地位单方面提升和经济影响力的单方面扩大。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崛起特别是文化上的崛起,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强大软实力的支撑,一国经济崛起就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案例研究显示,新兴大国目前在软实力方面普遍较弱;即便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也是如此。不少欧美学者就认为,中国传播文化和价值观的努力并没有赢得它所期望的吸引力。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新兴大国都已程度不同地认识到自身软实力的缺陷,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受硬实力相对不足以及历史、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国家软实力偏弱的状况很难在短期内根本改观。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预计,有效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愿景与既有力量相对弱小的落差,将是新兴大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为了巩固已有收益,继续提升在全球治理主导权之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新兴大国应当立足新时代,展现大格局,寻找大智慧,并由此发展出更多和更为有效的手段、方式和途径,其中积极建立议题联盟就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方式。
所谓议题联盟,是指国际行为体在某一跨国议题上存在利益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并据此自愿形成的一种合作形式。这里的国际行为体既可以是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议题联盟是联盟(Alliance)的一种新形式。它与传统意义的联盟即政治或安全联盟既存在着某些相同点,比如,联盟成员可以是跨地区的、跨社会制度的、跨意识形态的、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也存在诸多不同点。
第一,议题联盟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低位政治,如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贸易与投资问题、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等,这些问题虽然攸关国家利益,但常常并非核心利益,因此围绕相关议题的博弈比较容易达成妥协。而传统的联盟主要涉及政治、安全等高位政治。对联盟问题有精深研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就曾将联盟 “界定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从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这本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的内容设置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笔下的“安全”(security)指的是传统安全,属于高位政治范畴;他所论及的联盟自然也就只能是传统的联盟了。奥利·霍尔斯蒂(Ole R. Holsti)、特伦斯·霍普曼(Terrence Hopmann)和约翰·沙利文(John D. Sullivan)等人的研究也属于传统安全。由于传统安全问题与国家核心利益的关联度极高,因此相关的国际合作不易达成。
第二,议题联盟一般不需要以正式的国际文件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尽管传统的联盟也存在某种非正式的关系,比如,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就写到:“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从来就没有正式的条约,但没有人质疑这两个国家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的水平。……同样,苏联和埃及之间直到1971年间也没有签订正式的条约,但之前显然是紧密的盟友关系。”但更多的或主要的是国家间的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是通过为联盟所有成员国共同认可且得到各国立法机构批准因而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而建立起来的。比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北大西洋公约》,东南亚国家联盟有《曼谷宣言》,等等。形成和维系传统的联盟关系通常需要很高的时间成本、行政成本和机会成本。而议题联盟基本上不需要正式的国际文件,它往往通过双边会谈、口头承诺甚至是实际行动等方式而达成,对联盟成员的约束力较低,也因此只需要很少的时间成本、行政成本和机会成本。
第三,建立议题联盟也需要成员间相互信任,但程度上总体偏低。信任对于联盟的形成和维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工具价值角度看,信任可以减少联盟成员对彼此投机行为的担忧,从而对相互关系的未来产生稳定预期。一般而言,传统的联盟的信任度都比较高,因而联盟的稳定性总体上都比较高,存续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比如,北约、日美同盟等传统联盟已经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短期内仍看不到解散的可能。比较而言,议题联盟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一般都不高,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瞬时信任。这种状况自然会影响到联盟的稳定性,因而这类联盟存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联盟形式可能发生转化
最后,还需要看到议题联盟存在着向传统的联盟形式转化的可能。议题联盟形成的前提在于其成员在特定议题上存在共同或相近的利益、持有共同或相近的理念。如果这种暂时性的共同或相近的利益进一步巩固或扩大、共同或相近的理念进一步强化和内化,议题联盟就有可能向传统的联盟形式转化,或者形成其他较为稳定的组织形式。但很多时候,某一议题联盟的成员在其他议题上的利益和理念可能不一致甚至完全对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原有的议题联盟成员之间往往会产生明显的分歧和尖锐的矛盾,甚至形成激烈的对抗。这方面已有先例可循。比如,在增加新兴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所占份额的问题上,巴西与中国存在诸多共同点;两国还同属金砖国家成员,在有关全球治理的很多领域存在利益交汇点;然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巴西却与传统大国美国的立场基本一致,两国还曾联手对中国施压。美国希望借此将巴西发展成为自己的新盟友,并使后者成为调节美国与南美国家之间关系的平衡力。巴西则希望减轻本国货币雷亚尔升值的压力,刺激经济增长,同时还希望能够获得美国对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发展所造成的复合相互依赖高度发展的今天,在全球治理的任务日益庞杂繁重而单一国家行为体的治理能力不时捉襟见肘的今天,尽管议题联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它仍然不失为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它可能也是新兴大国扩展国家力量的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