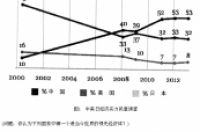
一、前言
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和焦点。在冷战时代,世界的重心和焦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世界的焦点是美国主导的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的八国集团。进入21世纪,当东亚四小龙所带来的亚洲奇迹处于乏力期时,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亚洲的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的地位在世界经济治理的舞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二十国集团迅速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危机之后的主要经济治理组织。而在二十国集团中,北美洲国家有三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南美洲只有两个(巴西、阿根廷),非洲和大洋洲各只有一个,欧洲有四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欧亚交界有两个(土耳其、俄罗斯),数量最多的是亚洲,共6个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印尼、沙特)。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最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仅次于美国。鉴于今年恰逢一战100周年,很多政策制定者、学者和研究机构都在讨论和对比一战前的欧洲和现在的亚洲,[1]这说明亚洲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亚洲的稳定和发展。
面对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发展,东亚国家在重新定位自己。中国最新的国家定位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日本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沉寂”之后,向世界发出“一个强大的日本回来了”的声音。[3]韩国提出了建设“新韩国”的设想。东南亚国家积极推进更加全面的东盟共同体建设,以此来增强外部竞争力和内部凝聚力。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重新思考如何与亚洲共处。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迅速调整了其在全球的战略重心。2009年,奥巴马总统宣称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4]之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5]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加深对亚洲事务的干预。美国重返亚太是与亚洲进行全方位的接触,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方面不断增强。在经济领域,TPP谈判迅速推进,美国商贸不断向新的市场开拓。[6]美国重返亚太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前的世界形势、亚洲态势和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尤其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和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不是全部针对中国的崛起,但毫无疑问,中国是美国需要战略应对的“重点中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发展好中美关系,如何搞好周边外交工作就成了新一届中国政府的重大外交挑战。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面对亚洲和世界的新情况、新趋势,正在积极审慎地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周边外交已经成为我国整体外交工作的核心,这一点在2013年10月份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得到了确认。本文的重点是讨论美国的轴辐式同盟体系如何引起东亚秩序失范,以及中国崛起如何消除秩序失范的问题,从而建设亚洲新秩序。建设亚洲新秩序困难重重,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中国执行更加灵活有效的亚洲地缘新战略。
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和介绍本文的研究视角。这一部分将重点介绍秩序失范的概念、原因和表现。在后续部分,本文将把地缘秩序失范理论应用到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分析之中。第三部分讨论东亚的秩序失范问题及美国的轴辐式同盟体系的负外部性。第四部分介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情况,以及解释为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法消除东亚秩序失范,也无法消除中国崛起在亚洲面临的问题。第五部分讨论中国的亚洲新战略。
二、地缘秩序失范理论
最近几年来,学者非常关注中美关系在亚洲层面上的发展。大多数文献围绕中美在亚洲的权力竞争展开,这背后打上了深深的大国权力政治的烙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在其著作《角逐霸权:中国、美国和双方的亚洲争霸》中直白地谈到:“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已经困在了一个静悄悄的但是不断增强的权力和影响之争,这不仅仅体现在亚洲,也体现在世界上。”[7]即使在一些对中美关系持相对乐观立场的学者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也需要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加强在亚洲的存在和干预。比如,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而美国需要“与北京持续进行一些合作接触的同时,在亚洲保持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并且在重大亚洲议题上保持非常高的影响力”。[8]我国学者对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关系上的研究思路与美国学者比较接近。例如,在孙哲主编的《亚太战略变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书中,对非洲事务、涉藏事务、经贸关系、东南亚事务、台湾军售等方面探讨了中美两国的权力博弈和战略竞争。[9]中美两国在亚洲的互动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外交的问题,也是一个多边外交的问题。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关系会不由自主地“外溢”到亚洲的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对亚洲的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虽然谈到了亚洲秩序的问题,但是很多学者没有对地区秩序本身的内涵和实质进行分析。因而,本文拟从地缘秩序失范的视角出发,来探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前景及其对亚洲的影响。
本文认为,亚洲地区出现的最大变化(或者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地区秩序失范。为此,我们将围绕亚洲秩序失范分析三个问题:什么是秩序失范?它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它的外在表现又是什么?
什么是秩序失范?失范这一术语最早在社会学中出现。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是最早系统研究失范的社会学家。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认为,失范是一种病态,它会影响社会分工和对不同社会功能间的合作造成伤害。[10]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失范就是“互动过程中结构性补充因素的缺失”。[11]在《纵容的外交》一书中,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贝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把失范这个概念系统地引入到国际政治中,他认为,当前是一个失范的国际体系。[12]本文把秩序失范引入到对中美关系和对亚洲的分析上,旨在说明,所谓地区秩序失范,是指一个地区的各组成部分(主要是国家)不能够协调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不能够建立起稳定的互动机制,不能够对新秩序的建设形成共识。
地区秩序失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造成一个地区秩序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讲,可以分为地区内部的原因和地区外部的原因。
地区内部的原因主要包括:内部权力出现重新分配但是并未获得承认;内部领导权分散化;破坏性行为缺乏惩罚机制。二战前的欧洲就是处于秩序失范的状态。比如,在二战爆发前,纳粹德国采取了很多破坏性的行为(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扩军备战、吞并捷克等国等),但是这些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地区外部的原因主要是指外部强国对地区事务的干涉。一个地区内部的事务应该交由该地区国家自主处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地区外强国会因为诸多原因(均势的需要、侵略的需要、和平的需要等等),插手干涉其他地区内部的事务。这种干涉在很多时候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秩序失范。需要说明的是,秩序失范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的发生,战争是消除秩序失范、建立新秩序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用和平的手段也可以消除秩序失范。以欧洲为例,二战战败之后的德国(主要是西德)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很快超越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受制于战败国的身份,重新崛起后的德国尽管实力强于很多国家,但是在国际政治层面,其大国地位并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面对这个问题,欧洲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欧洲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共同市场-欧洲共同体-欧盟),吸纳德国加入欧洲一体化组织,鼓励德国在欧洲事务中承担起大国责任。
地区秩序失范会有什么表现?总体来说,一个地区如果处于秩序失范的状态,那么合作将很难实现,冲突行为会增加,而原有的冲突解决机制可能无法发挥效用,新的冲突解决机制又很难建立起来。日益加剧的冲突状态会进一步损害地区的内部凝聚力,导致“双输”或者“多输”的局面出现。例如,一战前的欧洲内部矛盾重重,原有的冲突解决机制(大国外交、均势机制等等)都无法发挥作用,而新的冲突解决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导致“多输”局面在欧洲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地区处于秩序失范的状态时,地区内部的官方一轨外交、非官方二轨和三轨外交并不必然减少。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外交努力往往收效甚微,并不能有效推动地区合作的开展。
在意识形态和价值领域,秩序失范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僵化和价值失衡。以1948-1982年间的中东为例,这里曾经发生了5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地缘秩序失范的背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和价值失衡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都固守自己的宗教理念、战争逻辑、排他主义,意图以破坏和消灭对方作为自己生存的方式,而这显然与二战之后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和繁荣的思想潮流格格不入。
三、东亚秩序失范与美国的轴辐式同盟体系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重点介绍美国在亚洲的轴辐式同盟体系及其对东亚的影响。这一同盟体系对美国非常重要,很多学者认为它是美国在亚洲保持战略影响力的核心基石。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海外同盟体系是美国的一大优势。[13]本文的观点是,轴辐式同盟体系在亚洲同时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美国的轴辐式同盟体系在过去一段时间,维持了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它的正外部性。但是我们应该发现,美国所极力维持的是亚洲的旧秩序,是以维护美国利益和美国霸权为核心的旧秩序,而不是以维护亚洲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新秩序。这对于构建亚洲新秩序而言,该同盟体系主要会产生负外部性。亚洲地缘秩序失范的主要原因就来自于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负外部性。
第一,美国通过建立和加强亚太同盟体系,积极干预亚洲内部事务,这是亚洲秩序失范的外因。二战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几十年来,虽然东亚局势发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但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架构在总体上得到保持,并经受住了时间和事件的考验。[14]亚洲事务需要亚洲人做主,通过建立内部的合作机制和推进一体化建设,亚洲才能实现共赢,才能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但是美国基于维护自己霸权的需要,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干预亚洲内部事务。为了能够顺利和有效干预亚洲事务,美国所建立的同盟体系必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依附性体系。依附性的同盟体系对美国非常有利,但是却会造成亚洲的秩序失范。因为这使得亚洲内部的冲突解决机制和合作建立机制都被美国所牵制。换句话说,没有美国的积极推动和协调,亚洲内部的很多机制都无法正常运行。这自然会造成秩序失范的状态。
第二,美国及其盟国不承认亚洲内部权力的变化格局,不认可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具体来看,美国及其支配的亚太盟国(包括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先是抛出中国崩溃论,不承认中国的发展和实力增长。在中国崩溃论破产之后,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又提出中国威胁论,不仅不认可中国的领导权和对亚洲的贡献,反而极力抹黑中国,渲染中国威胁。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国家出现实力衰落也是现实,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出现变化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美国等国家极力以“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攻击中国,这必然会产生以下两方面的消极影响:其一,它使得中国难以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损害中国的大国威望。没有一个稳固的国际地位,没有一个坚实的大国威望,综合实力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受到“崛起焦虑症”的困扰,这不利于中国协调与处理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二,亚洲一些国家基于对形势的误判,往往会挑起矛盾和冲突,乘乱作为,从而加剧内部秩序失范的状态。
第三,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造成亚洲领导权日益分散化。美国在东亚的轴辐式同盟体系以双边安排为基础,这有利于加强美国对盟国的最大化控制,在亚太地区实现一种美式的“分而治之”,[15]而这种分而治之将导致即使在盟国之间都无法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联系。在整个亚洲内部,因为存在盟国与非盟国的区别,亚洲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很难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和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之间往往是处于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之中。由于地区大国之间都无法获得至高的领导权,地区组织往往会兴起并且代行一部分领导权,从而导致地区领导权更加分散化。这种领导权的“无序”状态非常不利于地区一体化的建设。在欧洲,欧盟的形成和发展是由法国和德国携手完成的,至今法德的领导权也是欧盟的核心支柱。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日本都是地区强国,但是双方都不享有绝对的领导权。这种情况反而给东盟发挥地区领导权提供了机会。目前来看,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大部分与东盟的推动(东盟10+3、东盟10+1、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有关。但是由地区小国组织的地区一体化如何发展,前景很难判断。目前来看,“小马拉大车”式的地区一体化已经达到极限,它在解决内部冲突方面也是乏善可陈。这些无疑会助长秩序失范的状态。
第四,美国的同盟体系导致破坏性行为得不到惩罚。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友,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至少是默许),两国在亚洲即使挑起事端也不担心遭受惩罚。目前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都不是中方首先挑起,而是由日本和菲律宾挑起的。这些争端严重损害了亚洲和平发展的秩序。但美国总是把责任推给中国,却对日本和菲律宾的破坏性行为不加约束。此外,美国对盟友与非盟友的双重标准也在扰乱亚洲的地区秩序。以汇率问题为例,美国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致使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产生。为此,美国多次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不然就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可是日本和韩国却在直接公开干预本国汇率。尤其是日本,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促使日元贬值,以此刺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日元贬值会对国际和亚洲地区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然而美国却从来也没有对日本的汇率操纵问题提出过质疑。
以上分析了美国在亚洲的轴辐式同盟体系如何导致亚洲的秩序失范。至于这种秩序失范在亚洲的主要表现,本文将在地缘空间、话语空间和价值空间三个维度上予以阐释。
1.在地缘空间,出现小国挑衅大国现象
2012年6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大小国家都要相互尊重,大国不能轻视和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16]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小国普遍被认为“它不能够主要通过运用其自身的力量来获致安全,为了实现自身的安全,它必须在基本上依赖于其他国家、制度、进程和发展的帮助”。[17]因此,在正常状态下,小国是不会侵犯和挑衅大国的。因为它既没有实力去这样做,并且这样做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是在秩序失范的状态下,小国就有可能去挑衅大国。目前在东亚,小国挑衅大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这种小国挑衅大国的行为在其他地区是非常少见的,尤其在地缘秩序维持得比较好的地区更是难以想象。这种小国挑衅大国的行为最后的情况往往是对小国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2.在话语空间,话语权丧失了流动性
话语权在国际政治中非常重要。话语权既是一种说话的“权利”(right),也是一种说话的“权力”(power)。[18]中共中央党校张忠君教授认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围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领域展开,也在社会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等软实力领域展开。无论是硬实力的竞争,还是软实力的竞争,争夺国际话语权在国际政治经济的角逐中日益具有重要的地位。”[19]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东亚的话语权却被牢牢地牵制住了。
在这里,中国的话语权被牵制的程度最深。中国的话语权在两个方面受到牵制。第一个方面是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上处于孤立状态。有学者评论道,当中国与西方围绕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国际话语权问题展开竞争时,总是被围堵、被孤立,处于被动守势,不得不常常以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特色”话语来抵挡某些国际强势话语的冲击。[20]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有些行为其他国家做就是正常的,中国照做就是不正常的。例如,2013年中国宣布在东海海域设立防空识别区(ADIZ),但美国、韩国和日本均不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区,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没有根据,是挑战现状。同样的外交行为,为什么在日本和韩国就合理合法,而在中国就没有根据?在这背后,反映出我国的外交话语权是被他国所牵制。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在西沙群岛海域开展钻探活动受到越南干扰。对此,中国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表示,中国在打井问题上非常慎重,现在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其他一些国家打了这么多井,外界没讲什么,而中国打一口井,马上就有这么多“横加指责”。[21]美国的同盟体系一直强势垄断当前的东亚话语权,而其他国家却无法获得自己的话语权,这是东亚秩序失范在话语空间的主要表现。
3.在价值空间,单一价值取代多元价值
世界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中国历来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22]东亚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与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存在不同。东西方文明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甚至取代另一方。美国南加州大学康灿雄教授在其著作《西方到来之前的东亚:五百年的贸易和朝贡》中指出,在历史上,当西方还在互相争战的时候,东亚却维持了长达500多年的和平与发展。[23]这充分说明了东方文明的独特价值。但是在当前的东亚,美国极力推行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认为西方价值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价值。[24]美方还认为,东亚应该以西方价值为基础,全面改造自己的体制。
事实上,西方价值本身也有很多缺点。首先,西方的价值观没有完全解决西方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亚洲极力推行自由民主体制,但是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它的政治体制在国内饱受诟病。美国人民对华盛顿的两党政治非常不满,这在美国因为“党争”而导致政府关门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此外,美国的体制几十年来始终无法解决大量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问题和犯罪问题。其次,美式民主在亚洲的推行出现一定的“水土不服”。这一点在泰国民主乱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美式民主毫无是处,中国的体制全是优点。相反,中国和美国的体制都有缺点,亚洲其他国家的体制也有缺点。在合理的亚洲秩序范围内,各国本应相互借鉴,而不是用一种价值去否定和攻击另一种价值。但在当前亚洲秩序失范的状态下,单一价值压制和取代多元价值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例如,日本领导人安倍和麻生等人多次抛出“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等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概念,以此来攻击中国。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消除东亚秩序失范?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之际,新型大国关系出现在习近平华盛顿的演讲之中。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正式推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新思路,目的是为了解决老问题,是为了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25]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非常难以处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者,往往对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互动过程持悲观态度。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崛起国。以经济为例,在2013年,根据布隆伯格的报道,按照进出口总额计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26]在经济影响力方面,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有53%的美国人在2013年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美国将会再一次面对一个潜在的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大国政治到时候就会全面出现。[27]不管美国如何设想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开展传统的大国政治斗争。正是基于这个理念,中国表示支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对于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东亚意味着什么,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周方银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涉及中美相互定位的变化。中美对于各自在这一秩序中的未来定位能否形成较为一致的预期,特别是是否愿意接受对方在地区秩序中的相应地位,是新型大国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28]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大卫·兰普顿谈到,中美双方“应该管理好各自的第三方国家,,避免产生无谓的行为刺激对方”。[2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30]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开盛认为“东亚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场’”。[31]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仅仅是一种双边关系建设,对多边外交和地区形势也有影响。
正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溢出效应,所以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就能解决中国在亚洲的问题,消除亚洲的秩序失范。但是,我们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能消除亚洲的秩序失范,也无法解决中国在亚洲的困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尽管有非常强的积极意义,但是目前来看,它存在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可能消除东亚的秩序失范,更不会有助于解决中国崛起的烦恼。
1.最根本的原因是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中方的目的是试图探索出一条新的管理和发展大国关系的路径。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中方最基本的理解是三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32]而美国政界方面从来没有对如何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路径安排和政策要求。美国政界除了在外交上对中方有一定的回应之外,很多时候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内容模糊,不具有明确的现实操纵性。比如,美方不清楚“不冲突、不对抗”是在什么层次上的要求。在现实中,中美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和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冲突和不对抗到底指的是什么。另外,美方认为中方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造成了责任不对等分配,这是要求美国承担更多责任。[33]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经针对新型大国关系撰文说:“中国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来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然而美国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主要关切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令人不满意的”。[34]中国派驻亚太经合组织的王嵎生大使也表示,要想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搞好,球在美国人手里。[35]美国政界对这些表态的理解是,中方希望美国管理好自己的行为,而对自己却没有任何要求。由此来看,中美双方对如何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达成根本共识,这必然会导致两国合作面临诸多困难,战略互信亦很难增强。因此,亚洲的秩序失范不可能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来消除。
2.美方没有对中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表示出强烈兴趣的意愿
从历史上看,中方从未有任何关于中美关系的重大理念和概念得到美国的认同,并上升到外交层面。事实上,美国是率先开展了对中美关系未来形态的探索,因为美国希望一直牢牢把握主动权。但是当美国提出“G2”、“中美国”等倡议和概念时,中方由于种种原因未予以正面肯定和积极回应。同理,面对中国提出的新概念,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自然没有动力去积极回应。我国学者张家栋和金新认为,美国视新型大国关系为一般性概念,并不想因此而约束自身行为,更不想以此来与中国达成某种战略“大交易”。[36]正是因为美国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一般性概念,不给予足够的重视,美国的外交行为和策略多次出现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相违背的举动。比如,美国频频在南海问题上和钓鱼岛问题上选边站队,不负责任地维护菲律宾和日本的领土要求。美国的这些行为进一步激化了东亚的内部矛盾,更深一步造成了东亚的秩序失范。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改变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
上文已经指出,美国在亚洲的轴辐式同盟体系会产生负外部性,这是造成东亚秩序失范的主要根源。当前中美两国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话和沟通,很少涉及美国的亚太盟国。也就是说,中美双方是在双边外交的层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并没有意图把它扩展到多边的层面。所以即使中美双方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也无法解决轴辐式同盟体系的负外部性问题。比如,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之一。在整个亚太同盟体系中,美日同盟具有核心地位。[37]而在当前的东亚局势中,日本在很多方面都是麻烦制造者。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日本的行为,但是日本的外交自主性并不完全受到美国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改善。而且,美国并不希望自己的亚太同盟体系瓦解,因此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会鼓励中国与其盟国在外交上走得太近。所以,要消除东亚的秩序失范,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消除东亚秩序失范是两件相对独立的事情。尽管二者有一些关联作用,但是要消除东亚的秩序失范,推动地区新秩序建设,关键是靠中国自身,中国需要发展新的地缘战略。
五、亚洲新秩序与中国地缘战略
构建东亚新秩序不能靠美国,要靠中国。美国没有动力建立亚洲新秩序,因为当前的秩序失范状态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正相反,中国有理由、有需求、有能力构建亚洲新秩序,消除东亚的秩序失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制定和执行更加灵活的组合战略。这一战略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方面它能够对冲和反制美国的轴辐式同盟体系,使得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负外部性减至最小。另一方面,这种战略能够把中国在亚洲的威慑转化为威望,使中国崛起的正外部性增至最大。
1.“互相保证牵制”策略
中美两国很多学者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战略建议。比较有新意的当属互相战略再保证。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 Hanlon)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在核武器、导弹防御、太空和网络、军事基地和部署等领域推行互相战略再保证(mutual strategic reassurance)。[38]笔者认为,在现实国际政治中,互相战略再保证尽管有新意,却很难实现。本文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冲突策略理论出发,[39]提出一个新的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策略——“互相保证牵制”策略。
互相保证牵制策略的前提是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这些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脆弱性。互相保证牵制策略的运作机制是,其他大国可以利用这些脆弱性,对该大国形成牵制。如果大国间彼此都对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有牵制能力,那么大国间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则会倾向于选择合作,减少彼此间的冲突。例如,长期以来,美国都会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西藏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政治改革问题与中国发生冲突和矛盾。中美关系经常受累于这些议题。但是当中国有能力牵制美国的核心利益的时候,美国往往会主动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2008年末发生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美国银行业困难重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企业倒闭。而当时中国经济表现抢眼,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当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之际,美国没有在一些诸如人权、政改等无谓的话题上与中国争论,而是在金融、环保、军事交流等领域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现在的形势是其他大国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形成了较强的牵制,而中国并未对其他大国形成足够的牵制。如果中国能够对东亚主要大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形成牵制能力,那么长久来看,大国间的合作行为就会增加,从而有利于建设东亚新秩序。
2.“威慑转化为威望”策略
对东亚的大国而言,中国需要执行“互相保证牵制”策略。对东亚的小国而言,中国需要执行威慑转化为威望策略。威望在国际政治中非常重要。有威望的国家能够积极调动国际资源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没有威望的国家,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维护本国的利益。那么威望如何培养?本文认为,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威望来自于威慑能力。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所有国家都必须依靠自身寻求安全。对外威慑能力强的国家(往往是大国)必然自身安全感就强,而且也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威慑能力就慢慢转化为国家的威望。
本文将威慑分为消极威慑和积极威慑两种。消极威慑是指基于防御的威慑。比如,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具有极强的威慑能力,而中国的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会对很多非核国家无法形成足够的威慑力。积极威慑是指基于进攻的威慑。很多进攻性武器或者具有进攻性特质武器的发明和使用都能增强一国的积极威慑能力。比如,反卫星武器就是为了增强积极威慑。有些武器的作用可能会介于消极威慑和积极威慑之间。比如,一艘航空母舰可能会倾向于近海防御,所以是增强消极威慑,但是多艘航母就会形成强大的积极威慑。中国需要发展积极威慑能力,帮助实现中国的对外威慑转化为威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要从其他方面积极进行配合,否则中国的威慑能力很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看作威胁。
3.建设“新亚洲”策略
本文所谈到的东亚是广义上的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以及毗邻的其他亚洲国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在东亚地区深耕多年,虽然在历史上曾经为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过贡献,但是对于未来的亚洲新秩序而言,这个同盟体系更多会产生负外部性,不利于亚洲未来的发展。亚洲未来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依赖中国、日本、韩国、印尼、泰国等几个实力较强的国家,更是要深度发掘一些小国的发展潜力。中国的目标是要支持那些有意愿建设亚洲新秩序的国家。这些国家会与中国一起,成为推动新亚洲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应该继续执行差异化外交路线,[40]对有潜力的国家进行耐心持续的援助,为中国在亚洲的全面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未来的亚洲局面很可能是以亚太同盟为核心的旧亚洲与以中国为主导的新亚洲并存的局面。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塑了一个或者多个地区的秩序。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展到更高层次的一种状态,更是对整个地区秩序的重塑。需要指出的是,构建亚洲新秩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中国付出长期而坚定的努力。中国越是发展,遇到的问题反而会越多。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中国也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而奋发有为。
注释:
[1]在政策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先提到把一战前的英德与中日关系作对比。安倍晋三在今年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时表示:“目前中日之间经济相互依赖,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彼此有着重大共同利益,这同当时的英德一样”,“但英德间的经济关系这并未阻止1914年大战的爆发”。在学术界,请参考Ja-Ian Chong and Todd Hall,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4(forthcoming)。
[2]2012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理念,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3]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主题就是“日本回来了”。
[4]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world/obama-calls-america-pacific-president-hails-expanded-engagement-asia-article-1.414495.
[5]需要说明的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未离开过亚太地区。所谓重返亚太,美国强调的是加强对亚太事务的关注和干预。
[6]美国商务部长佩妮·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四月份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演讲表示,她将积极推进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重返亚太。2014年6月份,她率领美国商贸团访问了越南、菲律宾和缅甸。
[7]Aaron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p. 1.
[8]Michael Swaine, 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p. 338.
[9]孙哲主编:《亚太战略变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10]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1893], p.291.
[11]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0[1951], p.39.
[12]Bertrand Badie, Diplomacy of Conniva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171.
[13]John Mearsheimer,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8, 2014.
[14]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5页。
[15]Victor Cha, "Power Play: Origins of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2010, pp.158~196.
[16]傅莹:“关于东亚的合作安全”,《联合早报》2012年6月2日。
[17]Robert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9.
[18]张忠军:“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理论视野》2012年第4期,第56页。对话语权与权力的关系的探讨,请参考韩真,张春满:“在全球化环境下重新定义和测量权力”,《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9]张忠军:“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理论视野》2012年第4期,第56页。
[20]同(19),第57页。
[21]http://news.163.com/14/0516/06/9SBKFVAQ00014JB6.html.
[22]参考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3]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Reissue edition, 2006.
[25]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该书在2014出版了修订版,最后的结论部分有较大改动。
[26]"China Eclipses U. S. as Biggest Trading Nation" Bloomberg. Web. 21 Mar.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2-09/china-passes-u-s-to-become-the-world-s-biggest-trading-nation.html.
[27]John Mearsheimer,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8, 2014.
[28]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第13页。
[29]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 Policy, July 2013, p. 66.
[30]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8页。
[31]李开盛:“东亚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场’”,《学术月刊》2013年第12期,第37页。
[32]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第1-2版。中国外长王毅在2013年9月访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之际,再次对中方的理解给出了权威的解答。达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讨,参考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33]参考Caitlin Campbell and Craig Murray, "China Seeks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Backgrounder, June 25, 2013.
[34]Michael S. Chase, "China""""s Search for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12:27(September 7, 2012): 14. http://www.jamestown.org/uploads/media/cb_09_04.pdf.
[35]英文原文是"The ball is in the U. S. court to make the New Type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work", 参考Wang Yusheng, "Is It Possible for the U. S. and China to Build a New-type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Issue 117, Spring 2013.
[36]张家栋、金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历史、理论与现实”,《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第25页。
[37]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5页。
[38]James Steinberg, Michael O"""" 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 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39]参考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Rev. e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