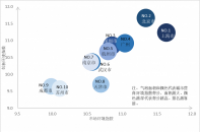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分处美国东西海岸的两个代表性科技园区,在相同的世界格局变化和产业革命的社会背景下,由于不同的发展理念、有区别的体制机制、较鲜明的文化氛围差异以及对产业机遇的把握能力等各方面的原因,128公路地区经历了兴衰历程而硅谷却保持了持续旺盛的生命力。自1984年我国建立第一批开发区至今,我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已经整整30年,且在今年来都有向科技园区转型的趋势。然而,由于体制机制不同、园区建立的历史背景各异、园区运营主体相差较远以及文化上的差别等原因,美国科技园区的兴衰经验和教训并不能对我国产业园区发展带来现实指导,有“远水解不了近渴”之嫌。但是,发掘美国科技园区兴衰过程中的核心理念,特别是硅谷长盛不衰的本质根源,把握住园区发展最基础的核心价值,却是十分有必要的。
斯坦福大学的功用化改革
当今世界顶尖的斯坦福大学在建立和发展初期,在科学研究和学术声誉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一地位不仅来源于斯坦福大学建校较晚,更是来源于其地理位置处于当时美国尚未发展的西海岸,与首都华盛顿距离遥远,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都是一个人才净流出地。但是,情况在这之后发生了改变。1933年,在竞选连任总统失败后,赫伯特·胡佛回到故乡,担任母校斯坦福大学的董事,开始主导斯坦福大学影响整个20世纪美国的改革。作为美国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一般拒绝联邦援助,其办学经费有一半来源于捐赠投资的回报。20世纪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使得这些投资回报不断降低。担任学校教务长的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推动了以与企业建立研发合同促进斯坦福大学学术声誉提高的改革方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战争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当时大学教师学术声誉来源的转变,即不再是以往的论资排辈,而是通过取得政府和企业的研发合同而得到的社会认可程度。这一改革也被称为大学功用化改革。
硅谷的前身—斯坦福研究园
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建立,它的兴起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大批青年没有进入战场,而是流入社会。一时间社会就业岗位紧缺,需要通过一种创新的机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最好的模式莫过于鼓励创业来吸纳就业。特曼教授在那一时期的初衷也仅是通过向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廉价的土地租金鼓励创业,一方面为学校积累办学经费,更重要的是为学校的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斯坦福研究园的建立初衷是来自于大学的需求,为了满足大学毕业生的创业和就业,更是为了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美国东海岸作为人才净流出地的状况。特曼教授建立研究园的思路不局限于当时全美顶尖研究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始终坚持的政府合同主导型模式,而是时刻寻求与企业的合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大量企业以开办分公司或成立新的子公司的形式不断向斯坦福大学周边集聚,通过科技研发集聚产业的趋势逐渐显现。
研究园的创新做法1953年,在建立斯坦福研究园的基础上,特曼教授建立了荣誉合作计划(Honors Cooperative Program)—大学允许附近的电子信息企业选派雇员到斯坦福攻读在职硕士学位,进一步加深了企业对大学的依赖;和产业合作计划(Industrial Affiliates Program)—大学在企业提出的任何特定需要之前,就向公司提供正式的、尚未公开的、军方资助的项目的科学和技术结果。这两项计划使企业和大学在合作中,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战略关系,在共同受益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大学—企业”的良性互动。这一互动使大学不仅能通过企业的资助聘请来最好的教师,而教师能培育出最出色的创新创业人才,人才又不必再流出到美国的东海岸,涵养在研究园内,可借助优越的创业和就业环境,自由发展并进一步回馈母校。斯坦福研究园在这种良性互动中,不断发展和繁荣壮大,成为现在的硅谷,已广为人知不必尽述。
二、对我国产业园区发展的启示
对硅谷长盛不衰的分析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由斯坦福研究园衍生而逐渐发展的硅谷长盛不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由MIT衍生且发展起来的128公路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近30年的繁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政府研发合同的大幅度削减而逐渐衰落。美国科技园区的兴衰交替也成为我国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热点。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政府—大学—企业”的社会创新体系中,MIT相对于企业始终都是强势的,而斯坦福大学却一直在尝试建立一种与企业平等共赢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机遇让斯坦福参与到“政府—大学—企业”这个创新体系中,政府对斯坦福的项目资助提升了大学在企业面前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在这之前一直都是弱势的。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大学参与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后来者,作为私立大学在进入这个体系后却一直都保持着和政府之间合适的距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又在促进与企业之间关系的互动和共赢。在这个“政府—大学—企业”创新体系中,政府对大学的项目资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大学—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赢使得三者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发挥出长效的、促进社会创新的作用。
催化剂研究合同、新兴产业引导
硅谷长盛不衰的核心理念在“政府—大学—产业”的创新体系之外,硅谷地区经历了一个社会精英的回归流。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校友,胡佛在总统连任失败后回到加州的家乡,作为斯坦福大学董事会中的核心成员,主导了斯坦福大学后来30年的功用化改革;20世纪4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校友,特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与完哈佛大学主持的雷达反侧实验研究工作后,回到加州的家乡,作为斯坦福大学教育长,积极投入到胡佛总统主导的斯坦福大学改革中;20世纪50年代,在半导体研发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威廉肖克利,也回到加州的家乡,在斯坦福研究园中开创企业,参与到特曼主导的美国西海岸信息产业的发展浪潮中。这种由政治精英的回归主导的管理精英的回归,以及技术精英的回归,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胡佛并没有因为在任总统时的业绩而获得当时美国人太多的好评,但其主导的斯坦福改革已经证明影响了全世界;特曼并没有因为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成就被世人所熟知,而广为流传的是他对初创惠普的扶持和“硅谷之父”的地位;肖克利在来到硅谷之前已经取得了人生巨大的成就,其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源自他之前对半导体的研究和发现了晶体管效应。但他在硅谷创建的仙童公司并最终被下属抛弃,“叛逆八人帮”成为硅谷最著名典故的同时,也引领了硅谷电子信息产业的不断昌盛。这些精英离开家乡—当时尚不发达的美国西海岸,取得了事业上的第一份成就。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历史机遇中,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由东向西的转移,亚太地区在战后的迅速崛起,他们回到家乡,对大学和科技园区的体制机制所做的一系列改革,起到了培育、涵养和发展人才的效果。我国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印证这一核心理念最好的案例。
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历程
深圳被认为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成功的“经济特区”。这种成功不仅体现在深圳城市化的速度、经济总量的增速、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更体现在从“科技沙漠”成为拥有一批如华为、中兴、腾讯等科技类巨型民族企业的“科技绿洲”。改革开放的初衷是由体制机制创新带动经济的活跃度,后期的发展一直以来是希望“以市场换技术”,深圳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显然是成功者。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历程中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为科研成果转化建立了一套目的性较强的体制机制;二是名校异地办学(只设立研究生院而没有本科教育)加速了大学功用化的发展和科技应用型人才的集聚;三是在大学作为一个社会创新主体长期缺位的情况下,企业作为科技研发主体是与名校异地办学最切合的企业科技创新模式。深圳在产学研合作发展历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的首创深圳大学和深圳科技工业园,到20世纪90年代的首创中国科技开发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虚拟大学园,再到新世纪的深港创新圈、大学城以及一系列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新型科研机构,所进行的探索是积极且富有成效的。虽然其中的很多创新构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一系列的“首创”围绕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吸引、培育、涵养和支持发展,完成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资源在深圳的集聚。这种核心理念恰是硅谷在异国的“知音”。
三、结语
吴敬琏先生曾经提出:“我们如果希望本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就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中去”。美国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与变化的世界格局、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社会文化氛围密不可分,更与顶尖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功用化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抛开这些解释,其长盛不衰的核心理念正是在一个欠发达地区由回流的政治精英主导,管理精英执行,推动科技精英的回归,所形成和遵循的“培育、涵养和发展人才”主线。这也是我国产业园区发展最值得借鉴和得到启示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