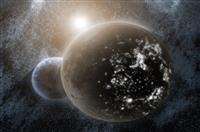一、引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1](P15)《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均提出我国要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如上海市提出了建成“9073”养老服务格局的目标,北京市提出了建成“9064”养老服务格局的目标。“但仔细分析相关政策条文就可以发现,其主要是针对机构养老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缺乏力度,90%居家自理养老的老年人更无具体的政策支持。”[2](P5)
针对地方政府过分强调机构养老而忽略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现状,学界表达了自己的关注与担忧。郑功成指出:“西方的机构养老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即使如此,欧美国家的老年人也并非喜欢入住养老机构,而是大多在高龄、失能或半失能状态下选择入住养老院,近几年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社会福利去机构化的倾向,表明社会福利模式不仅要植根国情,而且要与时俱进地发展。”[2](P5)金炳彻指出,当前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呈现去机构化趋势,“社会福利的中心将从以机构福利为主转到以社区福利为主”[3](P27)。丁建定指出,“国外养老服务经历了一个从机构化到去机构化进而走向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4](P22)。
由此,关于机构养老的发展路径便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发展机构养老服务,对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政策支持十分乏力;另一方面是一些学者对上述地方政府行为的批评,而学者批评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似乎去机构化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这样的观点不仅显得浅薄,而且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就非常有必要在此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去机构化究竟去的是什么?动因有哪些?实践及效果如何?去机构化给我国正在加快发展的机构养老服务带来了哪些启示?这些正是本文要着力回答的问题。
二、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动因
所谓去机构化是指20世纪初针对欧美国家大型精神病院中暴露出的非人性化问题而发起的一场运动,是用较少隔离的社区为基础的照顾替代精神病院的“全控式”照顾,以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场境,提高其生活质量的一种尝试。事实上,在去机构化运动背后隐含了几个基本假设,即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比以机构为基础的照顾更人性化、更有助于治疗和康复、更有成本效力(cost-effective)[5](P1040)。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运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来讲,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公众对机构服务质量的普遍关注。在19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大型精神病院对患者的控制、虐待和标签化等非人性化问题曝光之后,大型精神病院人满为患、医疗护理质量低下、患者权益受到侵害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鼓励下,针对大量精神病院开展的研究证明,住院治疗对病人的机能、动机和态度均产生有害的影响,如此的结果支持了社区精神卫生计划的发展。
第二,社区照顾被视为优于机构照顾。与精神病院照顾相比,社区照顾有许多优点,最为突出的是精神病患者可以在正常化的环境下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去机构化可以被视为“正常化原则”的一个切实产物。该原则假定:残疾人应该尽可能享有与社区中同龄非残疾人的典型日常生活相同的方式、条件、机会和环境。对这一原则的广泛接纳在逻辑上要求使残疾人避免非正常的日常生活方式、条件、机会、环境和社会地位等机构化要素的做法。[6](P605)
第三,减少财政支出的需要。二战后,各国对国内社会秩序的恢复高度重视,加之战争创伤导致精神病患者人数上升,许多发达国家政府支持建立的大型精神病院迅速增多,在1940~1950年代达到了高峰。“1930年代初期到1955年,州立精神病院全部居民数量从332000增加到559000,而1967年州立居住服务机构的日平均人口数为194650,达到了峰值。”[7](P71)大型精神病院的基本建设费用、管理费用和运作成本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社区照顾普遍被认为比机构照顾更节省财政支出。
第四,精神病人权利运动的推动。1960年美国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患者权利运动。在运动的支持者看来,精神病院剥夺了病人的许多权利,因此,精神病院越少,剥夺病人权利的情况就会越少。如果病人融入到社会中,在社区治疗设施的帮助下,他们就能恢复得更彻底,或者过上更满意的生活。病人权利运动者有一个基本理念,即正常的社区生活“是所有人——不论他的残疾程度有多重——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8](P19~20)残疾人对社区生活在身体与心理上的全面参与是实现社会公正理想的有效途径。[9](P379~389)
第五,新药物对控制精神病的保障。去机构化被认为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药物——酚噻嗪(phenothiazines)的引入而彻底开始的。与以往的精神病药物的疗效相比,新药物更加安全,有助于控制病人的大多数令人不安的精神病症状,使得很多长期以来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患者可以回到家中或社区生活。新药物的发明促进了社区心理卫生的发展,允许大量机构改变管理政策和减少强制措施。
第六,社会福利计划的快速发展。从1966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社会福利计划迅速膨胀,如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补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社会服务的残疾人保险(Social Service Disability Insurance)、住房计划(Housing Programs)和食品券(Food Stamps)等。这些福利计划的实施大大促进了美国去机构化运动的发展。
三、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和效果
不同国家因经济和政治体制、健康照顾和福利服务的结构不同,去机构化的进展也不同。美国社区心理卫生运动开始于1940年。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精神卫生研究法案》(Mental Health Study Act)。在1961年颁布《心理卫生法》(Action for Mental Health)。1963年美国肯尼迪总统促使第88届国会通过了《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法案》(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Act),该法案以联邦政府经费资助建造一种新型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设施,精神病患者去机构化运动就此开始,此法案是美国在精神病患者照顾方式改革上的重要里程碑。在英国,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英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在国家办的大型福利机构中居住的老年人在数量上超过了精神病患者和智障人士。“国家办福利”的模式使英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使福利国家财政负担问题更加凸显。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实施了减少财政支出、收缩福利计划的政策措施,“政府倡导在社区建立小型养老院或家庭养老,让家族成员和社区共同担负起赡养老年人的责任,以逐步打破大型福利机构的统治地位”[10](P20)。但是英国的去机构化远没有发展到在美国所能看到的势头。总体来讲,大多数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着手进行心理健康服务的去机构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去机构化。
1.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取得的成就
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颁布的社区心理卫生计划中设定,在10年或20年内,使机构照顾下的病人数量减少50%或者更多。实际上,去机构化的过程进展得比设定的目标更快、更广泛。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组统计数据得以证明。1955年,在美国大约有1/2的精神病患者被州精神病院照顾,而在1971年这一数字降到大约1/5。在1955年,不住院病人(outpatient)的服务仅占精神病人照顾的23%,而在1971年占到了42%。在1971年,联邦政府资助的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占精神病照顾的19%,而在1963年的《社区心理健康中心法案》通过之前,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甚至就不存在。在州精神病院居住的病人数量在1955年达到顶峰时的558992人,到1963年这一数字下降了45%。[11]到1975年,在州和郡精神病院的病人数下降了62%,到1985年美国公立精神病医院人数收缩到110000人。[12](P302)
随着“去机构化”运动的发展,很多条件和服务质量较差的大型精神病院被关闭,大量精神病患者被转移至社区或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美国在1960~2000年间关闭了113家大型精神病院,约占专科精神病院的41%。[13](P236~245)剩下的医院也都大大削减了住院床位,全国精神科住院床位由1970年的52.5万张(其中80%为公立机构床位)减少到2002年的约21.2万张(其中仅27%为公立机构床位)。[14](P685~688)“有数据表明,1955年时,美国每10万人口有339张精神病床;而到1994年时,已经剧降到每10万人口29张。”[15](P57)英国的精神科床位数由1955年的15万张减少到2007年的2.88万张[16](P1~2),大型精神病院由1975年的130所减少到了1996年的50所。意大利在1978年以后逐步关闭了全国几乎所有公立的精神病专科医院。[17](P1021)
2.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教训
作为精神健康领域的一场运动,或者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去机构化运动在西方学术界一直饱受争议,其所带来的一些教训也是深刻的。
首先,对于回归社区的精神病患者而言,重新适应社区生活是很困难的。然而,被设计的计划在提供给出院病人适应普通社区生活应具备的实践技能方面的服务明显不足。其次,由于长期背负的污名,大量精神病患者经常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客人”,给社区带来了恐慌。由于偏见,大多数心理健康专家反对让社区中的慢性精神病人工作。许多精神病患者因被社区和家人排斥而增加了羞耻感。第三,很多社区并未准备好充足的物质条件和设备来满足返回社区的精神病患者在衣、食、住、护理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尤其是合适住房的不足导致无家可归者剧增。第四,以社区为基础的心理健康服务经常缺乏集中管理,导致责任分化,社区治疗服务呈现碎片化特征,精神病人可用的治疗服务是有限的,尤其是缺乏有效的且不昂贵的治疗服务。最后,去机构化运动使个人和家庭遭遇巨大的财政困境。在美国,由于联邦和州政府面临着预算赤字收紧、津贴费(benefits)和公共医疗补助计划等方面的财政压力,美国公共计划逐渐收缩,以致到20世纪80年代,仅有2/5的穷人被覆盖。[18](P316)面对残疾人的日益增多,美国国会指导社会保障局核查残疾身份的合格与否,大量精神病人丧失了他们的津贴费。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的住房补贴也在收缩,对精神病人而言,低收入住房获得起来异常困难,无家可归者增多。
3.国外社会服务去机构化运动的结局
传统精神病院尽管有许多弊端,但是对于严重精神病患者而言仍是不可缺少的。即使在去机构化运动期间,美国那些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较好的精神病院依然被保留下来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时随着州和郡精神病院的减少,其他的非传统机构开始崛起。20世纪70年代在私人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数量增长了80%。最戏剧化的是,许多普通医院设置了新的精神科病房,而且其他的医院允许精神病人住在医院外科病房里。从1965年到1980年期间,在没有精神科病房的普通医院中入住的精神病人增加了6倍。[19]普通医院已经成为急性精神病人照顾的主要供给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疗养院(nursing homes)接收了许多从州精神病院转移出来的老年慢性精神病人,当时在美国疗养院收住了大约150万名严重精神混乱或痴呆病人。[20](P267~292)在社区,许多非传统机构以膳食照顾之家(board-and-care)、中途小客栈(halfway houses)、监护公寓(supervised apartments)和其他居住设施的形式出现,这些非传统机构加在一起很可能为30~40万慢性精神病人提供了居住安置。[21](P237~265)
近年来,针对去机构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大量精神病患者无家可归、患者家庭照料负担加重、回归社区的患者境遇改善效果不佳、“新长期住院”(new long-stay)患者增多、社区服务计划的财政负担依然较重以及个别患者回归社区后酿成的暴力凶杀案件等,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公众要求修改《精神卫生法》以强化对精神病患者强制收治的运动,以致有专家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国家重新走上了“再机构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道路。
由此可见,机构照顾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且也充分印证了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去机构化并非是不要机构照顾,而是要去掉政府包办的条件和服务质量较差的大型福利机构,去掉传统机构福利服务中存在的不够人性化、缺乏隐私保护、与社会隔离等弊端,防止不必要的机构服务,在保证机构照顾专业化、规范化的同时,要尽量做到机构照顾的人性化、正常化和社会融合化。从本质上讲,去机构化是指在机构照顾管理和服务模式上的“去机构化”。
四、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启示
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给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机构养老服务带来许多启示。
首先,我国需要加快发展机构养老服务。在去机构化期间及之后,机构照顾在国外社会福利服务中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不同的只是,在去机构化之初,国家办的福利机构中居住的对象以精神病患者和智障人士为主,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在国家办的福利机构中老年人的数量逐渐超过了精神病患者和智障人士的人数。而且在去机构化之后,与国家办的传统福利机构的减少相对应,大量的非传统福利机构崛起。反观我们国内,目前我国城市“三无”、农村“五保”等贫困老人以及孤老优抚对象的生活和权益保障,需要加强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等公办养老机构的建设;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日益加剧,需要不同程度介助、介护的高龄、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口持续增加,迫切需要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逐渐改变,整个社会对专业化、规范化养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目前我国城乡机构养老服务发展仍十分滞后,供需结构失衡、供需矛盾突出,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末全国共有养老服务机构4.2万个,床位381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1.96%[2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7%的水平,也未达到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罗马尼亚)的2%~3%的水平[23](P124)。因此,机构养老服务在我国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的问题。
其次,机构养老服务需要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就是政府不能也无力包办机构照顾服务。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去机构化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政府财政负担过于沉重,要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就需要减少政府包办的福利机构的数量,充分发挥社会、家庭和个人等主体在社会福利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去机构化背后蕴含的是新自由主义和福利多元主义价值理念的影响。对照国际经验,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数量剧增的国家,走政府包办福利服务的道路更是行不通。当务之急是要确立共同责任理念,建立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组成的社会支持体系。其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关键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和体制机制,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大力促进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实现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公平竞争、协调发展。
最后,我国机构养老服务要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从机构化到去机构化的道路,这样的发展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需要引以为戒。一是我国未来养老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要适度。其未来发展不能过滥,要防止不必要的机构服务。在我国接受机构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是少数,绝大多数老年人要依托社区分散在家中接受居家养老服务。这样的养老服务格局是由我国现实国情和传统文化决定的,同时也合乎西方国家和地区养老服务的经验。“据统计各国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英国为95.5%,美国为96.3%,瑞典为95.2%,日本为98.6%,菲律宾为83%,新加坡为94%,泰国为87%,越南为94%,印度尼西亚为84%,马来西亚为88%。我国老年人也热衷于在家里过晚年,北京、天津和上海关于养老方式意愿的抽样调查表明,90%以上被调查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24](P43)规模适度是指养老机构的规模不宜过大,更不能搞巨型养老院或老年集中营。因为大型养老机构虽然有规模效益,但弊端也十分突出。二是我国养老机构的建设不能远离社区、与社区隔离,要完善社区和家庭支持系统,使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保持与社区和家庭成员的交流。三是在实现机构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和职业化的同时,尊重老年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福利需求,改变管理与服务的模式,努力实现机构养老服务的人性化和正常化。除此之外,我国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还需要实现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协调发展和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机构养老服务的全面发展,以促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 [22].
[2]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与发展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 (2).
[3]金炳彻.从机构福利到社区福利——对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考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 (2).
[4]丁建定.居家养老服务:认识误区、理性原则及完善对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 (2).
[5]Richard Lamb, H., Bachrach, L. L. Some Perspectives on Deinstitutionalization[J].Psychiatric Services, 2001, 52, (8).
[6]Flynn, R. J., Nitsch, K. E. Normaliz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1980, 3, (4).
[7]闫蕊.美国残疾人居住及相关服务制度的演变[J].残疾人研究,2011, (4).
[8]Horton, C., Conroy, J.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s[J].TASH Connections, 2003, 29, (4).
[9]Duvdevany, I., Ben-Zur, H., Ambar, A. Self-determination and Mental Retardation: Is There an Association with Living Arrangement and Lifestyle Satisfaction·[J].Mental Retardation, 2002, 40, (5).
[10]仝利民.社区照顾:西方国家老年福利服务的选择[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4).
[11]Bachrach, L. L. Deinstitutionalizafion: An Analytical Review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M].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Rockville, Maryland, 1976.
[12]Mechanic, D., Rochefort, D. A.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 Appraisal of Reform[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0, 16.
[13]McGrew, J. H., Wright, E. R., Pescosolido, B. A. Closing of a State Hospital: An Overview and Framework for a Ease Study[J].The Journal of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 Research, 1999, 26(3).
[14]Sharfstein, S. S., Dickerson, F. B. Hospital Psychiat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Health Aff(Millwood), 2009, 28, (3).
[15]赵环.从“关闭病院”到“社区康复”——美国精神卫生领域“去机构化运动”反思及启示[J].社会福利,2009, (7).
[16]Green, B. The Decline of NHS Inpatient Psychiatry in England[J].Psychiatry on-line, 2009, 3.
[17]Barhui, C., Tansella, M. Thirtieth Birthday of the Italian Psychiatric Reform: Research for Identifying Its Active Ingredients Is Urgently Needed[J].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08, 62, [12].
[18]Mechanic, D., Rochefort, D. A.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 Appraisal of Reform[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0, 16.
[19]Kiesler, C. A., Sibulkin, A. E. Mental Hospitalization: Myths and Facts about a National Crisis[M].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87.
[20]Linn, M. W., Stein, S. Nursing Homes as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Facilities[J].See Rochefort, 1989.
[21]Segal, S. P., Kotler, P. Community Residential Care[J].See Rochefort, 1989.
[22]统计局:2012年全国养老机构床位达381万张[EB/OL].中国新闻网,2013-02-22,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2-22/4586957.shtml.
[2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 (3).
[24]熊必俊.论人口老龄化与建设人本住宅和亲情社区[J].住宅科技,2004,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