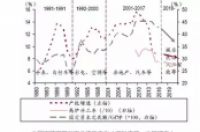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现代科学联系紧密,当前全球治理正向多元治理方向演进。科学家团体、企业、区域性的政治组织等也在全球治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包括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制定和维持着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如科学家团体、环保类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①]科学家团体不断为专业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符合全球利益的方向发展。从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IPCC报告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球治理议程都离不开科学家团体的重要作用。当前,北极区域政治和治理结构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北极和关于北极的政治活动增加,科学家团体在北极治理的议程、责任以及义务分担等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之作用。
彼得·哈斯认为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拥有决策的权威,哈斯强调把科学家团体作为国际决策中的重要一环,强调科学家团体的权力作用,认为他们会影响国际制度演进。哈斯理论侧重于权力维度而忽视了知识本身的影响过程。与哈斯的理论不同,本文提出科学家团体主要具有知识和规制两种重要作用:一是极地问题的知识化;二是北极事务的规制化。这两重作用体现在北极事务中的制定议程、确定议题以及阐述、实施、评估政策交互作用,并且推动极地治理事务的发展。本文选择北极科学家团体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对极地科学家与北极治理的关系进行剖析。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和问卷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实际有效问卷70份,受访对象主要来自参与极地事务的北极理事会下设的科学机构、极地区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北极地区议会常设委员会、北极动植物保护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北极海洋科学委员会、北极环境监控与评估项目、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国际北极社会科学协会、国际苔原科学实验组织等组织。
一、科学家团体与全球治理
知识对于全球治理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权力维度、共有知识和非国家行为体等理论分别从不同视角对科学家团体和全球治理进行了探索。
从权力维度出发,彼得·哈斯提出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②]概念,认为专家借助于专业知识劝服他者,形成政策目标的专家网络,并构建共有因果信念:首先,认知共同体可以发挥“知识经纪人”的作用,专家可以解释全球治理领域中各种议题的因果联系,并为国际谈判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其次,认知共同体可以起到“信号”或者“催化剂”的作用,专家推动某些议题在国际社会升温,带来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公共舆论的关注。第三,认知共同体也是一种的权力影响过程,在此过程中,哈斯强调“社会学习”的概念,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学习”产生共有知识,以此影响国际组织内部政策决策过程。
从共有知识角度,有学者认为共有知识是各国对全球治理的共同观念,具体指各国在互动中形成的对全球治理必要性的认知,彼此间的信任感和预期,以及对相关原则和方法的态度。共有知识是互动中凝聚起来的认知,如科学知识、观念、国际社会观点等等,其主要来源于科学家团体的观念和著作[③],认知论可以解释国际制度的整套程序。共有知识理论也强调国家利益是一种主观认识,它受到误判、意识形态、认识观点影响。认识学习也就是通过学习或在某种环境中的经历来促进决策者的知识[④]。科学家团体将会促进决策者学习的过程发展,并导致决策者的认识和观念变化,约瑟夫·奈指出,学习通常包括了从极度简单到复杂的综合概括,该过程推动了现实焦点汇入具体细节,并形成复杂学习过程的模式(complex learning)[⑤]。基欧汉认为,专业团体会在国际制度形成过程中提供主流信仰、原则性信仰以及道德信仰,以此影响全球治理进程[⑥]。
从非国家行为角度出发,研究国际制度理论的学者长期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制度等)对国家行为的塑造,科学家团体可将相关的知识和理念制度化:一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二是组建联盟,对源于其知识的政策予以支持其;三是创造基于其知识的组织实体[⑦]。在许多专业性国际制度决策中,科学家团体通常扮演了权威的角色,他们可以利用专长,对政策相关的知识提供权威解释并提供解决方案。因此科学团体提出的思想、观念、信念以及知识会指导决策者的行为、促进国际合作制度的演进。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气候谈判的影响[⑧],IPCC共发布了五次评估报告,对国际气候谈判均产生了重要影响[⑨]:第一次报告指出人类活动正在显著增加温室气体,推动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次报告强调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推动了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第三次报告推动了气候变化谈判确立适应和减缓两个议题;第四次报告明确提出气候变化很可能归因于人类活动,推动了“巴厘路线图”的诞生,第五次报告讨论了全球实现气温升幅2度内目标的几种排放途径,众所周知,气温升幅2度以内是各方推动2015年巴黎达成新框架的重要共识。
本文认为,全球治理中的科学家团体发挥了“制度”和“知识”双重作用:从知识角度来说,科学家团体帮助决定政策讨论的范围、议题解决的层次或场合,以及解决议题时会用到的规范和制度。这些初步选择为界定政策利益准备舞台。科学家团体通过特定的扩散机制向全世界宣传其观点,如会议、座谈会、研讨会、学术性出版物、研究合作,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交流等,并通过政策游说和信息传播提高主张和方案的被接受度。科学家组织和个人在掌握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环境、海洋、生态、气候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在政策主张上对国家政府构成了竞争性,有的时候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并不是主动接受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政策主张。因此,科学家组织就会与一些非政府组织结合,以各种方式宣传其主张,甚至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会议期间举办平行会议,吸引媒体和公众,给国家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变某些日程、立场和制度。从制度角度来讲,科学家可以促进国际治理机制和国际法律制度的形成,并监督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行为。有些科学家组织甚至帮助起草相关规制关键的最初版本,一些国际治理公约正式版本的附件大多是具有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士帮助起草修订的。此外,许多国际组织也都在制度安排上给科学家组织提供政策建议的渠道和场所,并保证这些咨询意见能够得到应有的反馈。更为重要的是,有些科学家参与了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工作组活动,从事实际的国际救助和国际协调工作,帮助国际组织完成具体的治理协调任务,这样可以保证国际组织的资源可以在科学家组织专业意见的指导下更有效的投入。在许多专业性国际制度的公共决策和规制建设中,科学家团体往往扮演了权威的角色。科学家团体可以介入、设计议题和帮助界定决策者的利益。科学家团体通过知识的制度化,将相关的观点、信念和目标形成共有知识并且固定化。
北极治理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就是人类北极活动增加与北极治理机制相对滞后的矛盾。制度作为治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缺乏与落后,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知识的缺乏。人类对北极多学科的研究和考察还相对不足,治理所需要的知识还相当缺乏。几乎所有与北极治理相关的报告都强调知识的特殊作用。知识对于制度的变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知识积累的有限性会限制制度创新的深度和广度,而知识存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人们发现制度不均衡进而改变这种状况的能力。[⑩]
从知识提供和建构角度来讲,科学家主要通过联合国下属国际组织(如国际海事组织、世界粮农组织)、政府间科学家组织(如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北极区域国际组织的工作组(如北极理事会工作组)开展活动。从北极治理角度讲,发挥更直接作用的是北极理事会的以下各个工作组:(1)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工作组(AMAP)——对北极环境人为污染物测量其污染水平并评估其影响;(2)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CAFF)——解决北极生物多样性问题;(3)突发事件、预防、准备和反应机制工作组(EPPR)——解决环境突发事件的预防、准备和反应问题;(4)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PAME)——解决政策和非突发性的污染预防问题;(5)可持续发展工作组(SDWG)——解决经济、文化和北极居民健康的保护和提高问题;(6)清除北极污染行动计划工作组(ACAP)——预防和根除北极环境污染。以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工作组(AMAP)为例,一些北极科学家就是通过该工作组,为北极治理提供可靠、充分的关于北极环境的现状和潜在威胁的信息,提供参考性的科学建议以帮助北极各国政府在减少和防止污染方面做出努力[11]。
根据笔者对参与北极科学研究的各国科学家,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参与北极理事会相关工作组的科学家的问卷调查[12],大多数受访科学家认为,科学家团体对北极治理较为重要,四成受访者对关联度打了满分(5分),只有约4%的受访科学家认为科学独立于极地治理。若答案D、E两项相加,则认可二者深度关联度的受访者达到62%,若答案C、D、E)三项相加,则承认有关联的受访者达到89%)。这说明参与极地科研的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的社会意义有高度的认同感,或者说希望他们的科学工作能够为人类幸福带来益处。(如图1所示)
从知识建构角度来看,要成功建构一个北极治理问题,至少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相关北极治理主张必须有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第二,对北极治理特别是北极环境变化的治理建构,必须要有相应的“科学普及者”,他们能将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能够为普通民众所理解的北极治理主张。这些科学普及者既有可能是科学家也有可能是科普作家,他们将北极治理的信息和资料重新包装以吸引新闻媒体、政治倡议者及其他意见领袖的认同。如在北极治理知识推广方面,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和极地年活动组织者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年蒙特利尔国际极地年活动有将近200个项目,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约1000名科学家参与,大批的政治人物、企业界人士、媒体也积极参与,为实现“从知识到行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为北极各项治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扫清了部分认识上的障碍。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技术变革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只有在和巩固或支持社会可接受的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基本信仰系统一起发生变化时,技术变革才会改变权力结构。[13]她试图说明的是,技术变革一定要引起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安排的信仰系统发生变化,否则不能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制度。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对于制度建立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当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一旦产生,它就会激发和加速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重新安排。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社会科学知识和教育体系的结合,扩展了知识体系的普及性,进而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在关于科学家团体在极地事务中的哪个环节发挥作用的问卷回答方面(图2),43%的受访科学家认为是科技咨询,22%的受访科学家认为是提出国际议程并确定优先顺序,21%的受访科学家认为是提供治理工具。从本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提供知识是科学家团体影响北极治理的重要途径。选择科技咨询作为主要环节的受访者,在态度上比较积极。他们基本认可科技知识备询者和诚实经纪人的身份,[14]但并不十分主动介入决策过程;倾向“提出国际议程并确立优先顺序”和“参与决策”选项的受访者态度则更为积极主动,按照皮尔克(Roger Pielke)的分类应当属于“问题主张者”,他们重视科学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介入;而倾向“提供治理工具者”的受访者,态度也属于较为积极,他们的关注点不是放在治理制度形成前或形成中的备询角色,而是放在治理决策形成后的治理过程中,发挥治理技术工具提供者的角色。
在北极治理谈判的议程设定方面,科学家团体通过提供某一环境问题的科学信息、加强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及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等,从而加深各国对该问题的认识,使相关新议题和议程被列入北极治理谈判的议题,并推动各国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利益,从而对北极治理机制的形成做出贡献。在北极治理谈判过程中,科学家团体通过对具体协商和谈判细节的研究,提高谈判效率和共识,推动北极治理相关合作的进程。为此我们设计了问卷,征询受访者关于科学家团体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根据下图的问卷(图3),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家团体为北极治理所提供的知识涉及面很广,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法律制度、能源开发利用、环境监测、海上救援、原住民和气候变化等等诸多问题。
北极治理制度对相关知识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第一类知识的需求是对北极自然环境各类变化的系统化的信息;第二类知识需求是关于北极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知识。最近几年北极各种治理文件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关于北极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知识的加速积累;第三类知识需求主要来自开发技术的发展。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部分,北极地区的资源、航道都会更深地与全球市场融为一体。要确保开发的速度和规模控制在北极生态系统可以支持的范围内,就需要必要的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的创新;第四类知识需求是源自北极治理制度建设的所需要的信仰系统,也就是非正式的约束部分。治理制度的演进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安排,都需要社会广泛的接受和支持。据此,本文发现,受访者对第一类知识的更为重视,比如说科学研究、气候变化有更高的重视度;北极人类发展报告(AHDR,2004),北极气候影响评估(ACIA,2004)等具有极大影响力。其次则是属于第四类知识的法律制度、国际关系和治理机制;再其次则是属于第三类知识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应用类,如能源开发、技术应用、基础设施、经济开发、海洋营救等;如北极石油和天然气评估(AMAP,2008),或北极海运评估(Arctic Council,2009)等出版物为决策者、公司,以及活动家提供了所有层面治理的信息。然后是涉及第二类知识的环境控制和原住民关切等方面。总体反映了受访者对北极治理对知识需求类别紧迫性的看法。
将北极问题和全球环境变化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涉及到很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必须包含对社会规范、价值和观念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领域的科学家协同设计和跨学科合作是重要的方法。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大学(UNU)、贝尔蒙特论坛(Belmont Forum)和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IGFA)等组织共同牵头组建的为期十年(2014-2023)的大型科学计划“未来地球(Future Earth),重点研究了未来几十年地球环境面临的主要变化和挑战,其中就包括了北极变化及其科学对策。
科学家团体不仅仅是作为科学技术和治理知识的提供者,也通过参与北极理事会工作组的议程设定、条约起草以及监控实施等成为北极治理制度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北极理事会成立于1996年,是北极问题最重要的治理平台,科学家团体在北极理事会相关制度建设中发挥了五重作用:推动北极治理制度建设,协调不同制度和治理领域、引入“极地年”等倡议、促进不同专业的协同合作、以及促进信息沟通和协作:
第一,对科学家团体而言,要能够成功地进入北极治理政策议程并最终得以发挥作用,应当有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确保相关科学建议的合法性和持续性,尤其是科学家团体的意见需要进入法律程序的过程中。在北极治理机制形成方面,国际社会如何理解某一机制所针对的治理问题并愿为此采取何种行动对该机制的形成是关键。北极治理科学家团体通过提供相关问题的科学信息、宣传北极环境变化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影响来加深各国对该问题的认识,使其列入北极治理谈判的议题,并推动各国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利益,从而对北极治理机制的形成做出贡献(图4[15]、)。在这个问题上,倾向“非常必要”和“必要”两项答案的分别是33%和40%,二者相加共有73%;回答“不太必要”、“不需要”和“不知道的”加在一起只有27%左右。这说明,极地科学家对科研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对治理作用的发挥特别有认同感,而且在极地科研中他们会比在其他地区开展科研活动的科学家更深切地体会国际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
第二,北极相关治理涉及很多领域和制度,既包括全球层面的制度,也包括区域层面的制度。在联合国层面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UNFCCC)等,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MARPOL)等。全球性制度具有全球适应性,参与的科学家的人数也更多。许多人并不直接涉及北极,但其对北极治理的贡献同样重要。因为北极冰封区域的特殊性,许多国际制度都给北极治理留出特别的制度空间,呼吁相关国家和地区以科学家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制定区域性的治理制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4条是唯一涉及北极海域“冰封区域”的条款,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北极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制船舶在冰封区域航行以及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即“沿海国有权制定和执行非歧视性的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船只在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冰封区域对海洋的污染,这种区域内的特别严寒气候和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冰封的情形对航行造成障碍或特别危险,而且海洋环境污染可能对生态平衡造成重大的损害或无可挽救的扰乱。这种法律和规章应适当顾及航行和以现有最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础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16]该条款不仅预留了区域治理的特殊性安排空间,同时将科学家的作用提升到必要条件的高度。国际海事组织(IMO)近年来正在制订《国际极地水域营运船舶安全规则》(极地规则),该规则将成为规范北极航运行为、保障北极航行安全、保护航行海域环境和生态平衡的、最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和技术标准(更多的全球治理机制请参加表格1)。这些治理平台和治理工具的形成和运用,都离不开科学家和专业团体的贡献,他们的贡献成为这些制度成立和完善的基础。
第三,在北极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如在北极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开发等领域,科学家往往需要在相关工作组内协同进行合作。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北极在全球气候体系中的作用预示着北极科学家团体在北极治理中的位置日益凸显,如北极气候评估项目(ACIA)的报告认为北极地区气温上升的速度是一般地区的二倍,北极理事会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SDWG)提出北极“脆弱性和适应气候变化(VACCA)”问题,这两个议题都在北极理事会气候适应议程中得到体现。在治理的全阶段,在任务分解和时间安排方面,工作组基于科学知识和信息,在治理中发挥着轴心作用,如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CAFF)根据观测结果和对动植物生态规律的揭示提出动植物保护方面的行动计划和相应制度,在其关于《2013-2021期间基于北极生态多样性评估基础上的生态多样性保护行动建议的执行计划》[17]中,工作组提出了许多科学的和社会的工作计划和方案,如环北极生物多样性监测计划Circumpolar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Program (CBMP)、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计划和方案、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方案、提升公众保护意识方案等等,明确了工作目标,并将这些计划和具体任务分解到十年中的每一个轮值主席任期之内和相关机构和部门之间,还强调了落实,体现了“从知识到行动”的精神。2013年CAFF发布的《北极生物多样性评估》[18](Arctic Biodiversity Assessment)便是CAFF通过其建立起的北极环境长期观测能力,对北极当前生物多样性现状开展的有效评估,就应对气候变化、基于生态系统基础上的管理、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北极理事会主流议程、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领域、应对生物多样性应激源(Stressor)、增进知识与公众意识等六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主要建议包括:将气候变化作为考量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的重要参照因素;提倡基于生态系统基础上的管理;将北极生物多样性目标纳入北极政策制定、标准设定与活动规则中。另外近年来,在相关不同领域科学家协同工作的基础上,北极海洋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不断更新的“北极近海油气开发指南”(Arctic Offshore Oil And Gas Guidelines ,AOOGG)[19]
第四,科学家团体通过国际极地年等机制推动北极理事会相关规则建设。科学家团体提出了“国际极地十年(International Polar Decade,IPD)”和“国际极地年”的建议。世界气象组织-俄罗斯水文气象与环境监测会议在2011年提出了“国际极地十年”,并推动建立新的极地地区治理架构。该架构包括了相关极地国际机构代表组成的专家组,通过专家组来分析极地治理需求和治理手段。2012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从知识到行动”国际极地年总结大会动力系列行动论坛(Action Forum Momentum Series)推出了国际极地倡议(International Polar Initiative,IPI),随后的旧金山和巴黎国际极地倡议会议发起成立了国际极地合作倡议(International Polar Partnership Initiative,IPPI)。该倡议于2017-2018年得到全面执行,为极地治理提供了大量科学依据。该倡议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作为重要的认为,通过对对相关类型的资源开发,进行极地环境影响评估(EIAs),并对极地资源的大规模商业利用进行制度和技术上的规范[20]。
第五,北极治理需要各相关方面的协调,科学家团体在其中发挥了促进信息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在一个多元多层级的治理结构中,信息沟通和知识协调对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意义重大。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21],受访者对科学家团体是否有效地提高了北极治理的信息沟通表明了各自看法,如图5所示。根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受访者中有89%的比例是赞成和非常赞成“科学家团体有效地提高了北极治理的信息沟通”,其中赞成的占49%,非常赞成的占40%,而不太赞成的为7%,不知道的占4%,没有受访者选择“不赞成”这一选项。
受访的科学家很多都是参与国际极地年、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等国际极地科学项目的人员。这些项目的目的性很强,与极地治理的关联度很大,体现了“从知识到行动”的精神。科学家团体在北极理事会的工作组层面参与了制定治理规则的任务,这些工作组包括北极污染物行动计划(ACAP)、北极监测和评估方案(AMAP)、北极动植物保护小组(CAFF),紧急事件预防、准备和响应(EPPR)、保护北极海洋环境(PAME)及可持续发展工作组(SDWG)等。相关工作组之间也有大量的协调和信息沟通。另外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AMAP)、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和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也联合发布北极苔藓报告,并将之引入北极理事会议程。
四、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北极治理中的科学家团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和塑造全球治理:一是知识层面,通过认知共同体产生共有知识(影响因素包括学习、国际训练、集体信念培养等),以及形成新的利益观念,如物质利益分配或者对利益的认知形成;二是制度层面,推动治理制度层面变化(议事日程的变化、决策机构的建立、决策结构的确立等)。北极海冰的融化触发了人类开发北极资源的愿望。北极的治理需要在开发资源和保护生态之间取得平衡。由于北极地区地理条件的严酷和生态的脆弱,人类对极地的知识又相当有限,科学家团体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科学家在北极的科学研究,为解决北极环境问题甚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所需知识和指导建议。科学家团体的参与将会有助于提高治理方案的科学性,有助于维护全球利益。科学家团体推动北极事务的国际化和规制化,这两重功能具有相互建构的关系:即理性主义的利益逻辑和建构主义的规范建构逻辑。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科学家团体在相关议题上的知识、规范认知会对极地规制的修改和变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北极治理中的三个重要环节都包含着科学家团体的重要贡献,其一是治理问题的提出;其二是治理议程的设定,其三是治理制度变迁。在北极治理最关键的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及其科学家组织的参与规模和程度是其他许多议题所不可比拟的。在议程设定中,科学家组织,特别是那些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工作组在治理日程设定的职能十分显著。他们在极地议程制定中起到了显著作用,通常能把科学信息转化为服从于法律和国际协议的形式。
注: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知识与规制:极地科学家团体与北极治理议程设置,项目编号:41240037)的阶段性成果,笔者感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剑研究员在写作过程中的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的指导。文章涉及的内容和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注释:
[①]Matthew Paterson,David Humphreys andLloyd Pettiford,“Conceptualiz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From Interstate Regimes to Counter-Hegemonic Struggles”.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3,Issue..2,2003,pp.1-10.
[②]Mai""""""""ak.Davis Cross.“Rethinking Epistemic Communities Twenty Years Lat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9,Iss.1,2013,p.139.
[③]Peter M.Hass.“Special Issue on Knowledge,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1,1992.
[④]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pp.35-117.
[⑤]Joseph S.Nye,Jr.“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
No.3,(Summer 1987),pp.378.
[⑥]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 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inceton,1993.
[⑦]Peter M.Hass.“Special Issue on Knowledge,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1,1992.
[⑧]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建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旨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评估与理解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这种变化的潜在影响以及适应和减换方案的科学基础有关的科技和社会经济信息。参见:http://www.ipcc.ch/home_language_main_Chinese.shtml,2014年10月6日浏览。
[⑨]王伟光,郑国光主编:《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8页。
[⑩]黄新华:《新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11]Charles Ebinger,John P.Banks andAlisa Schackmann.“Offshore Oil and Gas Governance in the Arctic:A Leadership Role for the U.S”,Brookings Policy Brief,Vol.14,Iss.1,March 2014,p.57.
[12]本问卷的题目是“请您给极地治理和科学家团体的关联度进行打分”,在0-5分中选择,5分为最高,作者注。
[13][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14]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教授根据不同的社会态度将科学家分为四类:纯科学家、科学知识备询者、问题主张者、诚实的经纪人。Roger Pielke,Jr.,Climate politics.The Climate Fix:What Scientists and Politicians Won’t Tell You About Global Warming ,New York:Basic Books,2010,p213
[15]问题为“您认为应对极地治理是否必须科学家团体的推动和协调配合”,选项为:A.非常必要,B.必要,C.不太必要,D.不需要,E.不知道,作者注。
[16]参见联合国网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八节冰封区域”,http://www.un.org/zh/law/sea/los/article12.shtml,2014年11月2日浏览。
[17]CAFF,“Action for Arctic Biodiversity: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rctic Biodiversity Assessment”,http://arcticbiodiversity.is/abt2010/,2014年10月12日浏览。
[18]根据笔者参加冰岛极地会议了解到,《北极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由瑞典环境保护署自然与多样性部门负责人Mark Marissink担任,并召集了来自北极八国,以及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30余名科学家共同完成,该评估报告也得到了加拿大、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美国、北欧部长理事会等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的资金赞助。
[19]Arctic Council,Arctic Offshore Oil And Gas Guidelines 2009,available at:http://www.arctic-council.org/index.php/en/document-archive/category/233-3-energy?download=861:arctic-offshore-oil-gas-guidelines,last accessed on January 12,2014.
[20]参见: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ce Committee,"International Polar Partnership Initiative (IPPI)",http://www.iasc.info/home/initiatives/current,2014年5月6日浏览。
[21]图5所代表的问卷问题是“您是否赞科学家团体有效提高了极地治理的信息沟通”,选项A.非常赞成,B
赞成,C.不太赞成,D.不赞成E.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