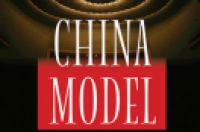
在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那里,“meritocracy”(观察者网注:即精英治国,又译作贤能统治、选贤举能)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但在你这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正面得多:为什么这个名词的意义会被洗白,这一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贝淡宁:在1957年出版的讽刺著作《精英社会的崛起》里,扬暗示道,一旦论功行赏的体系被制度化,就会导致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出现:在这个世界里,意志消沉的群众将被一群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精英所统治(观察者网注: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其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里,描述了一个按等级生活的社会,人们被分为不同阶层,分别从事或劳心或劳力的工作。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被剥夺,而“幸福感”是在麻醉的幻觉中得到的)。他把“精英治国”一词狭隘而生硬地定义为“智商加汗水”,并称“功绩”将被用来证明政治经济等级存在的合理性。就因为他的这本书,接下来的几代人闻“精英治国”而色变。扬同时也期盼着某种“时代精神”的降临,这种时代精神着重强调了社会生活在各个维度上的平等。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政治思想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促进社会的平等。在西方主流思想中,试图证明某些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不亚于踏入了道德禁区。
同他相反,我认为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都是需要某些等级制度的,而重中之重在于区分有益与无益的等级制度形式。我认为政治上的某些等级制度的确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同于扬的观点,在我看来,“政治功绩”的定义会在不同背景下发生变化,而“功绩”的含义只适用于证明政治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而非财富的不均)。我还认为,任何想使“精英政治”制度化的尝试都必须同一些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机制相平衡。事实是,在英语里,“精英治国”一词仍然带有相当的贬损意味,所以我才会用“精英政治”这个名词,来强调我对这个词语的特殊用法。再者,我的书主要在讲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文里是用“贤能政治”一词来表达“精英政治”的意思的。这个词听来就很正面,起码比英语里的“精英治国”要积极许多。
你是否能替“精英政治”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好让普通读者也看得明白?
贝淡宁:一个旨在推选具有超卓能力与美德的人作为领袖的政治体系,就符合“精英政治”的概念。我们既然要求在科学、法律和商业领域执牛耳者都训练有素、堪当大任,那么在“国家”这个最为重要的机构里,当然也该如此。“精英政治”与中西方的渊源都可谓深厚。政治领袖们(观察者网注:原文如此,按文意当为政治思想家)——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约翰·穆勒和孙中山——都试图找到能选拔出最佳政治领袖的方法:其人要具备能就一系列广泛事务作出政治判断的能力——明智,且无伤于德。然而,在二战后的年月里,诸如此类关于“精英政治”的辩论就销声匿迹了。在选择政治领导人时,西方社会几乎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不论是哪个层级的政府,都必须由一人一票制选出。所以讨论当代社会的其它构建模式毫无意义,甚至连想都不必想。也正因此,我才会在开宗明义的那一章对一人一票制加以批判。
贝淡宁:就如何将旨在选择优秀政治领袖的选贤任能机制与旨在让人民做主选择领袖的民主政治机制相结合,我在本书第四章里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在选票层面上将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统合在一起(比如说将额外的选票分配给受过教育的选民);第二种模式着眼于政治制度层面上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调和(比如说,在一个民主制的议院里,政治领袖由民众选举出,而在一个精英制议院里,政治领袖则是通过考试选拔的);第三种模式的目标,则是将中央层面的精英政治同地方层面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第二种模式的坚决拥护者,但现在却觉得,只有第三种模式是既合于政治现实,又不违道德理想的。此外,我认为正是第三种模式的变体——即,基层开展民主,中层勇于试验,顶层强调贤能——激发了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所以我才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模式”。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与民主式贤能政治的理想模式间存在的差距,并就如何缩短这种差距提出了一些建议。
你的研究集中于“精英政治”,并将其区分于更难为之辩护的“精英经济”,这是为什么?
贝淡宁:我赞成卡尔·马克思和约翰·罗尔斯这些思想家提出的如下看法:生而有才能者并不能授财富以道德性,因为“与生俱有”和“与生俱无”,同其个人作为无关。因此,我不会为经济上的“精英统治”而辩护。我要维护的是“贤能政治”这一理念,即,政治力量的分配当与才能及德行相一致。——只有在经济资源影响到了这一既符合道德理想,又贴近政治现实的“贤能政治”模式之建立时,我才会就其分配提出某些看法。我在第三章里指出,对物质财富的相对均等的分配,能控制政治层级僵化无法适应新环境的风险。
对于“精英政治”何以在今时今日焕发魅力,你给出了两个理由:西方民主政治的失败和中国的崛起。假定这两个条件并未出现,“精英治国”还会有吸引力,还会可行吗?
贝淡宁:我并没有暗示说民主在西方已经“失败”了。我的意思是,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形式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还存在着其它具备道德合法性的方法来选拔政治领袖。
在西方社会,选举式的民主政治已根深蒂固,要对其进行改动,在可预见的未来,代价也许会过高。因此我并不要求西方择路重来。而在中国,“贤能政治”的传统源远流长——确切说来,在中国,关于统治者应当拥有何种能力与美德的辩论,以及科举取士、依政绩从基层逐步升迁的实践,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中国过去三十年崛起之基础,正是这种现代化的“贤能政治”。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政治模式仍将继续。
所以,大体上看来,“贤能政治”在那些已有漫长实践史,且在近期仍创佳绩的国家里是最为可行和合意的,而目前最符合这些条件的,就只有中国(新加坡的条件也切近,但其统治政党是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贤能政治”的,如果反对党派取得了政权,这种唯才是举的政治体系也许就无法继续下去)。但前景总是莫测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会行至末路(我祈祷永远别有这么一天),而“贤能政治”也会被证明并不适用于中国(我同样祈祷永远别有这么一天)。
你所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精英治国”比一人一票制更有效。难道“内在价值”与绝对原则就不值得考虑吗?
贝淡宁:我的意思是,最好将选举民主看成是一种程序,旨在产生好的治理方式,如果其它的程序更加行之有效,就该择其善者而从之。政治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选举的看法,或者说,对选举的评估。话虽如此,民主政治更深一层的价值,即给予民众平等的政治身份,是为当代大多数社会所认同的,中国也不能例外。但这种价值可以通过某些机制(比如说,所有公民都有参加考试以进入仕途的权利,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实现,不一定要假手于选票制民主政治。在当代中国,几乎不会有思想家赞成恢复帝制时代那种视政治平等如无物的做法了:比如禁止妇女参加科举,或者对犯了罪的登科举子宽宥以待。
你在第二章里断言,中国的一党制有改进的空间,但目前它仍行之有效,也没有崩溃。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政治体系的弊端同样很明显:对异见者的打压、腐败、生态灾难、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难道这些消极方面同“精英政治”间全无关系吗?
贝淡宁:造成这些消极面的原因有许多,但有时应当归咎于为实现“贤能政治”而采取的不当手段。比如说,中国的环境污染部分就可归因于眼光短浅、以GDP增长来衡量官员政绩并决定其升迁这一事实。当政府把全副精力扑在消灭贫困上时,GDP增长的确是一个恰当的间接衡量值,而以此来评定政绩也不无道理。但当一个国家面对着一系列更为多样化的挑战时,这种评定方式就无道理可言了。政府同样要以更为多样化的标准来考察官员,环境可持续性当然包括在内。问题在于,当标准多样化后,评价难度也会相应增加,评定过程就会变得更为主观化。基于此,这些评价方式应当补充以更为客观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常常同政治领袖的良好表现相关(举个例子,研究表明女人拥有更多政治领袖所亟需的社交技能,这意味着应当提拔更多的女性)。再有,腐败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提拔官员时,上级领导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更了解被提拔者品性的无疑是其同侪,因此我认为要建立起某种机制,加重同侪评议的话语分量。
你承认中国有试验多套方案的能力,并肯定了它在治理措施上(尤其是在权力金字塔的较低层级)的灵活性。我在中国时常常会去报道中国政治体制中常常为西方所忽略的那些层面(比方说我曾前往许多投票站,报道朝阳区人大代表选举)。但说实在的,中国的政治体制真不是浪得虚名?换句话说,你批评其压制和审查制度,却不像反华论者那样加以诋毁。你是怎样调和这两种态度的?
贝淡宁:我相信中国理当获得一些掌声,它(重新)树立起了一种“贤能政治”模式,为其过去三十年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不过,如前面所说,中国实现其“贤能政治”的方式并不完美,政治改革仍当继续进行。比如说,基层选举应该更为自由、公正,具有竞争性;而夹在中央与基层之间的政府应当试行更为多样化的方式,推选出领导人。我的观点同中国的舆论主流一致。不同于大多数西方观察家之处在于,我不认为各级政府一人一票制选举能作为判断中国政治进程的终极标准。
此外,我之所以对压制和审查持批评态度,不单只出于一般言论自由方面的考虑,还因为这种举措会侵蚀“贤能政治”的根基。打个比方,社会舆论和媒体在揭露领导的不当行为以及批判腐败官员时,应该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否则被提上高位的就是那些害群之马了。方今中国社会在财富与智识层面都渐上层楼,相应的,民众也该得到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但中国决不能将政治金字塔的顶层开放为多党派竞争及一人一票制的试验场所,因为一旦选举制民主政治占据了最高层,经营数十年的整个贤能政治系统将毁于一旦:千锤百炼自这一系统的公务员们,其上升之路取决于实干,而非花言巧语。从某种意义出发,为使“贤能政治”体制更具民主的合法性,也许有必要就此展开一场全民公投。这样一来,对“贤能政治”的批评声音会被民众而非政府所止息,而原本用于稳固这一系统的审查与武力压制,也会少去用武之地。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在何时转向“精英政治”的?它肯定不始于脆弱的华国锋时代。这一转变是同邓小平的改革一道开始的,还是再要晚一些?
贝淡宁:它是在邓小平改革初期就开始了的。当时政府意识到,要运转一个现代化国家,掌舵者就必须是那些经过拣选、能力超卓的“精英化”政治领袖。从那时起,通过公务员考试和对低层级政府进行各层面的政绩考核等手段,这一做法就逐渐被制度化了。
在“精英政治”系统中,选拔的重要性等同于民众选举。但如果不通过民众选举,领导者又如何能被选拔呢?
贝淡宁: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以社会学、历史和哲学为依据,就一个广袤、和平、现代化的(非民主制的)“精英国家”政治领袖最应具备的品质提出了建议,我还在其后提出了相应的操作机制,以增加选拔此类领导人的可能性。之后,我又以这些最适用于一个广袤、和平、现代化的“贤能政治”体系下之领导人的能力、社交技巧以及美德来衡量中国现存的“贤能政治”体系。我的结论是,中国能够并且应当改善其“贤能政治”体系:它需要增加更多能够有效测试政治上所需才能的考试;需要提拔更多的女性领导人,增加领导者具备某些社交技巧的可能性,以促进政策的有效制定;它还应当更多地去系统化地运用同侪评议体系,好让那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得到提拔。
那么那些挑选者又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
贝淡宁:在开展这一进程时,必须在政治因素之外加入科学因素的考虑。比方说,谁来判断这些政治试验是否成功(包括提升低层级政府领导人的新方式)?在目前,这一过程并不十分透明,高层级领导人的评判仍是主要依据。但如果从国家顶尖高校里随机抽取一批教授,让他们在深思熟虑之后,就政治试验的成功或者失败作出判断,此举也具有合理性。要知道,中国历来敬重知识精英,即便最高层领导人依旧掌握着政治王牌,这些知识精英的判决仍会在政治上打开一个不同的局面。
这种“精英治国”体系如何确保挑选者与被挑选者都能负责任?
贝淡宁:我在第三章里讨论到了如何在不诉诸选举民主的前提下,确保政治最高层的责任制。对高层领导而言,任期和年龄限制了他们的权力(如果他们试图改变这套制度,就会引起担忧)。腐败问题可以通过诸如此类的操作机制解决:在提拔过程中引进同侪评议,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提高公务员工资,再有就是完善道德教育。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魔棒,不过是加大法制与道德教育的投入——少一点马克思主义,多一些儒家思想——将大有裨益。
那么这些有缺陷的民主政体(比如说欧盟和意大利等许多成员国)能从“精英政治”里学到什么?它们又如何将“精英政治”的要素吸纳进自己的体系?
贝淡宁:我要重申一句,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我认为西方国家一人一票选举政治领袖的制度不会受到挑战。但这些投票人也许能从“精英政体”的国家用以判断政绩的某些标准里得到一些启示。我在新加坡教过一个学期的课,当时有个很富创新精神的意大利博士生,叫做艾琳娜·兹立欧提的,提出欧洲选民们必须在通过关于两个欧洲政党的多项选择测试之后,才能投票。我们就此在《赫芬顿邮报》上合作发表了一篇评论,她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想法。在我看来,这是个绝妙的提议,就算现在看来不合政治实际,谁又说得准之后的几十年里会发生什么?当人们对选举政治领袖的方式有了更为多样的看法以后,能拿出现成的好建议,总归是有益无害的。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模式(精英政治)能成功输出吗?如何使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优异处不受其弊病所侵染?
贝淡宁:我在本书终章提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是能够输出的,但如果要输出整个的体系,载体就必须选择那些有着“贤能政治”传承、地域广大,并且尚未在政治最高层采用一人一票制的国家。比如越南。当然,制度输出的最佳方法莫过于作出表率,中国必须在一个开放、宽容、人性化的政治环境中,继续完善其“贤能政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