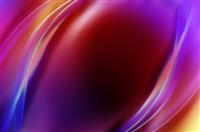几千年来,只有帝国才能终结乱世,这是人类政治的悲剧。牛津大学历史学者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曾做过这样的表述:“纵观世界历史,帝国主义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人类政治的默认模式(default mode)”。由于地理禀赋的不同,建立强大帝国所需要的实力从来不是在各国之间平均分配的,因此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土地进行统治并不罕见。不过,对于一个强国来说,对弱小国家的征服很容易引发自负心理、军国主义、僵化的官僚主义以及过度扩张的心态。在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看来,帝国的建立同时也就意味着那个国家的堕落及其民族文化的衰败。不过,对于英法两国来说,他们曾建立的那些帝国在崩溃之前却并未落入这样的窠臼。
如果帝国的存在是世界的常态(即便帝国最终难免以悲剧收场),导致帝国可持续存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能够使一个帝国免于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所说的那种帝国顽疾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国家制度呢?其实,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颠覆活动(campaign of subversion)、欧盟的成立以及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都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若要避免跌入帝国陷阱,人们需要大战略(grand strategy),而为了制定大战略,各国政治精英们一直在冥思苦想着。
中国:受到地理因素影响的、开明的威权主义
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解答上述问题的一种思路,而欧盟和美国则提供了另一种,两种思路各有千秋。
中国和俄罗斯是陆权思想和威权主义的继承者。这两个国家的扩张模式局限于地理范畴而非思想领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细腻的手段。事实上,他们都是非常难以对付的国家。
在中国领导人的认知里,明清时代(从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原注)的近代亚洲处于非常稳定的帝国朝贡体系之中,而且这一体系比以强调欧洲各国相互制衡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要稳定得多。南加州大学政治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指出,“朝贡体系内在包含着中国的承诺,即中国不会欺侮那些承认其权威的弱小国家”。因此,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帝国秩序不仅意味着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而且还意味着“中国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以及各方在此问题上的共识”。由于中国当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使亚洲保持了几个世纪的相对和平,而且这一秩序在当时是受到各方认可的,所以当今的中国领导人认为,以一种全新的、更加细腻的战略恢复地区秩序的和谐是无可指摘的。
中国当然不是一个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democracy),但中国也并非一个极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这正是中国的魅力所在(that is precisely its appeal)。我们只是过分简单地将中国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贴上“独裁”(dictatorship,这是个源自摩尼教的词语——原注)的标签。中国的独特制度不但使社会秩序得到维护,而且使国家政策具有可预见性。另外,在中国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在中国智库学者群体内部甚至在中国普通百姓内部,关于各种问题的各种讨论的确是存在的,这已经不符合我们对“极权”或“独裁”的定义。
更进一步来说,作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希望恢复地区和谐秩序的信念其实也体现着他在更高层面的追求,而具有这种追求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成功伟大国家的典型特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沿袭的是中国古代王朝通往伊朗和欧洲的商贸路线,这一战略使中国有能力为中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创造新的前景。在这一新的前景里,上述国家将有机会摆脱目前的经济落后状况、政治不稳定局面以及地理上的孤立感。
我们一般都认为中国是美国在经济领域的挑战者。其实,经济领域仅是其中之一。中国已经在根本的思想领域向我们发起了挑战。至少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国独特的制度为其人民甚至周边邻国提供了坚实的、可靠的发展保障。习近平并非独裁者,他在确保国家不落入失序状况的前提下为人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并使经济增长得以延续。这一切实际上体现了威权主义对我们的某种吸引力。中国具备俄罗斯所没有的制度优势(institutional strengths),而习近平对中国的领导与萨达姆对伊拉克的独裁统治或阿萨德对叙利亚的专制统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
不过,鉴于中国曾由于遭受西方和日本的欺侮不得不经历长达200年的衰落和混乱,以今日中国的经济活力和强压内心的忿恨(seething resentment),欲避免傲慢自大的心态(arrogance)颇有难度。而傲慢对中国来说将是致命(fatal)的。用耶鲁大学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话来说,傲慢将导致中国“过度使用自己的实力”。而且在这方面,中国可能很难控制自己。过去10年里的经济成就可能使中国过于自信,以至于中国会将“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到未来10年的经济增速所无法支撑的程度。也许,中国距离传统上所谓的“帝国陷阱”并不遥远。
俄罗斯:受到地理因素影响的、不开明的威权主义
至于俄国人,也许他们将戴着滑雪面罩的暴徒派往乌克兰的手段看起来有些笨拙,但他们在网络上颠覆民主政府的行径却巧妙得多,不但成本极低而且很难留下证据。更进一步来说,俄国人并不具有在中东欧地区重建华沙条约组织的意图,那只会暴露出大国的自负以及帝国主义的传统缺陷。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在那一地区做个搅局者。在叙利亚,俄国人十分谨慎,避免派出地面部队。在其周边地区,俄罗斯是富有侵略性的,但这个国家同时也是非常谨慎的。从地理角度来讲,俄国人希望将自己的影响力覆盖到前苏联的所有地区,但又不愿冒任何风险、不愿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寻求的是影响力的提升,而非实质上的占有。这种后帝国战略(post–imperial strategy)是非常明智的。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中东欧地区的颠覆活动虽然对势力范围的边界有所顾忌,但他的这种后帝国行为其实体现了其内心对与自由民主国家展开对抗的执着和痴迷,而且其中并没有更高层面的追求。冷战以苏联解体收场在他的心中引发了怨恨,而他的网络战策略不过是受到了这种怨恨的驱使。普京总统若没有对更高层面目标的追求,那么他的行为就失去了指引,俄罗斯后劲不足的国家战略就注定会以失败收场。
历史已经反复告诫我们,帝国要想延续下去,就必须(至少在内心深处)具备一个与文明教化有关的更高层面的目标(a higher,civilizing objective)。威尼斯和不列颠都认为自己通过贸易活动造福了全世界;罗马人相信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路基础设施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哈布斯堡家族(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主要分支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从1282年起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结束。该家族是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统治地域最广的封建家族——观察者网注)和土耳其人则认为保持对其君主的忠诚可以避免不同族群互相残杀。中国人在更高的文明层面也有自己的理想,但俄国人却没有。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缺乏强大的制度支撑(not buttressed by strong institutions)。俄罗斯也不像中国那样可以凭借“一带一路”倡议给各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希望。这就是为何中国能够以某种方式对美国发起挑战,而俄罗斯却不能的原因。有时候,一种威权主义与另一种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比威权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还要大。
欧盟:一个实质上的帝国
欧盟的成立是对本文开头部分帝国之问的最具创新性的回答。耶鲁大学历史学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曾指出,欧盟十分强调合法性和小国的利益,这把它从传统的帝国主义范式中解放出来。然而,斯奈德教授还指出,欧洲的历史是极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因此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那些东欧国家)若不生存在欧盟的羽翼之下,他们便毫无未来可言,而欧盟这一整体其规模和内部的多样性完全符合一个帝国的特征。实际上,欧盟是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帝国“天下大同”(cosmopolitanism)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因此欧盟完全有潜力在免于陷入自负泥淖的前提下在整个欧洲大陆发挥一个帝国的功能。不过,由于受到俄罗斯后帝国行为模式的威胁,欧盟很难完全保障自身的安全,这项工作最终要由美国承担起来。
由于欧债危机以及随后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欧盟在某种程度上也学会了谦逊的美德,意大利总理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最近的言论就印证了这一点。今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真蒂洛尼总理曾警告欧洲同胞们要提防“数字时代的精英们惯有的傲慢心理”。在强烈批评民粹主义的同时,法国总理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达沃斯提到了要尽力满足那些被民粹主义势力拉拢过去的民众的诉求。如今,欧洲的领导人们都已经意识到,只有让布鲁塞尔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只有改变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作风,欧盟这个准帝国的上层建筑(the quasi-imperial superstruc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才能继续存活下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正是由于当下的这种濒死体验,欧盟其实正站在历史的节点上,若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欧洲人便可以掌握未来。欧洲的领导人们如今为了避免悲剧发生都做好了最悲观的准备,这是他们在危机发生前从未做到的(至少没有做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鉴于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与作奸犯科密不可分,它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而中国的模式之所以在中国可行是因为它内在地包含有在西方不被认可的受控而有限的个人自由。欧盟若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在保留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前提下,成为一个去精英化的西方民主政体。欧盟必须做出十分审慎的调整(measured adjustments),这对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
20世纪以意识形态(ideology)为主题,而21世纪的主题将是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意味着处于竞争之中的不同制度之间的区别比二战以及冷战时期要微妙得多。摩尼教传统观点的问题在于,它认为独裁和民主两者之中仅有一方能够胜出。不过实际上,可能最后双方都是失败者。也许,将这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那个国家才能获得最终的竞争优势。
美国:命中注定的人类领袖?
由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对于该秩序所倡导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还是颇有自信的(至少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前的确如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后帝国时代这种自信仍然能够长期延续下去。在很多政策实施者看来,奉行帝国主义往往意味着一种教化全人类的使命感。
哈佛大学的奥德·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教授指出,无论上述关于帝国主义的观念带有多少种族主义和伪善的色彩(尤其在黑暗的欧洲殖民历史当中),这种观念的确是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人们甚至会产生一种“使命感和自我牺牲感”,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就曾深陷此类情感之中。事实上,冷战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冲突,不过双方都声称自己所扮演的是另外的更加崇高的角色。更进一步来说,由于美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遍布全球,它需要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撑,这必然导致巨额的军事开支。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观点,无度的军事开支必然使帝国走向衰落。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以及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的行动都带有某种帝国远征的色彩(hallmarks of imperial expeditions),对于一个帝国来说,入侵某个国家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其进行统治。当然,即便在世界尽头,美国也必须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但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巨额战争开支和数不尽的裹尸袋压垮这个国家。这是很难的事情,比听起来要难得多。毕竟,为了捍卫价值观而发动一场战争从表面看起来的确是有必要的。
作为总统,特朗普已经决定不再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帝国战争给予支持,他希望在不推翻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前提下击败“伊斯兰国”武装,特朗普如此决策也是顺应了华盛顿外交团队中某些人的呼声。另外,特朗普极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和狭隘的“美国优先”,这实际上使很多有切实作用和积极意义的外交政策遭到了废弃,这些都是美国在衰落的迹象。更进一步来说,他对军事力量的崇拜和对外交机构的轻视使人联想起所有军事帝国的命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曾用“一具穿着盔甲的尸体”来描述过度崇尚武力的亚述帝国。
美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100年前,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指出,北美大陆是亚欧非大陆(Afro-Eurasia)周边“诸岛”中条件最好的一个,这一块大陆不但能对旧世界(the Old World)施加影响,而且在地理上有一段距离,能够受到两个大洋的保护。因此,如果美国能够获取某种形式的准帝国权力(variation of quasi-imperialism right),那么这个国家仍将继续主导世界。在近四分之三个世纪里,美国似乎首次无法为世界提供以推动人类进步为目标的“宏大构想”。对美国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其他方面都无法与之相比。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帝国时代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领导力正是建立在以推动人类进步为目标的“宏大构想”之上的,征服其他国家或占有其土地的能力已经不再像过去那般重要了。
最后的思考
我们不应认为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是人类政治形态发展的终点。只有在内能给予其人民更多尊严、在外能为其附属国和盟友提供更多希望的制度才能够在这场制度竞争中获胜。的确,威权主义在当下已稍占上风,原因并不在俄罗斯,而是在中国。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高明的大战略(well-orchestrated grand strategy)使其获得了优势,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普选之上。
不过,我们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数百年来,美利坚合众国一直是一个能够启迪人类灵感的民主国家。虽然当下这个庸俗的充斥着数码视频的新时代鼓励多元话语,其实这反而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撕裂而且还使客观真理遭到掩盖,也许业已展现威权主义姿态的特朗普是这个庸俗时代所孕育出来的怪胎?还是说,他仅仅是美国社会里偶然出现的个例呢?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然是后帝国时代里世界各国的最佳选择。中国的模式虽然十分诱人,但它本质上是个圈套,因为它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落幕和西方(不仅仅是美国)的整体性衰落。我们应该将开明的威权主义视为一项挑战,我们绝不能认命向其屈服(we should take enlightened authoritarianism as a challenge; not as a fate)。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8年3月5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