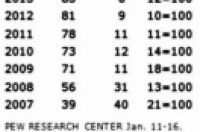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发展和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污染、交通拥堵、资源枯竭、疾病控制、贫困化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府应对上述问题的总体方案。在很多学者看来,行政能力和公众参与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治理水平的关键因素,但近年来人们在反思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状况时,对过去流行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替代性方案,即法治。在强调行政能力和公众参与之外,法治被认为能够弥补原有治理模式的制度缺陷,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公众参与意识较弱的情况下,强化法治更有益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当下,我国学者和政府机关对法治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事实上,相较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来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行政能力被视为影响国家治理的一个关键变量,“弱国家”会极大地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法律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政治学家断言,国家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制度吸纳能力低下和行政治理的低效。亨廷顿发现,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因为政治转型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相反,在那些制度化水平低的社会里,脆弱的制度无法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致使人们在选举之外寻求政治表达的途径①。福山认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在制度供给端设计一些能够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扩大执法范围的制度,例如,重新设计公共部门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对政治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重建合法性基础,推进公民文化建设等②。
但是,以行政机构为主体的治理结构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委托—代理的难题。这个难题根源于上下层级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常,代理机构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强化自身的议题,减少承担的责任,挤压委托人的目标,甚至在执行上级指令时“偷工减料”③。由此,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强弱就成为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④。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行为受到有限的责任制的约束,源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以及源于国家机构之间的责任约束都相对薄弱⑤,因此,委托—代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全国性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国家治理的效率。
由于历史与国情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治理尤其依赖行政力量。为了提高国家治理的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行政机构进行过多次改革。这些改革既涉及纵向的央地关系,也涉及横向的政府部门间的关系。纵向改革以增加地方政府自主权为目标,给予地方更大的行政、人事、财政以及地方事务管理的权限;横向改革以增强部门间的合作协调为目标,提高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整体效率,构建“无缝隙”的公共机构。客观地讲,上述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了积极的行政条件,在促进地方发展的同时,提高了公共管理的绩效。不过,由行政规模和结构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样存在于政府间关系当中。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五级行政层级结构中,即便每级政府百分之百地执行中央政策,来自最高层的政策任务在乡级政府层面最终也只能完成百分之七十左右,另百分之三十的政策任务由于科层制客观存在的问题而被消解掉了⑥。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虽然也强调了基层政府在实际执行中偏离中央政策的主观原因,但是,在解释基层政府之间“共谋现象”的时候,有学者仍强调了政府内部存在的制度性问题,也就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论者认为,存在于政府内部的三个悖论——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悖论、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的悖论,以及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的悖论——导致了基层政府之间制度化的、非正式的“共谋”现象,鼓励基层政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高级别政府的政策指令和检查监督⑦。
为了减少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地方的执行偏差,中央政府在改革初期就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维持一种有效的责任关系。干部岗位目标考核制度是约束地方干部、维护中央权威的一个主要机制。岗位责任目标被分解为“硬指标”与“软指标”,前者主要包括经济增长、计划生育与社会稳定等,后者包括的内容则更多,约束性也相对低一些。对此,基层政府会在“硬指标”与“软指标”之间进行权衡,前者的执行情况通常要好于后者⑧。基层政府对上级政策“选择性地执行”⑨或“非均衡地执行”⑩,是因为自主权的扩大推动了地方利益格局的形成,促使地方政府设法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同时抵制中央那些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政策。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策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地方社会的执行力,降低了国家对公共问题的治理能力,也反映了中央那些旨在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措施效果并不理想。
近年来治理理论更强调社会参与能够弥补国家能力低下导致的治理不善问题。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托克维尔研究美国的民主时就指出,乐于结社的自治精神填补了美国当时弱国家(特别是弱联邦)的缺陷,无意中为社会带来了繁荣与强盛(11)。社会参与对国家治理的贡献还来自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由信任、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其中,信任是核心内容。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合作本身又会进一步增加社会信任。在帕特南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同属于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意大利北部比南部更加繁荣、有序和民主(12)。在跨国比较中,福山同样发现了信任的重要性,同时解释了不同国家经济繁荣和政治发展的差异性(13)。善治理论承继了托克维尔的观点,强调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认为民间组织是善治的社会基础,不过,不同于托克维尔,善治理论更强调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制约功能(14)。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主要有两种形式: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前者强调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应当在数量上有所限制,在组织结构、组织目标和资金来源方面更依赖于国家;后者鼓励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在组织形式上倡导独立于政府之外(15)。来自于西方的这两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丰富的样本。
不过,以社会组织参与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否则,治理会陷入无序和混乱之中。第一个条件是,政府必须提供社会参与的正式渠道,如选举、结社自由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即使有相关的制度安排,也由于多种原因或者被闲置或者被扭曲了。第二个条件是,社会需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社会组织积极且善于合作,同时社会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等)进行治理。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缺乏自治传统,并且由于经济落后,社会组织也难以在民间募集充足的资源独立应对各种治理难题。第三个条件是,社会组织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参与到治理当中。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贫穷落后以及社会建设滞后,社会组织在治理方面拥有的专业知识也都非常有限。
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后获得迅速发展,介入地方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高涨。这些参与国家治理的社会组织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垄断式、垄断—自治式和自治式(16)。前两种类型是国家合作主义在我国本土化的典型,也是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主体。前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由于与政府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参与能力强,承担了许多政府转移过来的行政职能。第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尽管在内部组织管理上独立于政府,但也必须借用政府的平台和资源才能真正地获得参与的机会。例如,那些具有很强民间色彩的环保组织在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自我定位就是政府的“帮手”和“合作伙伴”(17)。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草根动员”成为普通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另一种渠道。“草根动员”通常是一种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行动的诉求主要围绕个人际遇,抗议的对象一般指向基层政府部门;为了降低政治风险,“草根动员”的参与者大多采取和平与理性的方式,集体诉讼是比较常见的形式(18)。需要说明的是,“草根动员”通常既无组织也无政治目标,对社会秩序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倡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治理同样也面临着诸多难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效。第一个问题源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利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而言,地方政府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因此,这种利益对立的情形有可能演变为真实的对抗事件,个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是这种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参与治理的途径还比较单一、稀缺。尽管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旨在使地方政府开放决策过程和履行行政责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出于多种原因对此贯彻得并不彻底,特别是在政府利益和民众利益有所冲突的时候,民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有时还缺少强有力保障。第三个问题是由于地方政府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为了“维稳”而可能抑制民众合理的维权行为,从而降低了“草根动员”对于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
在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体系中,法治是一个主要的变量(19)。在福山强调提高发展中国家行政效率之时,普拉特纳则坚持认为国家治理的改善有赖于法制的完善。在普拉特纳看来,官员的责任约束与化解纠纷的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只有在法治之下,公众参与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参与的效能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20)。由此观之,法治应是上述两种治理模式的补充和保障;没有基本的法治环境,行政治理与社会参与的绩效都会大打折扣。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仅仅重视选举制度建设、开放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是难以解决贫困、疾病、社会秩序等公共问题的;在很多情况下,民众会由于上述问题解决不力而放弃对民主制度的支持(21)。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民主试验失败的重要原因。
法治紧密地与国家治理能力及公民参与潜力联系在一起(22)。行政机构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组织,如果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缺乏刚性约束,政府责任问题就会成为削弱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律和制度的规范能够有效克服行政组织之间的结构性难题,强化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责任(23)。在法治环境下,由于获得了正式的参与渠道,社会也会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和参与热情,不仅能够监督政府的治理行为,而且能够积累无可替代的治理资源,更重要的是,民众还会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逐步树立起适应治理需求的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24)。因此,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法治不仅能够为社会参与提供通道和保障,而且还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平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颁布和实施了覆盖民事、商事、刑事、行政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建立起全国性的司法审判系统和律师制度,司法职业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规范政府行为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25),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简言之,当下法治国家的建设已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和条件,在日常治理中,法治所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为国内外投资方提供日益完善的产权保护和稳定的政策环境,促进了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26)。(2)为社会矛盾的化解提供制度性的平台和通道,成为社会矛盾的有效“缓冲器”(27)。(3)抑制了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法行为”,为公民行使监督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8)。(4)使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保护有法可依,相关的法律规章正在不断完善之中。(5)公民的权利意识在司法实践中显著增强,对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知晓度和利用法律保护个人及集体利益的积极性逐步提高(29)。
值得强调的是,推进以法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政治上低成本、高收益的事业。完善法制体系,建设法治国家不仅可以避免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带来的风险和压力,而且通过依法行政将权力关进司法的笼子,积极贯彻人民司法精神,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与民众信任度也将得到极大提升(30)。
虽然中国当前法治国家的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基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概言之,这些有待改进和完善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在司法实践中,党和司法部门关系的制度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通常表现为“以党代法”和“权大于法”,这种关系状况既影响到司法机关治理职能的正常发挥,也影响党的建设;司法机关的监督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司法机关和司法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有待提升;尽管行政诉讼改革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和行政领导干部的监督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还比较淡薄,行政机关纠错的自觉性还不够高;普通公民通过司法途径表达诉求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对司法办案的满意度仍然较低,“信访不信法”的风气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司法机关化解纠纷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一讲话有力地表明了国家治理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即将法治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以法治保障善治。由此观之,今后应进一步推动法治中国的发展,并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强化党对司法系统的政治领导,确保司法机关的工作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党对司法机关的政治领导要坚持以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为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党的领导体现在引导司法系统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公民权利的保护作为评价司法工作的核心标准;在重大问题上,党要善于领导司法部门进行合理、公正的决策,监督司法决策的过程。
第二,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两院工作必须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在组织关系层面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具有全面的监督权。除了一年一度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外,法院和检察院在重要案情和重要决定方面应定期地向人大常委会做汇报。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应进一步制度化。司法机关对办理的热点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应举行听证会。
第三,进一步推进行政诉讼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办理典型案件,有力推进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合理地运用司法权威,严格执行行政诉讼中的法人应诉制度,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强化行政机关的责任意识。司法机关要在国家治理的重点领域加大行政诉讼处理力度,在土地、环境、城市建设、食品安全等领域,敢于向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问责,积极地通过诉讼化解影响重大的纠纷。司法机关还须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机制,为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司法渠道保护公共利益,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
第四,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和完善开放的诉讼受理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公正的审理,使司法制度成为公民维权和参与治理的基本通道。实践证明,司法机关既是约束公权力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救济。只有向所有公民无条件开放,司法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上述治理功能。而且,向所有公民平等地开放诉讼通道,本身就是衡量法治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为提高办案质量,司法机关应改革内部考核制度,以办案质量为主要绩效考核标准,降低办案数量在考核中的权重;同时,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人口规模和财政状况,适当在财政拨款、人员编制方面向司法机关倾斜。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不仅行政治理的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社会参与也会在法制的规范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①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②Francis Fukuyama,State-Building: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p.29.
③John Brehm and Scott Gates,Working,Shirking,and Sabotage:Bureaucratic Responses to a Democratic Public,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④Francis Fukuyama,"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2013(3).
⑤Guillermo O""""""""Donnell,"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in Andreas Schedler,et al.(eds.),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
⑥Andrew H.Wedeman,"Incompetence,Noise,and Fear in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1(4).
⑦参见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⑧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3(1).
⑨Kevie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1999(2).
⑩Christian Gbel,"Uneve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The China Journal,2011(1).
(11)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2)参见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14)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15)Philippe 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1974(1).
(16)参见谢岳、葛阳《市场化、民间组织和公共治理》,《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
(17)参见赵秀梅《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Peter Ho and Richard L.Edmonds(eds.),Embedded Activism in a Semi-authoritarian Context: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Routledge,2008.
(18)参见谢岳、党东升《草根动员: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19)Daniel Kaufmann et al.,"Governance Matters VI: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6",Working Paper of the World Bank,2007.
(20)Marc F.Plattner,"Reflection on """"""""Governance""""""""",Journal of Democracy,2013(4).
(21)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Democracy in Decl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5.
(22)Guillermo A.O""""""""Donnell,"Why the Rule of Law Matters?" Journal of Democracy,2004(4).
(23)Guillermo A O""""""""Donnell,"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in Andreas Schedler,et al.(eds.),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24)Elizabeth J.Perry,"A New Rights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Democracy,2009(3);Mary E.Gallagher,"Mobilizing the Law in China:""""""""Informed Disenchan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sciousness",Law & Society Review,2006(4).
(25)Dingjian Cai and Chenguang Wang,China""""""""s Journey toward the Rule of Law:Legal Reform,1978-2008,Brill,2010.
(26)Randall P.Peerenboom,"Seek Truth from Facts:An Empirical Study of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in the PRC",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1(2).
(27)参见张文显《联动司法:诉讼社会境况下的司法模式》,《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
(28)Minxin Pei,"Rights and Resistance:The Changing Contexts of the Dissident Movement",in Elizabeth J.Perry,et al.(eds.),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and Resistance,Routledge,2003.
(29)Mary E.Gallagher,"Mobilizing the Law in China:""""""""Informed Disenchan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sciousness",Law & Society Review,2006(4).
(30)Wei Pan,"Toward a Consultative Rule of Law Regime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