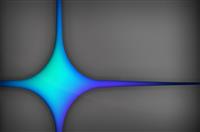
绿色和平组织从1971年成立,留给人们的印象大多是激进、顽强和坚定。雍容说,在中国做NGO,最大的收获,就是与这个大环境共同成长,所以,态度是激进的,而行动都是理性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了解国际新闻的途径,只有从黑白电视机里看《新闻联播》的最后五分钟,时间太短,往往印象深刻。很多人都记得在公海上向日本捕鲸船示威的小船,身着统一服装的人们,在高压水枪的喷射下,依然艰难的打出标语,用船身挡住大船,保护鲸鱼生活的区域。那时候中国人几乎没有听说过NGO这三个字母,但隐约地了解他们是在为动物做一点好事,有着典型的西方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事实上,这并非“个人”行为,也许有细心的观众会记得这个组织的名字——绿色和平(GREENPEACE)。
时隔二十多年,我们从不了解世界,到被世界迫切地想要了解,发展之快不言而喻。国际性的NGO组织,也像跨国公司入驻中国设立分部一样,开始了它们的中国之旅。从最早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到新千年以来在北京建立办公室的“根与芽”、在天津设立儿童村的“菲利浦海德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的NGO组织在华已有几千家。在这些组织里,也包括让上世纪80年代的观众们印象深刻的绿色和平。
摸着石头过河
很多在改革开放政策下自主创业的人,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都有很深的体会——它代表着环境与政策的不确定性、脚踏实地的精神、抛开一切顾虑的洒脱。同样有所体会的,还有绿色和平组织的施鹏翔。1997年2月14日,一个平常的情人节,绿色和平组织在香港建立中国境内的第一间分部。
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将东江水污染的案例分析报告递交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政府,次年,香港特首将改善东江水质的措施纳入施政大纲。在问及当时对北京办公室的考虑时,施鹏翔诚恳地说,事实上,谁也不清楚当时内地的环境合适不合适建立办公室,并且在香港的前两三年,首要的任务是筹得项目经费,但也已经开始着手做一些和内地相关的事情,比如出版《中国环境报告1998》等。
最初的联络,要归功于当时在做转基因项目的同事。他为转基因项目在民族大学设立了一个联络点,“以项目带动机构发展”的策略被确立,摸着石头过河的绿色和平来到了内地。
磨合:互动中的共同发展
2002年,中国已经有不少的环保组织,包括一部分国际性NGO,在做的无外乎是环保教育与概念普及。但很快,绿色和平就体会到了其间微妙的原因。
负责食品安全和农业的项目主任罗媛楠告诉我,2002年最开始做转基因食品时,没有人对“转基因”三个字产生敏感的态度,这是一个很难和公众沟通的项目。绿色和平把市场上的食品企业使用转基因原料的信息编纂成册,反馈给各大企业,希望获得他们的承诺。一部分跨国企业立刻有了回信,表示会在一时间段内不再使用转基因成分。但是,本土的国有企业甚至不清楚NGO是做什么的。罗媛楠说,发传真到国企去,几乎都转不进去,没有部门负责这件事,报告常常是石沉大海。
做公众项目的王珏说,那时候绿色和平在新浪做一个活动,是需要付费租赁广告位的,主流的网络媒体并不知道绿色和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谈公众活动项目很困难。
种种这些,让绿色和平体会到在中国做环保的尴尬。因为,7年前的中国,还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环保事件,没有媒体普遍报道的大规模因环境原因发生的群体事件,没有因环保问题频频举办听证会——这些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环境问题不严重,而是它没有具体化成一个重大事件进入公众的视野。
然而,紧接着的2004、2005两年,怒江水电站之争、圆明园渗水事件举办了历史性的听证会、松花江流域大面积污染引发东北地区饮水危机,这一系列大事件将环保二字推到了政府、主流媒体、公众的视野里,成为那两年的关键词。以此为转折点,中国人开始在危机中体会到环境保护的需求离自己越来越近。同时在2004年,绿色和平与《南方周末》的记者一起调查金光纸业集团毁林事件被刊出后,立刻由捕鲸船时期的印象重回公众视野。环境危机的曝光与国际性NGO组织与强大利益集团的博弈,使得民众对NGO有了更新的了解,人们发现,这个具有英雄主义情怀的群体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新闻中走了出来,离中国很近,离生活很近。
到目前为止,绿色和平在和许多超市合作,共同检测和抵制转基因产品,一些超市的进步态度让罗媛楠很是惊讶。她常常带着要打硬仗的心情前去沟通,可是超市负责人却早已开始自发的检测,并非常希望和绿色和平合作,以获得更多的技术支持。王珏也表示,现在,绿色和平的公众项目和网络的合作非常丰富,各大门户网站都曾为绿色和平的活动开辟专区,民众的声音通过电邮等形式大量的反馈给项目组,大家对环保议题关注的内容也从上世纪80年代仅有的保护森林、保护水资源转变到抵制超市残留农药的水果、寻求更多减少碳排放的方式等。
双赢的潜力
NGO的工作受限制这么多,在中国做环保还有潜力吗?
谈到限制,身份焦虑一直是许多进入中国多年却仍未注册的国际性NGO组织要面对的难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挂靠才可以注册,使得很多NGO一直是“黑户”——租用办公室,员工的劳务合同签署困难重重。绿色和平组织也是这样的“黑户”,政府与公众关系主任雍容则认为这对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身份的信任度,完全可以通过行动来证明。2008年的《奥运环境评估》,客观真实地表述了北京当时的环境状况,优缺点明显。报告影响很大,奥组委颁了一个“突出贡献奖”给项目组。作为政府的一个正面肯定,雍容觉得NGO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称之为 “用行动说话,用事实争取公信度”。此时,身份焦虑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环保的潜力,森林资源主任刘兵给我举了一个例子。2005年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家具的木材如果来自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片森林,但价格会涨10%,你会买吗?66%的受众选择会买。这个结果令大家都很惊讶,说明中国民众对环保意识的消化程度进步非常快。
但是谈到真正发展的潜力,更多的来源于整个国家的变化。当气候问题、能源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时,诸国的目光也同样会在中国身上多作停留,作为一个大国,与环境相关的决策除了影响十三亿人口,几乎也影响着全世界。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痛心陈述严峻的环境状况,随后,“节能减排”的指标成为十一五计划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从决策层面上树立了从源头解决能源问题的原则——这和绿色和平一直倡导的 “在前端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一致的。
环境,成为中国政府、公众舆论与NGO的共同关注点,NGO与政府的互动也越来越紧密。2005年,政府起草《可再生能源法》,邀请了绿色和平给出专业性意见。翌年人大通过法例,部分意见得到采纳。施鹏翔回忆起这件事来,还是很激动,他说,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可以在美国发生,就算是在欧洲,以绿色和平的影响力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可以做到,中国没有像美国或欧洲那种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和代表他们的专业说客,某种程度上,NGO的意见可以更容易被传达和被采纳。
与此同时,政府信息的公开化不断的加强,企业对于自身社会责任感的重视,使得NGO在中国开展环保工作,较之以前空间更大,也更加融洽。
中国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后,逐渐从最初疯狂逐利的状态慢慢回落,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也越来越丰富,不再单以金钱论成败。虽然物质仍然是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更多的人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反思,这种反思也渐渐的不局限于精英层面——厦门市民反对PX计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谈论环保的议题,大概会越来越有潜力吧。这潜力是绿色和平的,是为环保劳心出力的所有NGO组织的,是所有民众的,也是整个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