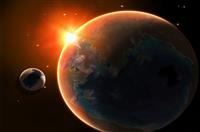复兴村妇女互助组在开展活动,她们手里拿的是“小母牛”的12条基石。
胜利村村民自己动手修路,这条路由香港某NGO资助,完全尊重村民意愿。
按香港某NGO的要求,村民大会将村上富裕的、中等收入的和贫困的农户分成三组来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定下个规矩:开会时干部不能发言,选项目最后交由村民大会投票决定。村民找来几口大碗和一堆苞谷粒粒,把治水、修路、农网改造等村民的需求写下来贴在碗上,一字排开,村民排队一个个地进来投票,想做哪个项目就在哪个大碗里丢一颗苞谷粒。
四川地震后3年,一个侧重恢复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一个侧重农村生计发展,香港某NG O和国际小母牛在灾区推进着不同的重建行动。
在绵阳、广元、德阳、雅安等9个市/州,及彭州、北川、剑阁、江油等9个县区,香港某NG O和“小母牛”分别参与了54个村和的63个村的灾后重建。今年,香港某NG O也开始转向结合防减灾的综合产业发展项目。在广元市利州区的龙潭乡,胜利村的香港某NG O道路援建项目已完成,另有复兴村等6个“小母牛”的养猪产业发展项目正在进行之中。它们给当地留下了一套参与式的观念、制度、组织,甚至生活方式。他们说“政府是正规军,我们是游击队”。援建3年,这些国际NG O组织又给当地政府留下了什么?
南都记者 吴珊 发自广元、成都
胜利村的路
“不干事还好,一干啥事儿都冒出来了。”决定集资修路后,由于利益难以协调,一个队长的头甚至都被村民打破了
从党家桥到胜利村委,3.9公里,一条3.5米宽的水泥村道被命名为共青路。沿着山坡,它把外来的车辆引入村庄,再把沿路的农户和村委会连成一线。延伸的道路紧密而沉实,就像这3年来村民不断生长的自信心一样。
5月2日,暴雨冲垮了共青路下的一小段路基,村民们都自发地出来修路。
胜利村离广元市区只有5公里,周广平每天进城去做建筑工,骑摩托车只需要30分钟,一年下来能攒下近两万块钱。村里的农户几乎家家都开始种菜,用摩托车或小车运到广元的菜市场,一亩地一年大概还能收入两三万块钱。
对城郊的农村来说,路就意味着生计。2009年共青路竣工之后,胜利村很快增加了20多辆汽车和几十辆摩托车;而2009年之前,村民们一年里还有半年要在烂泥巴路里挣扎着过日子。
广元每年5到10月都是雨季,雨水常常把胜利村变成一座孤岛———在城里务工的人、猪饲料和猪贩子等进不来,准备进城务工的人、村里的蔬菜、水果、生猪和突然发病的人等又出不去。
那时能吃苦的村民会午夜12点出发,一个人用背篓背起一二百斤蔬菜和水果,走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正好进市场去批发。而像周广平这样在城里务工的村民,也要每月拿出几百元在市区租个房子以备雨季过夜。
“夏修水利冬修路”,过去是胜利村干部每年最头疼的大事。雨季会造成泥巴路面的垮塌,冲出一条深渠;山坪塘会塌方、滑盖。可发动村民去整理路基和山坪塘,并不容易。
2005年,一个50多岁的村民跑来问村书记魏绍全说,“魏书记,我这一生还能走得上水泥路么?”受了触动的魏绍全就骑辆摩托车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跑,开始想办法,最终大家都同意集资先修一条通往市区的水泥路。哪怕一年修100米,10年1000米,也要把路修完。
“不干事还好,一干啥事儿都冒出来了。”关于集资方案,魏绍全陷入了村民各执一词的烂泥潭里:家里人少的希望按人头平摊,人多的想按户头平摊;有人认为买肥料、饲料和卖菜的人路使用得多应该多出;女儿嫁出去了户口还留在村里的不愿出,人到村里很久了户口却一直没过来的也不愿出……
利益难以协调,一个队长的头甚至都被村民打破了。
魏绍全召集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了半年,最终定下一个繁琐的规则:人在户口不在、人走了户口还在的、80岁以上的一律都要集资,方案有人均出300元的也有户均出200元的,要视村民所拥有的土地和山林的多少来定。
2006年,村民集资10多万修了1.3公里的水泥路,这时有些村民想一年内把路修完,乡里又没扶持资金,村民就找广元市上访告状,说乡干部不让村里修路。
最终龙潭乡政府给村上拨了6万元的人头经费,2006年村上的水泥路修通了3公里。2007年,再修通了10多公里。
民主修路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胜利村成为全乡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5户房屋整体垮塌,10多户房屋受损无法居住,共105户需要重建。
这年10月,因为龙潭乡乡长王静的争取,香港某NGO四川地震救援与重建项目办到胜利村来考察。此时香港某NGO香港总部已在地震后第一时间募集了1.6亿港元的善款,计划主要用于在四川帮助受灾严重地区恢复小型基础设施建设。
过去在利州团区委书记任上时,王静就有和国际小母牛等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经验,是川北最早引入N G O参与社区发展的干部之一。香港某N G O在胜利村的灾后重建项目,也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利州团区委来合作和执行。
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香港某N G O连同团区委书记和乡长到村上察看灾情、了解村民的需求。按项目规划,胜利村可以获得香港某N G O 50万元的小型基建资金,但到底做什么项目,要由村民说了算。
按该N G O的要求,村民大会将村上富裕的、中等收入的和贫困的农户分成三组来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定下个规矩:开会时干部不能发言。需求调研大会上一位副乡长想建议修路,被该N G O制止。
选项目最后分两次由村小组和全村的村民大会投票决定。2009年2月,村民找来几口大碗和一堆苞谷粒粒,把治水、修路、农网改造等村民的需求写下来贴在碗上,在村委会一字排开,村民排队一个个地进来投票,想做哪个项目就在哪个大碗里丢一颗苞谷粒,投完票的和还没投的都要分开走。
最终“修路”的大碗盛满了苞谷粒。
修路修哪段也由投票来决定。村委会再召集了三四次村民大会来讨论和投票,最终人口多、连通城区的村委会至党家桥段获选。
然而50万元资金,按路面18厘米厚只够修3.6公里,要想把3.9公里拉通,还差10多万元。对于是否发动村民集资,魏绍全和王静一开始发生了冲突。
王静想给胜利村补助这10多万元,魏绍全却坚持要由村民来集资。而集资按国家政策有风险。
魏绍全的理由是,“过去集资修路,现在不集资,以后在村里就没法再搞项目了,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而且用政府的钱,“老百姓是会感谢党、感谢政府,但是万一资金出了问题呢”?
最终集资经村民大会讨论,按1、2、4组受益农户人均400元来收,村民都说没意见。村上计划修3米宽,乡政府觉得应该修3.5米,最终这多出来的半米宽由政府补助8万元。
村民做主
工程是自建还是对外承包,香港某N G O也交由村民去决定。为了将修路的成本降到最低,村民都赞同自建。但怎么采购建筑材料、项目如何管理等,香港某N G O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他们先将参与项目实施的村民编为技术指导、物资采购、物资保管、财务监督4个组,组长和两到三名组员都由村民选举产生。香港某N G O规定村干部不能进组,只有负责调解村民纠纷的工程协调组的组长由村书记兼任,还提倡每个组设一名女性代表和一名贫困户。
村两委对整个工程负全责。
选举自己的管理团队的时候,每个村民都很谨慎,因为这直接涉及到自家门前这条路的建设质量和开支。
一组村民周银平是砖工,懂建筑技术,村民就选举他做技术指导组组长;一组村民周芝华有摩托车,在外面和建筑材料的小老板打交道多,就选举他做物资采购组组长;二组村民周广平是从浙江做建筑工回来的“刁民”,村民就把他选进财务监管组去监督账目;贫困户周银军比较有奉献精神,村民就把他选到技术指导组去帮忙。
魏绍全等村干部原本认为这个管理团队是有问题的,“过去修路很多管理工作都是村干部在做,采购组等又不拿工资,谁愿意去呢?”后来发现这个团队和制度的威力。
以前村民修路,就是村委会说买什么,财务就去买,出现过采购员和厂家分成的情况。施工中如果一下雨,都是村干部跑去盖水泥。“干部做了很多事,还容易讨村民的骂,说干部不做事,还怕筹的钱让干部给拿去了。”
香港某N GO用一套新的制度来调动村民的积极性。物资采购建议采用招投标的办法,货比三家,让厂家到现场竞价。村里将制度进一步细化,如采购组长周芝华把价格较优惠的3个厂家的信息带回,招标那天按最低价录取,还要先交3万元保证金,路修完了才退。
财务监管上用严格的流程规范:香港某N G O分3批向团区委拨款,先由物资保管组、物资采购组和财务监督组验收前一阶段的工程,票据签字,再拿到项目组组长也就是村书记那里签字,再报团区委书记签字,然后再由团区委向财务监督组转下一笔工程款。财务监督组还必须每3天更新一次公示栏,每个村民都可以随时监督。
“细化了分工,规范了流程,村民更信任管理组,修路也真正变成了大家自己的事,村干部也更轻松了。”魏绍全说。
2009年3月3日,共青路正式开工了。1、2、4组共80多户300多村民,如何投工投劳是个难题。村委召集大家商量之后定下原则:一户投工60多天,定下的青壮劳动力不能找人代工,不能出工的,每天交150元误工费。
一个村民在广元做菜贩,该他出工没有出工,当天晚上生产队队长就到菜市场去找他:要不交误工费,要不回去出工。偷工的现象慢慢减少。
村委还将工程分包到组。一个组10多个人实行包干,可以加班加点节省工时,节省出来的时间村民可以回去打工。但魏绍全发现这还不够。
修路的辅助材料中有盒子板,一般修50-60米的路基需要用掉2000元的盒子。但如果小心使用,修几公里都可以一直用这一副盒子,极大节约成本。
他想了个办法,把村民自己集资的人均400元中,抽200元出来放到每个包工组自己购买盒子板、铁丝等辅助材料,节约下来的钱归包工组,不够再筹资,“这样把每个老百姓的利益捆绑到工程里去”,就可以节约开支。
这年5月11日,这个讨论了6个月的工程,最终只用了69天就竣工了。造价和工程质量让香港某N G O、政府和村民都很吃惊:每公里造价仅16万,比全包工程节约了一半,而且质量还能让每个村民都放心。
项目留下的厚厚的几本会议记录是另一笔财富。6个月的时间开了80多场会,每场都解决了一个问题,“像上了场大学”,魏绍全说。
复兴村的猪
这两头猪并不是白送给胡玉琴,她和“小母牛”签有协议,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借鸡生蛋”,利用礼品猪增收之后再将5000元的礼金传递给其他新的项目农户,这就是“小母牛”最重要的扶贫方式和价值———“礼品传递”。
沿着胜利村往山里走,到龙潭乡较为偏远的复兴村,散落的农户的屋顶大多有蓝黑两色,蓝色下的是水泥砌成的猪圈,黑色下的才是土坯加木头搭成的民居。
2007年胜利村的猪一下子暴增,这年猪价高扬让很多在外打工的女人都回乡养猪,村里一下子建起了很多上百平方米的水泥圈舍。
家庭贫困的胡玉琴这年也借了4万多元将老猪圈改造,扩建成170多平方米的水泥圈,再花3万多元购买了20多头小崽猪和两头土母猪。
结果猪一买回来就降价,2008年又发生了大地震,村上15户家庭垮房,800多平方米的圈舍倒塌,死了10多头生猪。胡玉琴家震后小猪不吃奶,站不起来,没三四天40多头小猪就全死了。
2009年,村民听说有一个叫“国际小母牛”的慈善组织到周边两个村子帮助村民养猪,就鼓动复兴村村主任杨久弟去找乡长王静,希望把复兴村也划入项目点,还按要求自己先组建好互助组,眼巴巴地等着“小母牛”来。
“小母牛”还真的来了。2010年9月,“国际小母牛”、项目实施的合作伙伴利州区扶贫办和胜利村正式接轨,项目开始实施。
和香港某N GO在灾区扶持的小型基建项目不同,“小母牛”主要帮助灾区农户搞畜牧养殖以发展生计,是个总部在美国的N G O,2008年在四川注册为“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地震后又组建了灾区重建项目办。
礼品传递
2010年12月3日,“小母牛”第一批64只礼品猪被运送到复兴村3组,分发给16个项目农户,每户的礼品猪价值5000元,胡玉琴也分到了两头二杂母猪。
这两头猪并不是白送给胡玉琴,她和“小母牛”签有协议,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借鸡生蛋”,利用礼品猪增收之后再将5000元的礼金传递给其他新的项目农户,这就是“小母牛”最重要的扶贫方式和价值———“礼品传递”。
除了礼品,“小母牛”带来的还有生态环保畜牧业的整套观念和技术体系,这个部分必须和当地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合作。
“小母牛”广元项目官员宋真明和城关畜牧站站长梁举坤的到来,让复兴村的猪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过去它们的圈舍铺的都是干稻草,粪便一到两个月主人才给打扫一次,喝水在槽里喝,每头猪可能还分不到1平方米的居住面积。
现在它们的圈舍安装了清洁的自动饮水装置,干草不见了,主人在圈舍下建了沼气池,湿粪直接从圈舍流入池内,产生的沼气可以供给厨房做燃料。主人还会每天一到两次来清理干粪,统一从圈舍一侧的通道收集起来发酵杀菌,然后再回田给耕地做肥料。
“小母牛”送来的母猪都是良品猪,它们和公猪杜洛克产出的三元杂交猪长势快、瘦肉多、体格健壮,一头母猪的售出价格差不多可以比土母猪多100多元,土母猪将渐渐被淘汰。
主人更清楚母猪们什么时候在发情。交配的时候,老母猪第一天就交配,第二天轮到中年的,第三天才是小母猪,这样交配时间长,产的崽才多。母猪都有单独的一间10平方米的圈舍,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生下来的小猪。
这些都是复兴村的村民们从“小母牛”和畜牧站的培训中得到的知识。培训用大量的案例教学和现场指导让村民真正学会养猪,同时也把生态环保的观念带进村子,间接影响村民的生活方式。
互助组的价值
2007年以来,建立互助组就成为“小母牛”在四川实施项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之前在做单家单户的养殖中,我们发现最后农户可能增收了,但是对社区和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却并没有提升,这违背了‘小母牛’所倡导的价值”。四川海惠震后灾区重建项目主任庞宗平说。
互助组以15到25户为一组建立,组员居住最好相对集中,并统一发展一个类型的牲畜,这样方便开会,每个人也都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
“小母牛”借鉴尼泊尔和印度项目办的经验,在互助组成员中设立互助金,由组员自己制定收取和管理办法。
在复兴村3组,16个项目农户选举出自己的互助组带头人。常桂芳是复兴村有名的女强人,外出打过工、个性也比较泼辣,被推选为组长;她的表妹常菊兰年轻、有责任心,被推选为会计;64岁的杨久义有文艺特长,在村民中有威信,被推选为出纳。
互助组定下规矩每周两次开会,组员互相交流养殖技术,学习“小母牛”的“12条基石”,会前会后唱歌娱乐。并规定实行军事化管理,每次开会迟到罚款5元、请假的扣10元、不请假缺会的扣20元。
同时每户每月5元设立互助金,用于组内开支,统一防疫时可以用于购买喷雾器和消毒液,组员资金短缺时还可以找互助金借贷,不收利息。目前已累积有3000多元。
杨久义的儿媳今年意外去世,一下拿不出钱来办丧事,找互助金借了2000元,3天后归还;常菊兰今年修猪圈借了800元,也已还清。互助金的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因为借和还主要靠的都还是信任”,常桂芳说。
互助组的组员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大家一起开会、聚餐、唱歌,每个人都遵守定下的规则,“过去可能连对方住哪都搞不清楚,现在感觉比亲戚还要亲”,胡玉琴说,“心情再不好,大家一唱起山歌来笑起来什么都忘了。”
组里的女人渐渐形成互帮互助的习惯。今年常菊兰修新房,男人在外打工没回,组里所有女人都自发跑去她家里帮忙拆旧房子;常桂芳家里修新猪圈,拆和建组员也都自发过来帮忙;谁家打油菜缺人手,互相都帮一把。
直到村上要平整道路,互助组也主动组织出工……
“感觉像回到了毛泽东的大集体时代。”村主任杨久弟说。同时他也是“小母牛”在村上的协调员,负责联络和发动。村上另外4个互助组都被发动到这个妇女互助组来学习。
这也正是“12条基石”中的重要价值,“礼品传递,传递的是诚信、责任和义务”,庞宗平说。
而按“小母牛”的计划,互助组的未来是发展为具有法律地位的专业合作社,目前他们在四川灾区已发展了十多个,复兴村妇女互助组也正在筹备统一购买饲料,做生产联合。
合作者的成长
“(NGO)只作为一个协调者提出问题引导思考,让我们自己想解决方案,也不给结论和评价,比如写项目申请书。”利州团区委书记谭芳从中体会到,“所谓参与式,就是尊重对方的主体性,真正让对方自己成长。”
2009年,胜利村的路终于修完了。共青路的执行力带来了龙潭乡政府追加投资,几乎照搬共青路的方式,村里剩下的7公里道路到2010年全部完工。
2009年,龙潭乡的村村通水泥路也修完了。乡政府将胜利村的民主修路总结为“胜利模式”在全乡推广,一年下来修了103公里的水泥路。
2010年2月,广元市利州区委办到龙潭乡调研,把该乡的“民主修路”总结成一个材料下发各乡镇,加以推广。
然而其他乡镇的干部来龙潭乡学习,回去之后却杳无音信,“首先集资一条其他干部就否定,同时对非政府组织的理念能够接受,但并不愿意推行”,龙潭乡一干部说。
他对香港某N GO资金监管的严肃性印象深刻,这体现的是“对捐款人负责”,“但其他乡镇干部就未必想找麻烦”。
目前国际性N GO组织在四川灾区做项目,大多数选择了和当地区县党政部门结成伙伴来执行。“因为基层政府是有独立财务体系的法人机构,在农村社区里较有公信力,项目容易推行。”四川海惠重建办主任庞宗平说。
“有的政府部门不愿做‘小母牛’的项目,因为怕礼品传递,政府的项目验收完了就完了,小母牛的却停不下来,觉得麻烦。”利州区畜牧局一工作人员说。
和香港某N G O、“小母牛”都合作过项目的利州团区委书记谭芳也认为,N G O倡导的价值在中国的现实中“有时会有点理想化”,因为“农民还不习惯自己决策,都是上面说什么就做什么;目前农民还是更关注经济发展,不愿对公共事务过多参与”。
实际上参与式的工作理念政府并不陌生,“一个扶贫办的股长都可做我们年轻官员的老师”,香港某N GO四川地震救援与重建项目经理翟凡说,“但他是否有时间精力投入在项目上?我们程序要求这么细,他们又有行政体系内完成一定量的任务,这里就有矛盾。”
而政府的扶贫项目,大多都是先由村民自己集资、垫资来发展,政府验收合格了才买单。某重灾区县的一个村子,上头发文要搞个产业项目,每家每户来养猪。而对于这个村的农户是否都建有猪圈、农户是否愿意养猪、每户能给几头猪的资金都未做调查。农户自己临时建起了猪圈,政府两次来验收却都认为不合格,农户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合格。
“政府的角色多重,既要管理又要服务,上级关注的就多做一些,过一段不关注了就又不做了,不像N G O会持续地做一件事,做得也更专业。”利州区扶贫办一官员表示,“政府与N GO是伙伴关系,不是上下级,就可以实话实说,做工作也更实在。而如果是上级交代下来的工作,即使不符合实际,也不会指出来。”
利州团区委书记谭芳、利州区扶贫办副主任王文元、龙潭乡党委副书记许联明、利州区畜牧局的梁举坤等,普遍都接受过四川海惠对政府合作伙伴的培训,参与式的手法让这些基层官员颇受触动。
谭芳本以为培训会和老师上课一样,只要带支笔和本子,到课堂的后排找个位置一坐记录就好。结果发现培训的现场没有讲台只有圆桌,每个人都要站到前面去发言,甚至还要自己设计小品等角色扮演,她有次扮演了一个到村里骗钱的牛贩子。
“‘小母牛’只作为一个协调者提出问题引导思考,让我们自己想解决方案,也不给结论和评价,比如写项目申请书。”谭芳从中体会到,“所谓参与式,就是尊重对方的主体性,真正让对方自己成长。”
向四川海惠提出合作意愿的基层政府等会被列为潜在项目伙伴,海惠随后对其中的一些官员开始半年3次的培训。
“有的培训了一两次就不来了,像都江堰、汶川、茂县、青川的官员,这是自我淘汰”,庞宗平说,最后能坚持完成培训的,也就成为真正认同“小母牛”价值观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