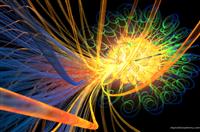
“危机”事件,传媒启动政府
“由于媒体的一篇报道,儿童村今年的燃煤费终于解决了!”可能因为从焦虑、奔波求助到如愿以偿之间的启承转合太富有戏剧效果,在“燃煤事件”已经尘埃落定一个多月之际,张淑琴在言谈举止之间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张淑琴是北京顺义儿童村的创办人。作为陕西监狱局的高级警官,她从1995年开始在陕西举办为服刑人员子女教育成长服务的儿童村,2000年又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北京。今年10月冬季来临,由于取暖用的煤炭涨价,顺义儿童村113名孩子组成的“超大”家庭短缺8万元购煤款,遭遇“燃煤” 之急。
对此,中国扶贫基金会施以援手,并促成了北京晚报的一篇呼吁报道。其后,北京市一位领导的批示带动市、区两级政府教育和民政部门的关注。仅一两天功夫,高效的政府拨款和社会捐款近50万元化解了这次“危机”。一篇小报道启动了一次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尽管它并不能为儿童村困境带来机制性的改变。
某种意义上,传媒启动政府其实就是民意启动政府。是媒体传达了 NGO的声音。
“传媒是NGO亲密的合作伙伴和强有力的支持者。”张淑琴对媒体的作用十分肯定。作为草根组织的创办人,她没有政府背景可以依赖。媒体使她成为公众人物,也为她带来了公众信任——在以爱心为基调的慈善活动中,信任作为一切资源的源头,为她游走于捐助者之间提供了身份名片,“在公众活动中成功率要高很多。”
除了儿童村自身事业的正当性, 张淑琴坦率地说,媒体关注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罪犯和女警官题材的奇特结合,容易激发媒体的想像力。这些年,大大小小的报道已经无法统计。除了平面媒体,她的身影还陆续出现在央视很多栏目中。在十年的光阴里,今年56岁的她“从‘半边天’做到了‘夕阳红’”。而陕西电视台断断续续跟踪拍摄8年,把她“折腾成了老演员”,“好在长跑中呼吸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不过,尽管长期沉浸在媒体情结中,“不放过任何一个豆腐块”,尽管外界对儿童村的报道处于低潮之际难免会引起一点心态上的落寞,频频而来的媒体到访有时也会让张淑琴“有些烦恼,有些发愁。” 它们问得比较频繁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何办儿童村?”
这个故事张淑琴讲了十年。个人倾诉的需要加上媒体的兴趣,使她长期沦陷其中,到现在“似乎再没有什么力气”重复讲述这个故事了。张淑琴要结束这个“以讲故事的形式浅薄地诉苦的时代”。她非常希望能在媒体面前多说一点“新的东西”,希望媒体不要拘泥于儿童村和她本人自身的故事,而要多发表有份量、有深度的报道,把着眼点放在推动社会环境的改善,使政府和社会担当起对罪犯子女的责任。2002、2003年南方周末对儿童村和女性刑释人员中途服务站1的两篇深度报道,探究了张淑琴的事业在夹缝求生中面临的困惑,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态度,使她印象深刻。张淑琴说:“儿童村哭穷没有饭吃,展现求助形象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除非每年策划2-3次重大活动邀请媒体参与,儿童村已经不再主动请媒体到访。当然,尽管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儿童村对国内外媒体还是保持着友善和耐心。张淑琴还将手下5-6位工作人员分成三组,负责接待媒体和志愿者,以分担自己的一些压力。
显然,象儿童村这样,随着自身的成长发展, NGO对媒体的需求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在质疑中成长
近年来,有关“丽江妈妈”和沈阳儿童村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类似机构的质疑,也波及到千里之外的顺义儿童村。2张淑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象经历了一场沙尘暴”。她承认,由于从事类似的工作,深切体味到其中的艰难,从情感上对两位争议中的人物抱有同情心理。
与很多个人创办的草根组织一样,由于领导人的长期影响,组织和领导人之间几乎可以划上一个等号,张淑琴和儿童村也有这样的对应关系。由媒体呈现给公众的儿童村印象,还多局限于张淑琴个人以爱心为依托艰难面对现实,或者带有一点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缺乏背后的反思。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捧上天,也容易被打下地。也许正是这些事件的影响,面对公众对NGO日益增长的公信、透明的问责要求,促发张淑琴开始更加理性和坦然地看待并调整自己与儿童村的关系。今年4月,她委托朝阳区公证处进行公证,明确儿童村资产不属于作为法人的张淑琴个人。并确定如果儿童村发生意外变故,其资产转入其它慈善机构。
对慈善事业来说,爱心不可或缺,爱心受到质疑无疑十分痛苦。但无论有多么强烈,仅靠爱心独自担当社会责任固然勇敢,却终有不能承受之重。看得出,张淑琴在慈善机构的制度建设上已有了新的思考和举措。
张淑琴和传媒的关系其实由来已久。在创办儿童村之前,她是陕西省监狱局《新岸报》副总编,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流落社会的服刑人员子女,萌生了救助这些儿童的想法。记者的经历使她对媒体需求有较为敏锐的直觉。她甚至为一些记者进行选题策划,商讨报道的视角和切入点。某种程度上她和媒体的双边关系并不被动,而象能够相互获取资源,谋求共赢的伙伴。
“作为记者,我看到的是悲剧。作为NGO领导人,我看到的是力量。”
与张淑琴总体上对媒体的热情相比,同是记者出身的刘开明一开始并不那么“开明”。
从2001年创办关注劳工问题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基本上是悄悄做事,低调为人。媒体报道固然能够带来名声、资本,能够增加NGO在政府面前说话的底气,在国外筹款也比较受欢迎,但也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干扰,对劳工问题这个敏感领域而言尤其如此。新生的机构需要摒除外界影响,静心思考问题、摸索方向。“报道报道,一报就倒。”刘开明认为,并不是只要媒体关注就是好事,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媒体打交道,这个时机一等就是三年。不过,研究所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直在背后给媒体提供素材,由他们来呼吁社会关注,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珠三角是全球跨国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外来农民工是工厂的劳动力主体。近年来,广东省劳动争议案件持续上升,这些劳动者创造无数劳动财富的同时,基本权利不断受到剥夺和侵犯,成为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弱势群体。创办研究所之前,刘开明作为深圳法制报的记者,在报道中接触到大量的工伤者,并在1998年开始关注为工伤民工打官司的律师周立太。1999年,他和工人日报记者孙覆海就打工者工伤问题合写了一份内参,由工人日报上传中央领导层。2002年他又就农民工问题向上呈递内参。
“这些内参让尉建行夜不能寐。”刘开明对内参的效果十分满意。 但是,“做记者只能乞求别人的帮助,领导人的帮助。”
起步阶段的研究所顾名思义,以观察研究为导向探究这些悲剧背后的原因。从2002年开始,研究所为劳工创办了法律援助项目,直接为其提供帮助。2003年,相对于庞大的民工群体,由于深感止步于工厂大墙之外的法律援助只能是杯水车薪,研究所进行了策略转移,法律援助作为“治标不治本”的策略退居其次,而对劳工和资方两个层面的培训成为亮点。
围绕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研究所直接把项目开进壁垒森严的工厂,搞管理层培训和企业社会责任培训,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培养企业长远的战略眼光,帮他们认识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竞争”模式。而劳工方面,因为“缺乏教育机会是导致劳工权益受到侵害和阻碍农民工改变自身境遇的主要原因,”同年9月,研究所和美国加利福利亚伯克利分校共同开办了深圳当代社区教育中心(劳工学校),把教育送进社区,为外来工持续发展提供教育和培训支持,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创造条件。针对劳资两方双向展拓的目的,是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化解冲突、合作共赢的机制。
今年3、4月间发生在广东东莞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旗下几家鞋厂数千名工人卷入的骚乱,证实了劳资双方有组织地谈判,有序地表达各自诉求的重要性。《新闻周刊》评论说,“他们常常难以找到合法的、公正的诉求管道。冲突的代价不仅由工人们付出,资方、政府和整个社会都是输家。”
刘开明说,“作为记者,我看到的是悲剧。作为民间学者,我看到的是悲剧背后的社会生态链。作为NGO领导人,我看到的是力量。”从记者到研究者,再到投身现实的NGO活动者,渐变的轨迹反映了刘开明这些年的心路历程。“现在,农民工已经不是人们印象中的保姆、建筑工人的形象,而是产业工人的主体。如何使他们的力量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力量,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我看到他们已经完全不是悲悲戚戚,而是非常有力量的一群人。”
“记者就象狗,丢一块骨头,所有的狗都会扑过来。”3
2003年底,为扩大社会影响,推动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打了三年基础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对外“开放”,媒体报道接踵而至。刘开明透露,2004年一年内,面对面直接采访的媒体报道大约100多个,而通过电话等其它途径采访的就更是不计其数。
“记者就象狗,丢一块骨头,所有的狗都会扑过来。”曾经是记者的刘开明拿自己作为解剖记者心理的标本。他透露,当时用来 “引导”媒体嗅觉的“骨头”,是去年底今年初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制造”的两个热点话题:“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珠三角“民工荒”。显然,这些话题一方面有效地引起了社会关注,同时,研究所的各项工作也连带吸引了不少眼球。
不过刘开明知道,要持续触动记者的新闻敏感和热情并不容易,“下一回你丢同样的骨头,他就不会来咬了,你可能需要丢一块肉。”
曝光也使刘开明成为国内外视野中的公众人物。对此,刘开明似乎并不太领情。作为公众人物固然有常人并不具备的各种好处和影响力,“坏处也不少。比如,你没有私生活,要经受各种人群的道德拷问。而且如果是因为个人影响造就了机构,机构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非常小。”。对NGO发展初期媒体对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报道,刘开明并不认同,因为“过度的报道容易让个人膨胀,就机构或者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而且从组织运行的角度,有名意味着将面对更为挑剔的目光。”
市场导向的媒体普遍喜欢将NGO人物塑造成为精彩故事中的主人公,而不是去关注组织本身的事业。为持续发展考虑,刘开明有意要把社会的关注从他个人引向机构。
“媒体出于同情或者采取NGO立场来报道,我觉得还不是太多。主要还是出于职业需要。”这位被媒体塑造的公众人物对记者的动机抱持冷静的理性。“全世界的记者都是要挖丑闻的。所有记者成名都是靠挖丑闻,某种意义上,使人们看到悲剧是记者成名的捷径。”对媒体和NGO而言,他不愿意用良心来评判其动机,因为“良心是靠不住的。”在一些情况下,也许不问动机,只问过程和结果,能够减少很多误解和委屈。
懂得媒体需求为刘开明在媒体间回旋提供了条件。在刘开明看来,媒体曝光多也不一定是好事,要看曝光什么东西,是否符合机构的需要。在媒体之外,NGO其实还有多种渠道传递自己的声音,比如研讨会,比如大学演讲等等。不过对研究所来说,媒体都是朋友,维持这个关系非常必要。
寄望媒体
刘开明希望媒体在对NGO进行报道时,能够放下既有的思维定势,深入了解,避免急于用自己的价值和知识做出判断。刘开明对此举例说明。今年《南方周末》记者为报道企业社会责任对研究所的工作跟踪了很长时间。为表明SA8000和其它责任标准相似但有不同之处,刘开明特意带记者观察了工厂评估方面的全部过程。他说,这篇文章本身写得不错,但编辑在处理文章过程中,由于不了解情况做了修改,结果最终给人的感觉还是对他想要强调的社会责任标准的差别之处未加区分。尽管对文章本身比较满意,刘开明还是对这点缺憾久久不能释怀。
现在,被媒体置于“潮头浪尖”之上的刘开明开始策划自己四年后的“退休”计划,当然,其前提条件是需要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并稳定下来。设想中未来的组织架构是涵盖社会服务在内的非营利性的劳工学校、一个独立的民间思想库、以及包括咨询、评估服务在内的营利性机构,三个机构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营利性机构对前两者提供支持,并且确保现有的宗旨不变。
为事业疲惫奔波之余,刘开明希望在将来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能够调整自己的角色,“给自己留一些空间、时间和挣钱的机会。”他说,“我们倡导社会公正,呼吁保护弱势人群,不等于我们就是弱势人群。”作为和草根化组织发展相互对应的另外一种NGO的精英发展模式,这种想法合乎情理,但在目前似乎又有些超前。
注释:
1.儿童村和中途服务站是陕西回归研究会下属机构。中途服务站为女性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前进行过渡性心理调适和培训安置。陕西回归研究会是张淑琴创办的民间组织,其宗旨是研究服刑人员在思想、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为他/她们提供帮助。
2.背景资料见第17页。
3.尉建行时任中央常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