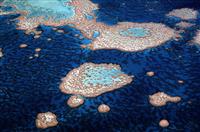攸乐山的茶与易武相比,偏于苦涩。我更喜欢易武茶的清甜韵深。清代是攸乐山做茶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把攸乐山排在六大茶山之首,可以想象出攸乐山曾经有过的繁荣与辉煌。
攸乐山的茶,枝繁芽肥。之所以在清代被列入贡茶,大概与攸乐山当时的植被丰茂、降水丰沛,以及红色的酸性土壤有关。清代阮福在《普洱茶记》里认为,古六大茶山的茶,茶的气息和滋味,因土性而不同,生于红色土壤和土杂石中的茶,品质最佳。
攸乐山现在叫基诺山,世代是基诺族的居住地。近几年茶的品质确有下降,一方面,当地烧山砍林破坏生态,种植了大量的经济作物漆树。另一方面,基诺族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刀耕火种的习惯,近百年来,烧山开荒种粮,毁坏了大批的古茶园。我在基诺山最大的古茶园亚诺村发现,许多数百年的古茶树,普遍存在着矮化砍伐,和用火焚烧后重新萌发的痕迹。大大小小的树疙瘩,即使覆满翠绿的蕨类和苔藓,也遮不住古茶树遍体鳞伤的沧桑。
曾经的基诺族以茶为生,至今保留着浓厚的原始茶文化。基诺语称茶为“啦博”,“啦”是依靠,“博”是芽叶,其意是赖以生存的芽叶。在攸乐山我还能看到古老的凉拌茶,火燎鲜茶,包烧茶,竹筒茶,铁锅蒸茶,原始茶膏的制作等等。
我们常说的“吃茶”一词,可能来源于基诺人的凉拌茶吃法。我第一次去攸乐山,就吃倒了苦涩麻辣的凉拌茶。紫切为了招待我,让他妹妹去茶园采来刚萌发的茶树新梢。他用手先把鲜嫩的茶叶揉搓变软,把新鲜的黄果叶、辣椒和大蒜切碎,然后在碗里加适量的盐巴和泉水搅拌。凉拌茶,对食辣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下酒佐饭的清爽美味。
我喜欢攸乐人用青翠的毛竹,烧烤制作的竹筒茶,茶里有竹沥的清香。颜色乌润的传统茶膏,古来醒酒第一,应该是基诺人津津乐道的草木精华。这里特有的火烧茶,让我眼界大开。类似竹筒茶的做法,他们把茶的鲜叶用一种称为“冬叶”的植物叶子,包裹起来,放到炭火上烧烤。当外面的“冬叶”烤干后,把里面的茶取出来煮饮,或者揉捻晒干后留着饮用。
原始的火烧茶,去除了茶的寒性,降低了茶的苦涩度,增加了茶的香气和耐泡性,为我野外寻茶和鉴茶,提供了迅速便捷的评茶方式。
春在枝头已十分。古农的岩文兄陪我到易武时,已是春分时令。易武的春,来得比江南早。易武没有江南浅黛春山的细腻,单单那条乱石铺就,通往茶山的颠簸马路,已经让我初步感受到易武的粗犷与悠久了。
提起普洱茶,易武是一段无法逾越的历史。清朝道光年间,在倚邦、莽枝等茶山逐渐衰退之际,易武茶山却迅速崛起,成为六大茶山所产茶叶的集散地、 生产地与茶马古道的源头,从而开创了普洱茶的易武时代。
易武茶的内质浑厚细腻,不去感受易武茶独具魅力的柔滑茶汤,对全面了解普洱茶的知识体系是个很大的缺憾。易武茶梗长叶厚,条索黑白相间,像条条油润的美女蛇。突然想起傣语里的易武,是美女蛇居住地的意思,这是巧合吗?难怪易武茶如此勾魂,茶汤隽永得如此动人魂魄。
在小车家里品的那泡刮风寨,至今记忆犹新。茶汤入口轻盈粘稠,清甜饱满,香气沉稳,蜜韵十足。三水后竟然出现特有的脂粉香。细腻柔滑的汤水,喉韵深长。那种难以言说的清雅风韵,让我感觉“班章为王,易武为后”的说法确有道理。易武茶里,有雍容含蓄的贵气,有绵绵不绝的柔情,让多少爱茶人“半缘修道半缘君”。
春分夕阳西下,我踯躅独行在易武老街的石板路上,遥想着古镇当年茶香中的繁华。树影里光滑的青石板上,云南小马踏出的清晰深凹的马蹄印迹,似有空谷遗音,踢踏声响。让人禁不住联想到,百年前的同庆号、福元昌、乾利贞等老字号的茶马辉煌。驼铃声中,大队的马帮风尘仆仆,常年奔波在斑驳沧桑的青石古道上。鸡声茅店月的霜雪中,把一剁剁普洱茶和自己的梦想运出茶山,残阳如血中,把生活必需品和红尘外的传说带回古镇。
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山林里苍老的古茶树,草丛中残缺的旧石碑,老街上鳞次栉比的老木房,是尚能触摸到的繁华与凋敝的痕迹。这种依旧温暖的力量,让轮回中的茶与人,再一次在历史的茶马古道上,有信心从冷寂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