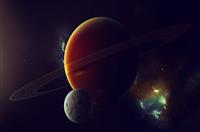
立夏三日,我竟然无觉,时间过得真快。泉城花木青翠,细雨轻烟。胜景中,我和朋友们焚香瀹茶,在品一款桐木关的小种生晒茶。
这款茶,干茶青白,气息幽深,喝起来酸酸甜甜,香馨芳幽。茶友们说,这茶的滋味和气息,不就是《山楂树之恋》里“静秋”的清纯明媚吗?我说,清甜中微酸而又有点青涩的滋味,是像初恋的感觉。但叫“静秋”太具体了,还是叫“山楂树之恋”吧!
这款妙意深长的茶,是三年前我在桐木关做茶的一次失误中诞生的。我清晰地记得,茶青是严格按照一芽一叶的标准,立夏后在高海拔的山场采摘的。
当时,我们大约采了二十余斤鲜叶。
下山的路上,大雨滂沱。回到茶厂,我把装在编织袋内的茶青放到萎凋室的一角,便去换衣吃晚饭了。然后又是一如既往地和朋友们品茶,至深夜,我才猛然想起那两袋鲜叶。等我急匆匆地打开袋子摊晾时,发现茶青有些轻微发酵了。我愧疚地抖而嗅之,茶青粘粘的,酸而不馊,微酸中竟有幽微的奶香味道。我当时想,既然不能做红茶,不如顺其自然,摊晾生晒,做成白茶。中国茶的发展史,与茶类品种的延伸拓展,不都是在偶然的失误中向前发展的吗?
我把这茶带回济南,一个月内品饮,青气重且微涩。两个月后,青涩褪去,茶汤酸酸甜甜,乳香幽幽,有山楂膏的味道。次年的五台澄观云茶会,在山西太山的龙泉寺,我用龙潭的泉水瀹泡“山楂树之恋”,此茶微酸中细幽的妙韵甜香,令人愉悦青目。寺庙的主持恒锋法师说:“这是一款令人心生波澜、幽微耐品的妙茶。”
去年的清明,我和丰年兄问茶安吉。在恒盛茶厂,用安吉的白叶一号,按曾经失误的方式如法炮制,制作了两批晒青白茶。有趣的是,鲜叶萎凋后,没有经过轻微发酵的晒青白茶,半年后青气不褪,苦涩偏重。而鲜叶经过湿闷发酵,酸味中带着浓浓奶香的茶青,做出的干茶,一个月后青涩褪去,茶汤依然酸甜悦人,十水后淡淡的乳香仍浓。
借鉴白茶的工艺,我用安吉的白叶茶做出的晒青白茶,是名副其实的安吉白茶。与烘青工艺的安吉白茶相比,晒青白茶的耐泡程度要高出两倍以上,转化出来的幽淡香韵,实在不可思议。
曲径通幽处,对茶的认识和探索,我还在路上。茶路上存在的失误和错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大格局中,说不定就是前方的柳暗花明。
窗前的紫藤花开了,藤萝垂蔓,浓浓淡淡。静清和茶斋里,清供着一盘麦黄杏和红樱桃,红黄烂漫。我用老铁壶煎水,小银壶瀹泡前年的私房茶“韭春”,招待来自云南、淄博、宜兴的茶友。两载的沉寂和静养,“韭春”的火气褪去,入口更加醇厚与甜畅。金黄油亮的茶汤,犹如桐木关的春天里,山野竹木草花间漏下的细碎阳光。
古人认为用金、银质茶瓶煎的水,味道最佳,又叫“富贵汤”,宋徽宗说煎水“宜用金银”。唐末的苏虞在《十六茶品》里说:“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胶。”茶性本俭,富贵汤于我,如浮云耳。使用铁瓶银壶,我只想手追心慕古人的风雅,品茶还是得真味、知茶意为重。
我平时吃茶,长于佳茗淡泡,注重茶性的寒温相宜、中正平和。“韭春”
性温,便辅以一款性寒的生普“清蘅”伴饮。“清蘅”陈放在济南,虽不足十年,但已汤色橙红,油亮通透。三水青味褪去,果香浓郁,回甘迅猛。齿颊留香,舌底鸣泉,茶质厚重,喉韵深长。
茶浓香短,茶淡趣长。品茗茶淡香远,淡中知味,益于养清静之和气。我絮叨数语,仍未能说尽茶意。知茶味者,莫若隐居终南山的如济兄,还是读读如济新赠我的茶诗吧!诗云:“莫道茶味淡,樱桃有娇颜。铁瓶新汲水,玉盏捧纤纤。”此中有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