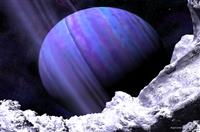在中国历史学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都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领域;而在这两个领域中,明清史又与近代史有着时段上的直接联系,因此,在研究主题上,应该具有相当的连贯性。在近年来的研究及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中,一些明清史和近代史学者的努力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在这其中,两个领域中的一部分学者开始进行积极的对话,使长期被人为隔绝、甚至对立的两个领域有了沟通。但是,就这两个领域中的主流研究来看,自说自话、各有各的话题、各有各的研究模式,还是很普遍的现象。对这种情形,实在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反思,以推进双方的互动和发展。因此,本文是一项学术史意义上的回顾性研究,它侧重的依然是史学研究创新过程中的理论模式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尽管是有明确指向性的,但却完全无意进行微观层面上的批评指摘。
一、问题(topic)的缘起
“明清史”、“近代史”和“社会史”这三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并不完全是传统的、甚至本土的概念。
在传统史学中,有“明史”,也可以有“清史”,但是不会有“明清史”。将明和清并列到一起,不仅表明他们不是“明朝”和“清朝”、而是“明代”和“清代”的合并概念,既淡化其正统的王朝世系因素,强化其时期的因素,而且表明人们已把明和清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一个历史时段,或即共同代表着王朝史的衰落期——这当然是事后总结出来的看法。“近代史”这个概念是个西方的舶来品,在英文中即modern history或history of modern times,传到日本后曾被译为“近世”,这些已被许多学者谈及,不赘述。当然,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使用的时间也许比“明清史”还要早些,在清末民初并不罕见了。而“社会史”(social history)这个概念当然也是从西方传来的,民国时期便已颇为流行,甚至在那时发生了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社会史大论战”。这三个概念的共性,就在于它们都是20世纪初的产物,都是“新”概念。在当时,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张力远没有今天这样大,这当然与具体的实践者及其赋予这些概念的内涵有关系。
在今天看来,这三个概念又的确代表着不同的取向。它们曾经历时性地代表着三种不同时代的史学范式:“明清史”毕竟以客观存在的政权或国号为时间标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王朝体系史,至少是具有浓重王朝体系史痕迹的写史方式。此种方式古已有之,且中外皆然,今天我们将其归为断代史。“近代史”则以主观判定的时代为时间标记,代表着一种具有某种科学思维特点的历史认知方式。这是“近代”以后从西方产生的,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现)代”是比较晚近的事。所以,一方面他们是根据自己所处时代向回推,离自己最近的就是modern,最远的是ancient,夹在中间的就是mediaeval或者middle ages;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分期界线也是根据近代以后产生的认识来划定的,古代与中世纪之间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是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开辟他有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这些都是近代思想的成果。特别是由于“近代”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转折点——不是“之一”,因此带来一系列对于历史认知和写作产生重大影响和争论的概念:前近(现)代(pre—modernity)、早期近(现)代(early modernity)、后近(现)代(post-modernity)等等,无论前后左右,都是围绕着近代这个概念转的。近代史这个概念及这个领域或学科,也毋庸置疑是近代的产物。与前两者不同,社会史的定语已经不再是一种时间标记,那就是说,它的革命性的或者突破性的意义就在于,它要突破一个被某种意识形态因素限制和困扰着的时间范围,而把表意时间的角色留给“史”去担当,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问题。这三者背后的语境关系如果得到较透彻的理解,我们的研究就会不断呈现“柳暗花明”的前景。
在当下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目前冠以这三个名目的领域中,有着最为活跃的研究群体和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在日本,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的学者及其成果,与研究后面历史的一样出色,那么在美国,研究明清以至民国历史的群体则要比研究前面的群体大得多。可能是由于所研究的时段特征和资料的缘故,无论是明清史、近代史还是社会史研究的学者,较多注意理论和方法的思考、范式和概念工具的更新,较多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动,从社会史(类似地,从新思想史、新文化史、新法制史)的视角观察问题的,亦多为明清史和近代史学者一-也许正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这个主题。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使我们的讨论可以建立在可以相互理解和取得共识的基础之上。
如前所述,从所描述的时代看,“明清”和“近代”在时间上是前后接续的,甚至包括了近代中的晚清部分。它们接得如此之紧,以至清史学者难得经常把自己看成与研究商周史者同样的“古代史”研究者。其实,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先秦史或秦汉史与明清史并存于“中国古代史”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认为,这些时段之间并不存在差别,或者它们完全同质。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真地认为一前一后两个历史时段具有本质上相同的特征,那等于说中国真的是一个停滞的、甚至是静止的社会。与此同时,说得夸张些,近现代史学者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明清史视同于唐宋或许更早,其具体表现在于1840年的“断裂”得到了极大的强调,而明清与唐宋之间的“断裂”——假如确有这个“断裂”的话——显然不可与前者同日而语。这一方面是忽略了明清史与晚清以降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则是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简化了,简化为只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碰撞——资本主义化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化——才是真正的或唯一的剧烈社会变革。
事实上,我们较少对为什么强调“近代”的划时代或转折点意义进行学术史的反思,而将其作为“应然”接受下来。为什么近代这个转折或断裂比任何其他转折或断裂意义都更重大?是不是真的因为它创造了超过以往的巨大的生产力?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例,我们无可否认近代开埠给这些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正如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学者告诉我们的,当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广州去南边的黄埔、甚至中山之时,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路上需要不断地换车和轮渡,而仅仅过了二十年,人们只需要1小时左右的车程,眼前的聚落格局和社会生态已根本改观。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比此前的一个世纪发生的变化更大,这是否可以说标志着另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无论如何,因为有了对“近代”的追求,才有了“启蒙时代”,有了“萌芽”等等,它们都是以“近代”为指归的。这些对历史时段的表达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近代人群体所发明的,后者并不考虑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因为那些人“俱往矣”。
“明清”和“近代”及其“史”都是标记时间的符号,至于研究“明清”或“近代”的什么“史”,显然在这里没有清晰表述出来。这一表述有赖于不同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典章、纪传、风土、五行等等到现在让位给了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等等。这里面除了“本土话语缺失”的问题以外,本来并无大碍,但现在由于前两个概念的存在且形成根深蒂固的不同“学科”,而在“社会史”前面冠以“明清”或者“近代”的时间标记,问题便凸显出来。
二、问题(problems)的凸显
“近代”是某种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的产物,分期就要考虑上下限的问题。几十年来,近代史较多考虑下限的问题,较少考虑上限的问题,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对断裂和连续性的判断——1840年作为标志,与以前的时代有明显的断裂,而跨越1911年,前后的两个时期有明显的连续性,就好像宋与唐的连用比宋元的连用更让人觉得习惯一样。这个断裂体现在哪里呢?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影响。这个模式的不足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讨论,毋庸赘述。问题不在于强调这个断裂是否恰当,而在于在这个前提下讨论“近代”的社会史,或者讨论众说纷纭的“现代化”问题,是否可以和不引入这些概念的传统讨论具有本质的差异呢?一旦前提确定,结论怎么有可能突破呢?无非是解释和评价发生了反转,从单一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变成同时强调西方现代化输入,一切的“社会”历史现象,无非是洋化及其本土反应而已,不同的只是过去讨论战争、机器、制度,现在则加上些衣、食、住、行、玩、乐罢了。
近代史中聚讼纷纭的“革命”模式和“现代化”模式也是这样,难道近代历史上志士仁人的革命不是为了追求现代化吗?难道追求和建设现代化不是一场革命吗?它们怎么突然变得对立起来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现代化”和“革命”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我们是否只是把它们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被动的反应,而较少思考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较少思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明清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元明史、偏偏明清连用呢?两个北方族群建立的王朝夹着一个汉人王朝,这其中清人强调“清承明制”,明人、特别是朱元璋强调“一反胡元之政”,好像一个是更多连续,一个更多断裂。我们需要对这些说法的产生多做一些反思:清人强调“清承明制”,是有他们重建和稳定秩序的考虑的,在相当程度上也的确是事实,但毕竟不是这么简单的,清人也是有许多自己的创造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空前多元的、地域广大的统一帝国。假如我们看看王朝更迭时期的战争,元末汉人自己打得比和蒙古人打得激烈得多,明朝人把蒙古赶出关外,用了一年左右时间,而清兵人关到统治基本稳定,经历了四十年战乱。我们认真思考明朝、特别是明前期制度的历史,和元朝的渊源关系是非常直接的,比如军事制度,明朝对元朝的继承关系是很清楚的,而清朝对明朝就改变了。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当时的主流文献的误导,我们面对史料的方法,究竟应该是把它当作历史真实的全面反映,不假思索地拿来就用,还是需要对史料的作者、对该作者为何及如何制造该史料进行了解,才能真正地理解史料?
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的研究者,往往自动放弃了对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历史的探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近代史已在现行学科体制内被单独划分出去,从教学到研究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他人无从涉足;另一方面是近代史所讨论的主题与明清史完全无关,顶多是在中外关系方面——比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等——为近代史的主题作一些铺垫,相反,倒是论证清统治者恪守传统的“重本抑末”国策、举出乾隆皇帝自称“天朝大国无所不有”那段名言——无论是否符合事实,为近代史定位清朝盲目自大、必然被动挨打提供依据。其结果是,明清史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都是被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古代史”的框架内,讨论明清社会如何衰落,某些新的因素如何受到制度的阻滞而夭折。于是,这种状况就更强化了近代史的“前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靠自己已经无法变化,只有凭借外力的推动。
难道明清、甚至宋元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历史线索,到道光二十年以后都不翼而飞了吗?打破分期的桎梏,实现“瞻前顾后”并非难事。在国内近代史的主流研究中,事件史和制度史一直占据比较主要的位置,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长期以来无法“瞻前顾后”,无法梳理事件或制度所在的历史脉络,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的事件和制度已有了明确的时代定位。当着力于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探讨制度、文化和社会层面问题的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近代史研究的时候,他们在“顾后”到民国初年方面比较得心应手,但“瞻前”到明清时代就比较困难。实际上,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其具体结论,国外一些着眼点实际上在晚清和民国
社会变迁的学者,多从16世纪以后来审视这一过程,
而我们却多少显得力有不逮。在这种情况下,亦无论现代化是否晚清历史的主线,有关它的论说还是不免落人“冲击—反应论”的窠臼。
最近听到一些研究生介绍其学位论文的构想,反映了这样一种问题定势的困境。一个研究生谈到,在某一地区的乡村,清代同光时期的碑刻中出现了不少整顿风俗的规约,比如禁止赌博、嫖娼之类,她似乎希望表达,这是晚清以来近代化过程的结果,原有的“近代”城市病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进入乡村。这当然不是一个年轻学生自己独有的看法,因为我们在其他学者的近代社会史著作中也看到过类似的表述。问题在于,这些社会弊病早已出现了不止千年,至少我们在此时期前的乡村中也见到过大量类似的禁约,它怎么能和晚清的所谓近代化或者工业化挂起钩来呢?这当然不是这个学生的问题,甚至主要也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学术界的问题。很多学者真的不太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他们往往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看。到的一些事情是新鲜事物,因为按照某种教科书式的“常识”,某些东西“理应”是新的时代的产物。有意思的是,这个主题看起来好像是“社会史”的,但实际上是在一个既定的“政治史”框架中去提出假设或结论的。
以政治史或社会史的不同思路去重新阐释明清史或近代史问题,其不同之处也体现在资料的使用以及由此升华出来的方法论上。事件史和制度史成果的取得依赖于近年来一些学者孜孜不倦地爬梳一手档案文献,厘清了许多扑朔迷离或长期被误解的历史定论,使我们的讨论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实证基础上,但另一方面,这些档案文献的史料性质及围绕其形成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们在制度史或事件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同时也决定了它们在处理其他许多相关问题、特别是其社会情境和实践层面问题的软弱无力,从而限制了在更深层次问题上的解释力。而当人们试图采用和解读档案文献以外的史料时,又会在方法上束手无策。在这个意义上,柯文的《历史三调》应该是具有启发性的。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莫过于明清史研究中的徽州文书。从其规模和资料性质来说,那真是历史研究者的宝库,当然多年来也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目前这些民间文书档案的保存状况,使它可以在制度史研究上显现其巨大价值,比如研究赋役、户籍、诉讼制度,研究宗族制度等,但对了解徽州区域社会来说,这些资料的原有系统都已经被打乱了,这个单位收藏了这部分,那个单位收藏了那部分,原来一家一族一社的东西被拆得东零西落,或者按照某种“科学”分类(比如土地、商业、祭祀、宗族、教化、灾害等等)把原来历史上的资料系统重新编排,这该怎么研究?是放弃,还是借助其他资料的配合及相关方法,把原有的系统尽量恢复起来?如果做后面的工作,我们如果素无训练和眼界,是否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干脆放弃,那么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目前所做工作的解释力?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关于兰克传统的讨论就好了。兰克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大量利用档案文书,认为这些史料最为可靠,同时再辅以严格的对史料的批判性检验,相信可以获得比较客观的历史真实,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兰克科学实证的方法对史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历史研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经验的工作基础上,其成果至今仍有生命力。但为什么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人们对兰克传统产生了质疑?为什么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是后面这些人完全无视、全盘否定兰克传统的积极意义?还是无事生非,标新立异?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兰克传统的工作,那么怎么可以在方法论上完全忽略20世纪的这段学术史?怎么可以忽略后人对兰克传统的批评而我行我素,“涛声依旧”?
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即时间上连接的明清史与近代史经常在研究主题上无法对接。是明清的问题到1840年以后就戛然而止了吗?是1840年以后出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前面探讨的帝国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的运行状态、市场体系、内发的社会危机及其应对等等,到后面就缺失了呢?为什么后面探讨的沿海开埠城市的社会变化、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运动,甚至经学、理学等等与前面的历史脉络了无干系呢?也许,社会史可以在这方面做些沟通的工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从问题出发、打破主观分期局限的一种探究方式。
三、问题(questions)的探索
打破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单一标准的分期模式,以问题为中心“瞻前顾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中理解历史变革,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个责任只能由社会史、或者由社会史视角的历史写作者来承担。原因在于,社会史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综合的、整体的、长时段的,它既不是把政治当作一切,也不是依据政治来理解社会,而是从社会去看政治,看其他。
在目前以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出自明清史领域的一些人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传世文献与民间文献的解读相结合,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解释思路,试图使社会史研究摆脱“剩余的历史”之讥。其实除了区域史的指向是整体历史或大历史,以及田野实践并不仅是搜集民间文献,还在于理解传世文献等外,很重要的是他们以“问题”设定研究时段、重新审视传统分期,而非在传统分期的既定框架下解释历史的做法。
关注明清史的社会史学者日益发现他们的问题囿于1368-1644年或1644-1840年的时间范围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的。他们关注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要素,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渊源,以前的历史遗产如何成为这一时期的资源;他们也关注这些因素到以后获得怎样的发展变化,才导致了后面的一些事态的结局。
我们日益发现了解明代的卫所及军户制度的重要性,但在这方面作出突出成就的学者不多,而相比之下这个问题却异常复杂。要想研究明代以后的移民问题,几乎无法离开对卫所、军户制度的了解,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不是指迁移过程,而是指迁移的原因和移入后的社会秩序——几乎是了解明清社会不可或缺的。另外有些北方族群的问题,比如所谓中国穆斯林“大分散,小聚居”的问题,在我看来也离不开卫所制度,而卫所制度又与元代的军事制度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也会发现,仅把清初江南若干大案放在一个王朝更迭或者族群冲突的框架中去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江南士绅的集体态度、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他们与地处北方的朝廷之复杂关系,至少要从元明说起,否则我们对他们和清朝统治者双方的表现,都不会有透彻的认识。
对于1900—1911年的社会—政治变动,给我以真正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我所读到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而是鲁迅的小说。从那里我才真正知道各色人等是如何经历一场变革,小知识分子、农民、市民、商人、军官……各种不同的心态、经历、际遇、沉浮,在一个个非常生活化的、普通的空间里,被作家塑造和加工了的人物形象是栩栩如生的、可信的,重要的是他们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情境。在这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事件,辛亥革命是每一个经历者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历史写作中,重大事件是被高高地架起来的,是改朝换代和宫廷斗争的工具,它好像不仅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而且与州县、市镇或者乡村也无关。于是,无论对于理解这些事件,还是对于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历史都变得残缺不全了。这便是我关注浙江湖州双林镇的近代“政治史”的缘由。通过梳理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各支力量的数百年变迁轨迹,我们便可以知道,社会史是否不“关心政治”,特别是社会史如何“关心政治”,或者,对“政治”的关心是否可以脱离社会史的或长时段的取向,而研究近代的政治史是否一定需要“跨区域”,则似乎不必讨论。
近代的历史也并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和开埠城市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和“近代化”也不能涵盖中国“近代”的全部主题,甚至也不是近代研究唯一的问题意识。晚清时期大规模铺开的西部移民开发以及所造成的“边村社会”的形成,同样也是这一时期这一广阔地区的剧烈变化。而且,这一变化如果不从明朝、至少是清雍正以后的移民浪潮去把握,我们就看不到从云、贵、川西南地区,渐次而至蒙古、青海、新疆,甚至西藏从“新疆”到“旧疆”的过程,在19世纪中国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以内蒙古的土默特地区为例,如果不是从一个较长时段去提出问题和进行观察,其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生计方式中的晋北汉人、蒙古人、旗制、喇嘛制度因素也难以理解。
我们发现,当我们习惯于处理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或著名人物之后,当我们转入内地进行观察,我们忽然会觉得如脚踩棉花,软绵绵地无从着力——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无事件境”:难道近代中国的变化只有一种面貌吗?难道对近代中国的解释只有一个标准吗?难道那些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干的事情真的没有联系、而只能被解释为因中国太大而存在的空间差异吗?我们对“变化”采取的是一种线性的、单一的认知,我们也缺乏一个处理“平安无事”的社会的方法论——我们在中国历史内部造就了一个新的两分,一面是因与西人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有历史”社会,另一面则是似乎“静止”的“无历史”社会,就好像当年西人看待东方和非洲一样。
因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诸多学者、国民政府的关注而闻名天下的定县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当年平民教育试点的那个村的邻村,看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庙宇韩祖祠,其中供奉的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民间宗教领袖飘高老祖,现存多块碑刻说明了当地的信仰系统历经数百年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代平民教育实验和这个信仰体系共处于同一个空间,它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张力?定县士绅长期以来不断塑造的韩(愈)苏(轼)形象,与现代平民教育运动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仅从清末改制、新学推广、思想启蒙等因素,是否能全面解释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前因后果?我们在这里看到,除了被新型民族—国家树立为楷模之外,新知识分子在这里对民智的改造基本上是失败的,他们甚至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方法——比如把这里的庙大多拆了,这种做法在此后的50—70年代依然得到延续,但是怎么样呢?那个被明清统治者恨之入骨的民间宗教的庙如今又死灰复燃了。相信假以时日,还会有许多庙被重建起来,做这些的人可能是另外一些人,但绝不是那些新式教育的精英。
在近代史研究界,试图突破前述束缚的努力在思想史领域已有体现(比如许苏民关于“三大突破”的观点和一些学者的具体研究,如葛兆光的“渐行渐远”等),这固然是因为“思想”的脉络无法与某种分期完全吻合,也是因为思想史和社会史一样,也是从问题出发的方法论视角。但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对历史进行多元的、尽可能贴近历史情境的重释?我想首先应该做的,是对以往的学术史进行认真检讨,对目前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加以反思;其次,加强史料的多元性并从对它们的不同解读入手形成新的方法论;最后,在具体的、而非抽象的、非来自概念和想象的历史情境中,对问题和史料进行阐释。
就后者而言,从明清史出发的社会史学者倡导“区域社会史”的切入点,尽管有学者将此“区域”误解为具有明确边界的概念,而提出“跨区域研究”的、其实并不冲突的说法(任何一个上一级的“区域”相对下级的“区域”来说都是“跨”的),甚至将“宗族”、“庙宇”误解为区域社会史的“核心概念”(也许有些人类学实践是这样表现的),但它毕竟是实践这三条理念的途径之一。比如对清东陵的研究,既无宗族,也无庙宇,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故宫档案,但它依然可以符合区域社会史的理念,将相关事件、人物、礼仪制度和整个清代历史的变迁及其复杂关系放到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去理解。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爱新觉罗皇族及其陵寝与汉人宗族制度、庙宇的神圣象征意义联系思考。
对于从边缘社会入手的人来说,无论他们从何处着眼和着手,他们关注的是何时和如何被整合到主体社会的历史过程,注重这一过程的多样性;对于从腹心社会入手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这一社会何时和如何变化,在整合边缘社会的过程中,原有地位强化还是弱化了。简言之,区域社会史的途径是推重问题的,允许跨时段的,其最终目的一定是跨区域的,甚至是整合性的。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也存在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中国,甚至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边缘与中心地区、群体等等不断发生置换,就像当年中国处于核心的领导阶级现在已经角色地位边缘化,20世纪的广东也处在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如果历史的分期是重要的话,那么这应该是衡量历史分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也许,把近年来明清史、近代史和社会史名目下的研究成果放到一起去比较一番,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它可能让我们搭建一个平台,使明清史学者与近代史学者在其上进行有共同逻辑的对话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