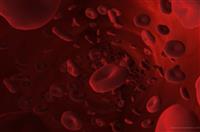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统以君王为代表,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道统则以读书人为承载,担当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如果说政统代表的是政权,那么,道统所代表的则是话语权。最早提出道统说的是被流放潮州的韩愈,他认为:士人所代表的道统要比君王所代表的政统更尊贵,因为道统是儒家的“内圣之学”,政统则为“外王之学”,是先有“内圣”,方能“外王”。社会的发展也应该循着理想的道德和天理来运行,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不可改变的,而政权则是可以世代更替的。
但自古以来,道统与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皇权,官僚和士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士人不断遭到来自政统的压制和迫害,迫使他们面对“从道”还是“从君”的选择。屈于压迫而背叛了操守落入名利场的士人固然不乏其人,但有风骨的士人都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道统的精神力量超越世俗政权,并构成对政统的制约和监督。如东汉太学生贬斥浊流而前仆后继,明朝东林党人抗议恶政而视死如归,都表现了读书人对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追求。明代理学家吕坤说:“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正是这种内在的独立性,使士人在坚守道统时,可以坦然面对皇帝与权贵,超越贫富贵贱,视死如归,并铸就了士人秉持道统为帝王师的辉煌梦想。
数千年来,士人与皇权的争斗,一直在政统与道统的这种张力中持续着。进入20世纪以后,第一个将二者统一的是孙中山。他既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是新道统的阐述者,又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领袖,是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随之,在延安通过整风击败了来自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的那群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建立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老人家因此成为革命的领袖和理论家,导师与领袖的合二而一,是政统与道统的合并。从此,这些思想导师兼政治领袖的人物,一身兼二任,游刃有余地主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与政治两大领域。自此以后,统治者的追求,便成为意识形态中所必须坚持的东西。二十世纪的新传统,彻底改变了数千年来政统与道统分离的老传统,真真是应了《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
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相互分离时代的了结,也是士人在社会中所担当重要角色时代的彻底结束。试想,一个不能为社会前进执掌方向,产生重大思想的阶层,其价值何在呢?读书人由此一分为二:一部分变为职业官僚,补充到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中去;另一部分则以知识为谋生手段,在社会的群体中日益边缘化。当社会中响彻最高指示的时候,举国的读书人都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变成了思想的侏儒。士人从此一变而为文人。文人者,玩弄文化之人也。在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文人的最好出路便是当官,即便是做学问者,也多学会了擦鞋,变着法地歌功颂德。在这个时代,他们中产生的最杰出代表就是钱钟书和季羡林。他们可以懂多种语言,脑子里装满了世界几乎所有的知识,却惟独没有他们自己。不过,这不能怪他们,是这个时代不需要他们去拥有自己。
在政统与道统走向合一的同时,士人也在这个社会中渐渐丧失了独立的地位。首先,学校被官府垄断,学在民间的讲学之途被废止;随之,“官本位”又将士人驱逐于狭窄的仕途,为稻粮谋的读书人,在终日的忙碌之中,渐渐失去了原本独立的自我意识和精神价值,获得的只能是日益依附于君王的奴婢地位。这样的士人,连自我的主宰都谈不上,何谈明道、行道和内圣之学?古人那种伟岸精神和超拔气象,只能是一种渐行渐远的往日印象了。过去学而优则仕、敢为帝王师的理想情结,早已冷却为一枕黄粱。
没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支持,读书人想坚守道统,摆脱对政统的依附,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社会则由于道统与政统的合一,实际上消除了道统对政统的约束力和制约作用,日益走向了肆无忌惮的专制。文革中知识份子的集体失语,和今天社会意识中的民主就是“为民作主“思想的表达,都由不同的侧面反射出道统被改变后的严酷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