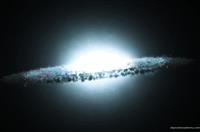把正义作为社会之善,即社会的“好”来讨论是出于两重考虑。第一,正义观是随着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的,因此,对正义的思考总是与某种社会正当性或正当性批评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正义观,正义是一种起源于社会,受制于社会的正当性观念。第二,“什么是正义”的问题总是和“要正义做什么?”及“正义有什么社会作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包含着社会理念,它们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霍布斯说,正义的作用是保障众人的安全,免得他们相互使用暴力。洛克认为,正义的作用在于保护各人辛苦挣得的私有财产。针对洛克的正义保护“自然权利”说,卢梭提出,正义的作用不是保护,而恰恰是限制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市场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就是保障不受任何外力干扰的自由竞争。福利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是让国家可以干预市场的无秩序运作,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民族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是维护民族的完整、独立和生存。专制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是维持由我代表的绝对权力,我权力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民主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在于维护每个人基本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尊严,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形成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稳定发展,等等,等等。由此可见,正义观实质上就是关于什么是好社会和如何实现好社会的理论。
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是,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甚至也不是集体道德。正义涉及的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如果能,那么这个体制或制度就是正义的(just),即具有“正当性”(justified),否则便不正义。人们对正义指什么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需要正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正义是我们精神世界中最受尊重的理念。不管有无宗教信仰,所有的人都援引正义,没有人敢公然摈弃正义。”(注1)
最早的正义观是以神学和哲学思考的形式出现的。正义观涉及是非、允许和不允许、禁止和不禁止以及提倡和不提倡的问题。古希腊人的正义观生动地展现在荷马的《伊里亚特》中。在麦勒劳斯(Menelaus)和阿格曼农(Agamemnon)那里,正义指的是复仇,也就是合理地杀人。《旧约》中上帝降怒于Sodom和Gomorrah城,显示的乃是神的正义。正是这种血腥和暴力的正义观让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新正义观的伟大转折意义。在苏格拉底那里,正义是社会和心灵的和谐,不是冤冤相报的仇杀。《圣经》所展示的正义观也同样体现在它的新道德教诲上。旧约中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再是鼓励暴力,而是要将报复和惩罪规定在有多少罪,得什么报的限度之内。于是,惩罚只是针对过错者,而不是株连过错者的家庭、部落和城邦。从报复到非报复,这是正义观所经历的一大转折。
早在古代,正义就是社会性的,与社会批评和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希伯莱的诸多先知们(Isaiah, Jeremiah, Amos, Hosea)都以正义的名义来批评他们当时的社会。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花了许多篇幅来讨论正义,以构筑他的理想王国。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在《尼可曼伦理学》中讨论的也是正义。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正义指的是“各得其所”,也就是每个人都应得到他资格内理应得到的那一份。在当时,谁得到他那应得的一份是由他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来决定的,各得其所的正义观是和特定的社会秩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用什么决定每个人有资格得到哪一份呢?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也是最持久的回答是“法”。这是法和正义两个概念联系紧密,甚至相互混用的原因之一。法和正义的另一重联系则是在于法所体现的、旨在恢复正义的惩罚,即惩罚性正义。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正义”用来讨论个人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与法有关的公共行为。因此,“非正义”(unjust)既指一个人份外的侵占(不正当或不正直之人),也指一个人触犯刑法。亚里斯多德的结论是,“不受法和不正直之人都是不正义的,‘正义’指的是合法、公正和公平。‘非正义’指的是不合法、不公正和不公平。”(注2)正义与“各得其所”和“法”的合而为一延续了十几个世纪。十七世纪的霍布斯也把违背法视为非正义。每个人有资格得到的那一份是由以私有财产法为核心的法所规定的。正如弥尔(John Stuart Mill)所解释的,“首先,剥夺一个人的个人财产、自由或者依法应属于他的任何其它东西,都被社会视为非正义。……这样运用‘正义’或‘非正义’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尊重一个人的法定权利为正义,不尊重则为非正义。”(注3)以法(和法定权利)来说明正义当然不是唯一的正义解说,它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但它却有利于理解正义,首先,以法量度众人,人人平等(具体的法是否公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其次,以法一以贯之,人们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预测结果,因此也就有了安全感;再者,恒常以法行之,法制秩序得以稳定并始终一贯。因此,虽然具体法律的正义性会受到质疑,但法与正义的基本关系并不受影响。
具体的法虽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它本身也有是否正义的问题。我们批评某法律制度为非正义,往往并不是要取消其中的法治成份,而是要以正义之法代替非正义之法。法并不如霍布斯所说,总是保护权利的。弥尔就此写道:“一个人被剥夺的法定权利也许一开始就不应当属于他,换言之,把那些权利赋予他的法可能是一个坏法。”(注4)同样,法也可能并不将人们应有的权利赋予他们,这样的法也应视为坏法。因此,从古代哲学、传统宗教或伦理、自然法理论到今天的全球正义和人权,它们的作用都在于为人们提供了某种评价和区分法和坏法,正义或非正义之法的更高标准,也就是一种与正义相符的更高法。选择什么样的更高标准?认可或者不认可存在这样的更高标准?用这一标准评估哪些体制性的法规?建立一种怎样的正义秩序?这些便成为思考实在法和更高法关系的关键问题。任何群体自我想象和自我构建的主要途径便是公开地共同讨论这些问题。
近世的正义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非惩罚性正义的问题上,反倒有忽视惩罚性正义的倾向。由于现代专制政权往往动用国家机器对政治异己作惩罚性压迫,由于专制政治对司法正义的实际限制,讨论惩罚性正义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司法惩处是惩罚性正义的主要表现形式。现代社会中的惩处都是以法律的名义来进行的,这使得现代刑罚与古代的复仇或神罚(或天罚)有所区别。今天,人们往往把所谓“绳之以法”看成是正义得以伸张。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注重人权还是侵犯人权的国家,都以法律为管制的手段。如果过分强调这一共同点,就容易对法有一种实证论或形式主义的观念,即“凡是有国家法(Rechtsstaat)存在的地方,都已不可能有非正义法的存在。”〔注5〕而事实上,现代国家法的正义性是以现代社会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条件的。
惩罚性正义不仅与实在法的政治制度环境有关,也与刑法惩处的目的有关。任何社会都有触犯法律者,也都有对犯法者的惩罚,凡是惩处罪犯都会涉及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惩罚他们?如何惩罚他们?国家主义的惩罚正义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犯法者不论犯了什么法,都得惩处,如何惩处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惩罚犯法者首先是因为他藐视法律,因为他不把法律背后的权威放在眼里,其次才是因为他的犯法行为对他人或社会所造成的伤害。从主权国家刑法的角度来看,同一种犯罪行为(如偷盗)在不同社会中的惩处轻重虽有区别(有的坐牢,有的砍手),但惩戒它的正义性是一样的。惩罚的作用也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惩戒维护国家权威。犯罪是冒犯国家权威,惩戒是国家权威对此冒犯的报复。国家主义惩罚在专制国家严酷对待政治、思想、信仰犯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清楚。思想异见者未必就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但他们却冒犯了国家关于异见的戒律,国家必须惩戒异见者,否则不能维护国家权威。国家惩戒于是成为对冒犯的报复行为。
即使在非专制的现代国家中,惩罚正义观也会对惩处的目的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对国家主义的有用程度是不同的。即使从非国家主义出发的惩罚正义,也有可能被国家主义利用。这是我们在思考与正义有关的惩处时需要格外注意的。在为什么目的而惩处罪犯的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认识,它们分别是,慑阻类似的犯罪(以敬效尤),重返正常社会(改过自新),以罚抵过(付出代价)。现代社会在惩处罪犯上常常会混合这三种不同的目的。但惩罚如果要体现正义,它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目的中,哪一个是首要的?康德曾经提出,只有以罚抵过才是正当的惩罚。康德认为,犯罪者必须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哪怕惩罚不能起到任何慑阻效果,不能维护国家权威,哪怕“这个社会明天就会散伙”,也一样需要惩治罪犯,跟他们算帐,叫他们为犯罪付出受罪的代价。〔注6〕在这一点上,康德是对的,因为除了惩罚真正的罪犯,还有别的远为有效的慑阻手段,例如,严刑苛法可以慑阻犯罪,但这些手段不仅未必正义,而且可能是非正义的。展示国家无情的暴力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国家政权可以定期不定期地搞些政治运动,公开严惩,大力显示国家权力的惩治力量,弄得风声鹤泪,人人自危。严酷专制时代犯罪率反倒较低,但这并不能证明政治运动时代的法律惩罚更具正义性。
对于民主法制国家中的人民来说,仅仅与禁止和惩罚联系在一起的法的观念是极端而狭隘的,因此也是不能接受的。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公民不受国家权力的随意侵犯,而不是方便国家权力去控制或惩罚人民。法律的核心是全体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国家对这些权利的武断限制。现代民主法制国家中的法律正义必然从惩罚向权利倾斜,普通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必然越来越紧密地和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人权正义性联系在一起。
现代社会保障社会一切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它的法律正义性首先体现为立法程序的民主性和司法程序的公开性。它要求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程序公平和量罪公平。这和专制社会中经常用搞运动破坏法制,以“严打”代替以罪量刑,听由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以至虐杀被拘人员是完全不同的。在当今许多社会中,刑法非正义是国家非正义最明显、最具压迫性的手段和表现形式。国家暴力的阶级压迫或信仰压制,对政治异见的镇压或扑杀,对公民言论、集社和新闻权利的压制,种族迫害和种族清洗等等,都是以先立法再执法来获得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合法性的。国家暴力和人权正义是完全对立的。
人权,而不是某种至高的“神法”或者“自然法”,为当今世界的人们质疑和抵抗国家暴力的实在法和国家非正义提供了正义标准。随着普遍人权的道德和价值权威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扩大,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国家非正义行为正在受到一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重新检讨。纠正国家非正义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惩罚性正义的超越,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于叫犯有过错的政权“付出代价”(最直接的代价当然就是下台)。它的目的在于澄清历史事实,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过错。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道歉越来越成为纠正国家历史非正义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1995年7月,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1993年,叶尔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拉克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挪威国王1997年10月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托尼.布莱尔于1997年5月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反思和道歉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注7〕这些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压迫、迫害和惩罚都是以过去的国家实在法为依据的,但是在今天世界普遍人权的更高法面前,那些具有压迫性的实在法不仅失去了正义性,而且恰恰代表了非正义。
正义观最初是与报复和惩罚联系在一起的,
惩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人类社会,仍然牵动人们对正义的思考,这是因为人类社会至今仍不完美。尽管如此,正义关心的更多的却是较为理想的人类社会。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指的是社会的和谐。正义的理想是理想群体的基础。在基督教伦理中,正义是宽恕和仁爱。同样,自从正义在古代从报复转变为非报复,它就一直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日常琐事联系在一起。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公平对待,赏罚分明,到公平交易,正义涉及各种各样“公平”和“公正”的人际关系。到了现代,正义的重心越来越放在社会财富和社会利益的分配和交换问题上,其中所涉最深的便是个人财产和个人自由权利。
个人财产和自由权利是现代社会契约思想的核心内容。“社会契约”并不代表社会现实,它往往只是某种想象的喻说。社会契约指这样一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和模式,那就是,理性、独立的人们了解自己的不同利益所在,并愿意互相协商,形成一种公平的秩序,使自己和别人都能最大程度地增进各自的利益。最彻底的社会契约观是在与无契约关系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对比中得到表达的。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之间相互敌视或者相互漠不关心,他们不相互合作,因此无法享受唯有文明契约社会所能提供的福利和安全。在自然状态的生存中是没有正义可言的。正义无法在自然状态中自动发生,因为正义是一种“人为”之善,一种社会性的惯例和发明。社会契约观在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也体现在象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这样的政治文献之中。契约社会和自然状态的对比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思想家对正义的思考。
对于什么是现代社会契约,什么是它的作用和意义,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说法。社会契约说于十八世纪充分形成。霍布斯对比自然状态和契约社会的生活,他的结论是,前者受制于残酷的暴力争斗,毫无幸福可言,后者崇尚协商妥协,既安全又美好。霍布斯写道,在社会形成之前,处于战争状态中的人生孤独、贫困、悲惨、残酷而且短暂。〔注8〕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不象霍布斯所说的那么恐怖。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自顾自拼命劳作,独自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他们后来缔结的社会契约完全是为保护个人勤劳所得。〔注9〕卢梭则把自然状态描绘为一种美好的境界,与后来的文明社会相比,自然状态中的人们要生活得远为自由和幸福。卢梭认为,社会对人类生活所起的是腐蚀作用,使得人人相互牵制依赖、苦不堪言。人类的自由和理性使得他们放弃了自然的幸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社会枷锁之中。面对着人类社会的腐败和不公正,卢梭设想另一种不同的社会,一种他所说的社会契约。按照这个契约,社会不再是由少数当权者和多数愚昧者所构成,社会由一切公民所构成,公民们服从他们自己定立的法律,一起培育道德的公众生活。〔注10〕
在以某种社会契约观讨论正义观时往往会涉及两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权利”和“平等”。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中,权利和平等的矛盾性成为在正义问题上多有分歧的主要原因。例如,拥护自由市场者强调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在他们那里,私有财产的权利是自由市场经济正义性的主要支柱。但是,从卢梭到马克思,许多思想家都把私有财产权利视为现代社会严重贫富不平等和非正义的主要原因。他们批评道,市场经济虽然看上去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的普遍公正原则上,但市场经济并不能为不同家庭出身、社会背景、政治关系、教育程度的人们提供相等的竞争机会,这使得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针对这种批评,拥护市场经济者反驳道,出身、背景、教育等等的差别是社会不平等,不是市场不平等,如果不强调人人平等地进入市场,那么连自由市场也会变得象社会一样不平等。一旦社会或政治外力以“正义”的名义介入市场,那么市场便会就此失去自由。尽管自由市场并不完全平等,但它最终还是能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好处,包括那些自由市场中呈现为弱势群体的人们。
权利和平等之间的矛盾性在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论和诺齐克的自由意志论的争论中充分表现出来。罗尔斯以一种假想的社会契约观来说明什么是正义。正义是社会组织必须服从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以这样一种假想的“原始位置”来确定的,即人人同等地自由、理性和对自己的私利一无所知。罗尔斯再三强调,这种社会契约说只是用类比的方式来作假想,并不是真的在历史上发生过。“原始位置”说指的是这样几点:第一,处于这种契约关系的人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其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地位或制度因素。第二,他们不知道自己自然的分配差别,如愚智、男女、强弱,等等。第三,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什么道德观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等等。总之,他们处在“无知的屏障”之后,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或克服自己的短处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但他们确实知道一些现实世界的基本情况,那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既不特别丰富,也不特别吝啬,所以他们的相互合作既不多余,又有可能。而且,他们的利他行为是有限的。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把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在“原始位置”中的人们会相互定立一些原则来帮助自己各自实现他自己心目中的好生活,这些原则就是正义原则。在这种典型的自由主义认识中,正义本身并没有实质的价值内容,价值内容是由个人确立的,正义只不过是为自由、理性的个人确定自己生活目标提供基本的生活世界条件。〔注11〕
罗尔斯认为,只有当人们不知道各自能从正义契约中得到什么私利时,他们才能订立出真正公正的契约来,“一个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是最接近于一个自愿结合体的,因为这个社会的原则就是自由、平等的人们在公正的情况下制定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成员是独立的,他们所承认的义务是他们自己所设置的。”〔注12〕罗尔斯提出社会正义有两个具体的基本原则。第一是基本权利平等原则。每个人在基本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如果剥夺了一个人的“政治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那就是非正义。〔注13〕第二是差别原则。它强调平等机会,不只是形式平等(说人人可以平等地参与竞争),而且是尽量的实质平等(为社会弱势者提供增强竞争能力的实际帮助,如优先考虑入学、就业,等等)。但它也允许保留一些尽量有利于所有人的尽量小的差别。〔注14〕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自由主义五特征顺序是基本权利平等、自由、机会平等、个人自定好生活理想、尊重个人独立选择。〔注15〕
诺齐克从自由意志论的角度反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义论,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理论”,即“分配是否公正,全看(财产的)来路如何。”〔注16〕他把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最后顺序价值提到第一位,并确立为唯一的原则,因而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正义观。譬如,一个老人决定如何把遗产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有病,最有需要;二儿子一直在家照顾父亲,最份内应得;三儿子游手好闲,又不缺吃喝。老人把钱全给了三儿子,这样是否公正?无论我们是讲“平等”,讲“赏罚”,还是讲“需要”,这样的分配都不正义。但诺齐克认为,只要老人的财路来源正当,怎么给儿子都是正义的(都具有正当性)。诺齐克认为,从“平等”、“赏罚”或“需要”来评断正义都是从“接受者”(诺齐克称之为“结果状态”,end-state)而不是“给予者”的角度来看正义,都只是看到接受者拿到分配物的那一刻(诺齐克称之为“即刻时间”,time slice),都是要不得的模式分配原则(patterned principles of justice)。诺齐克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按某种“结果状态”原则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达到了一种“即刻时间”的正义,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了新的财富差别,那又怎么办?是不是无休无止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重新分配?他的结论是,“一切结果状态原则或正义的模式分配原则,都只能在人们生活不断受到国家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实现。”〔注17〕诺齐克认为,一个人的财产只要来路清白,他就有资格拥有这财产,如果他能对穷人行慈善,那固然很好,如果他不行慈善,那也不等于非正义。就象政府不应强迫双肾健全者为缺肾人捐献一肾一样,政府不应运用纳税制度将富人的钱转让给穷人。这两种政府行为都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如果说罗尔斯力图同时兼顾平等和权利,那么诺齐克则专门强调权利,尤其是个人对国家强迫说不的权利。
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往往把人们看成是一些原子型个体,个体的人们自由而理性地选择并缔结一种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契约关系。对这种契约观批评最激烈的是社群论者,他们是自由主义内部的批评者。社群论者强调,个人并不降生于人际关系的真空状态中,并不能“自由地”缔结契约关系。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已经是某个实在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早就有它自己的制度、规范和价值。群体环境是在历史和传统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不同的群体环境使人们成为不同种类的个体,自由主义型的个体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正义原则往往表现为国家制度特征,但正义原则却更与群体生活方式有关。例如,美国国家制度固然以其宪法为标志,但是美国社会的许多结构特征却是在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前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早期来美洲的殖民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欧洲的传统、语言和对“新大陆”生活的理想。美国宪法建立了一种政府的形式,但并没有建立一个社会。早在美国制定“按被统治者的意愿统治”的原则之前,许多社群就早已在按这个原则运作了。换句话说,早在美国宪法将此原则确立为政治正义的内容之前,它已经是社会正义的内容了。在另外一些国家中,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虽然国家宪法中确立了民主的原则,但在政治实践中却仍然沿袭传统的专制独权、等级区分和家长权威原则。
强调群体,也就是强调社会不等于国家。国家正当性必须建立在广大公民的支持上,但社会的正当性却并不必须如此。例如,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可以通过选举程序来显示,但社会的正当性却不然。社会中的正当性,亦即“正义”,比在国家中更体现为一种自愿服从的义务感。社会契约作为一种自愿服从模式,其意义正在于此。虽然社会契约是理性个体间达成的关于某种公正秩序的默契,但它的意义却大于所有个人利益的总和。早在苏格拉底那里,正义就被设想为一种无须在其自身之外寻找合理性的、自我完足的“善”,尽管这种善对行善者最终还有其它益处,就象通俗佛教的善为真果,但毕竟善有善报。
作为社会之善,正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善,而是体现为社会不同生活领域中关于不同物品的正当分配原则。这种群体论正义观在华尔泽的《正义的领域》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华尔泽认为,正义并不是外在于实在社会的单一抽象原则,如“平等待遇”、“各得其所”或者“权利”。正义始终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群体中已经存在的种种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正义是多元的,每个社会领域都有它自己的特定分配物品,这个物品往往包含了关于它自身的分配标准,这个分配标准就是正义。例如,医疗保健领域中的分配标准是需要,金钱和商品领域中的是自由交换,教育领域中初中等教育的是平等,高等教育中的是(受惠)能力,等等。他提出,每个具体领域中的分配都不可能做到按它自己标准所设置的绝对公正,总有一些人会比其它一些人更受惠于现有的分配标准。但是,由于每个人都不只活动于单一领域,都必然涉及多种不同领域,所以,只要严格保持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不让一个领域中的优势转化为其它领域中的优势,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领域中受损,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受惠,以形成一种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终取得“复合平等”的结果。因此,正义的关键在于维护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区分和各领域的独立,以防止一些领域对另一些领域的“宰制”。在这一点上,民主而且自身独立的国家权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之好并不等于个人利益的总合,社会之好必须是一种集体考量。社会不是自顾自的个人所拼合的沙盘,社会是一个由具有集体意识的公民成员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华尔泽认为,社会整体应当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础结构,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国家公园、通讯系统、学校、博物馆等等,这些基础结构既扩大个人生活的范围,也塑造个人生活的样式。共同的生活资源帮助广大公民参与必要的和有价值的社会活动。这些公共资源的衰败和私有化必然会使得有些公民被排斥在那个由这些资源所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之外。
〔注18〕
华尔泽强调,社会有责任维持和增加投入,以保障群体所有成员的生活品质环境。只要社会在进行这种投入,就应当让所有的公民,而不是某一些人,从中同等地得益。否则,那些被排斥在外者就会遭受双重的非正义对待,受损害的不仅是本应受群体重视的需要,而且还有作为群体成员的尊严。华尔泽就美国医疗领域中的非正义现象写道:“瞧医生或上医院与社会阶级相关,但与病患程度或事故却无甚关系。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统计更能说明当今美国医疗(非正义)了。如果医疗是一种奢侈,那么这种病与医的脱节便不重要;但是如果社会把医疗认定是一种需要,如果群体为提供医疗下了本钱,那么这种脱节就是很严重的事了。得不到医疗者遭受的是双重损失--他自己的健康,还有他的社会身份。……只要群体在医学研究、建医院、医生工资等等上花了(共同的)钱,由这些支出所提供的服务就必须同等提供给所有的公民。”〔注19〕
华尔泽在批评美国医疗领域中的非正义时,并不是以某种永恒的、抽象的正义原则为标准(如罗尔斯的“原始位置”),而是诉诸于美国的本土价值传统和美国社会现已具有的正义共识。例如,在美国社会中,人体器官是不准买卖的,当一个人得了重病绝症而又无钱求医时,往往会激起很大的社会同情,这些都说明美国社会群体在健康是人的基本“需要”(即医疗领域中的特殊“物品”)而不是一种商品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许多别的社会领域中。例如,人们把“娼妓”、“贿赂”、“买卖圣职”等当作很坏的词眼,这是因为他们在“家庭”、“公职”和“宗教”领域中的正义共识反对这些领域受金钱主宰。金钱主宰使得那些本不该由金钱收买的特殊领域物品(“性关系”、“权力”和“神恩”)往往变成了商品。华尔泽说,“一切分配,是正义还是不正义,都是视(特殊领域)物品的社会意义而言的。”〔注20〕一个社会群体对于具体领域中分配物品性质所达成的共识(是否可以买卖,是否可以随意为权力所霸占,是否准许通过裙带关系获得,等等)决定了这个群体关于以什么原则分配这物品的共识,这种原则共识代表着这个群体的正义观。
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共识,也就有什么样的群体。从国家制度来看是如此。人们常说,专制之下,人文和科技皆为娼优,指的就是政治权力对其它社会领域的侵犯、暴力和宰制。从社会群体关系来看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群体的广大成员对弱势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只讲一些人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权利,却无视另一些人免遭困苦的权利;如果一个群体总是特别奖励一些“才能”(拍马逢迎、谎言假话),而冷落另一些才能(独立思想、理性批判),那么他们就是在用一种现行的正义观(华尔泽并不否认这也是一种正义观)向世界宣告他们是怎样一个群体。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本土或民族特色的群体,但却未必是一个受其它群体尊敬的群体。
一个群体,它的成员之间互相做些什么和互相不做些什么,远比他们空洞的理想口号更能说明这个群体的现状。正如华尔泽所说,正义涉及的乃是“在实在的群体中,公民们应当彼此做些什么。”〔注21〕如果群体成员真的互相关爱,真诚和诚信,尊重和自由交流,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互相伤害、欺骗、欺压、告密和尔虞我诈。这些行为固然与个人道德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它们还决定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秩序,因此也更与“正义”有关。社会领域会因为受外力宰制而蜕化为滋生不道德行为的场所。例如,商品市场领域中的许多不道德行为其实都是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集团勾结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宰制破坏了商品市场的公平自由买卖的正义原则,使之沦变为一个权贵利益场所,它的“正义”原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般商品经济领域的正义原则。
申张社会正义可以从识别现实社会中各种因外力宰制而恶性变质的领域开始。正如商品经济领域可以蜕变为权贵利益场所一样,公职领域可以蜕变为“官场”,司法领域可以蜕变为“衙门”,教育领域可以蜕变为“学店”,新闻领域可以蜕变为“宣传阵地”,公共舆论领域可以蜕变为“一言堂”或者“假话秀场”,等等,等等。在这些恶性变质的领域中存在的是制度问题,而不只是道德问题。恶性变质的领域能使大部分人变成不道德的个体。个人道德固然有助于实现好社会,但是好社会的实现却并不需要等到人人都先成为道德者之后。社会之善不一定是全体社会成员之善的总和。以重在制度的正义来期待和要求一个社会,也就是相信,好的制度可以改变缺乏道德的个体。即使在一个未必人人都是道德君子的社会中也可以建立自由、理性和公正的秩序,这种秩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之善。
注释:
1. Chaim Perelman, Just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 3.
2. Aristotle, Nichmachean Ethics. 5, 15: 1129a 32-34.
3. 4.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1861), ed. George She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79, chap. 5, 42-43; 43.
5. Giovanni Sartor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ed. Part Two: The Classical Issue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87, p. 323.
6. Robert C. Soloman and Mark C. Murry, eds., What is Justice: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1.
7. Elazar Barkan, Guilt of Nations: Restitution and Negotiating Historical Injustic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ix.
8. Thomas Hobbers, The Leviathan. New York: Hafner, 1926, chaps. 13, 14.
9.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3.
10. Jean-Jacques Rosseau, The 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
11. John Rawls, "The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 in Robert M. Baird and Stuart E. Rosenbaum, eds., Morality and the Law.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1988, p. 127.
12. 13. 1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5; 61; 60.
16. 17.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155; 163.
18. Michael Walzer, "Justice Here and Now," in Frank S. Lucash, ed., Justice and Equality Here and Now.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7-138.
19. 20. 21.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p. 67n; 9;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