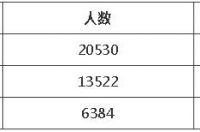没有比模糊的语句更适合造成混乱——或者实现共识的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那些哲学难题其实只不过是误用语句所造成的后果罢了。相比之下,外交的艺术就是要找到一些掩饰不一致意见的语句。
一个所有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同意的理念就是,在自然矿藏资源之外,穷国和富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既不来自资本,也非源于教育,而更在于“科技”。那么科技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而答案则体现了经济学家之间不同寻常的共识,因为“科技”被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范畴去进行测量,一个在计算了其他生产投入(比如物质和人力资本)之后依然未能解释——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称之为“全要素生产力”——的剩余量。正如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在1956年巧妙地点出那样,这个余量并不多于“对我们无知事物的测算”。
因此,虽然认定是科技构筑了国家财富比承认自身的无知听起来更有意义,但其实并非如此。而我们必须应对的也正是自身的无知。
在一本重要著作中,W·布赖恩·亚瑟(W. Brian Arthur)将科技定义为特定文明所能利用的器材和工程应用的总和。但器材可以被放进集装箱并运送到世界各地,配方,蓝图和操作指南也可以在网上传播,只需几下点击就唾手可得。因此互联网和自由贸易应当可以令我们称之为“科技”的理念和设备散播到全世界。
事实上,从1980年代末期保罗·罗默的研究开始,大多数现代增长理论都产生于一种认为生产力的提升来自于那些难于创造但易于复制的理念。这也是为何要用专利,版权和政府补贴来保护发明者的原因。
因此,如果理念易于复制而设备易于运输,为何“科技”上的差距依然顽强地存在于国家之间?
当某些事物扰乱了一个有益的自然秩序,人类就会渴望用一些体现邪恶势力的说法去解释。比如说,达伦·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著的《为何国家会沦落》(Why Nations Fail)一书认为科技之所以无法渗透到某些国家是因为当地的统治精英的阻挠。他们会采用排斥性的(坏)体制,而非包容性的(好)体制,因为科技会颠覆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控制,所以这些人选择将其排除在外。
而笔者作为一个正在眼睁睁看着自己祖国走向崩溃的委内瑞拉人,也必须承认人类历史上有着许多权势阻碍进步的时刻。而我也震惊于政府常常也会采纳一个共享增长的目标——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就是一个好例子——却最终无法实现。
上述那种政府推动教育、自由贸易、知识产权,社会福利项目以及互联网,但它们的经济依然停滞不前。如果科技只是关于设备和理念的话,那究竟是什么制约了它们?
问题在于科技的其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专项技术要领(knowhow),也就是执行并实现一个目标的能力。而这种技术要领与设备/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包含在(对某事物的)理解之内,也无法通过理解而获得。
网球冠军拉菲尔·纳达尔(Rafael Nadal)在成功接到一记发球时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动作是什么。他就是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这一切难以用语言去描述,而且就算努力描述也无法令其他人变成网球好手。身兼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对这类隐性知识的看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因此我们不需要排斥性的精英或者其他邪恶势力去解释为何科技无法四处渗透。科技渗透的难处在于它需要技术要领的协助,也就是一种认知其模式并以有效行动去做出回应的能力。这种大脑的联结需要多年的实践才能实现。这令渗透变得非常缓慢: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知晓技术要领的人到了某处这些要领才会随之落地。而一旦落地,他们就可以训练其他人。
此外,随着如今技术要领变得更加被集体而非个人所掌握,渗透也随之变慢。集体性技术要领指代的是那些实现一些无法被单一个人实现的目标的能力,比如演奏交响乐或者传递邮件:单靠一名提琴手或者邮差是无法完成的。
同样,除非一个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已经拥有获取互联网,信用卡和速递服务的途径,否则这个社会是无法简单模仿亚马逊或者易趣所蕴含的理念的。换句话说,新科技的渗入需要以其他科技的先期渗入为前提。
这也是为何各个城市,地区和国家都只能渐进式地吸收科学技术,通过将一些业已到位的技术要领(或许再加上某些部分,比如加入一位低音提琴手来完成弦乐四重奏)结合起来以实现增长。但它们无法一蹴而就地从弦乐四重奏跃进到整个交响乐团,因为还缺少太多乐器——更重要的是,缺少太多知道如何演奏这些乐器的音乐家。
只有在进入了理论生物学家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所谓的“相邻可能”(adjacent possible)才能出现进步,而这意味着在某个国家找到可行方案的最佳途径就是考察已有的东西。政治可能确实会阻碍科技的渗透,但在在很大程度上,科技无法渗透的原因其实源自于其自身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