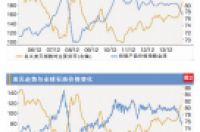——张瑾对话西奥多·库迪切克
2014年2月至5月,我有幸在密苏里大学历史系访学,该系的西奥多·库迪切克(Theodore Koditschek)教授是现代英国社会史和大英帝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也是我访学期间学习和请教的主要对象。他的第一本书《城镇工业社会的阶层分化:布拉德福德,1750—1850年》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和罗伯特·利文斯顿·斯凯勒奖(Herbert Baxter Adams and Robert Livingston Schuyler Prizes)。之后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其新著《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与历史想象:19世纪的英国图景》也于最近在北美的英国研究会议上获得了彼得·斯坦斯基奖(Peter Stansky Prize)。借着访学的机会,我和库迪切克教授探讨了英美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马克思主义吸引我研究英国历史
张瑾:作为奥地利移民后代的犹太历史学家,是什么吸引您投身英国历史的研究?
西奥多·库迪切克:我刚满16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伯特兰·罗素的自传。父亲是个沉默的人,从来没有谈过他二战前在奥地利的情况。当时我以为他给我这本书是想向我传达某种神秘的消息。不管怎样我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罗素自传,学习了以他为代表的英格兰贵族式的自由主义。除了他的贵族身份,我发现罗素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对学习、政治和爱情都倾注了激烈和不妥协的激情,是一个颇具吸引力、值得崇拜的对象。16岁那年的夏天,我除了罗素自传外,还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该书建立了英国工业革命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正是这两本书让我开始对英国历史产生兴趣,只不过当时我还没想到今后会研究它。
大学一年级时,我读J.S.穆勒的《论自由》,认为这是罗素思想的重要前导,是关于英国的另一个重要阐述。当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的灵感反而是被夸张的理论诉求所激发的。我看到穆勒缺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马克思缺少穆勒对自由的捍卫。如果二者可以结合起来,结果将是完美的。所以,我选择了哲学作为我的专业。幸运的是,我很快意识到不太能在哲学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况且哲学太过抽象,为了让学业与研究更加具体,我考虑了一系列社会科学学科。但当时以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学显得过于保守,人类学又要求具备外向的品质,而我不具备刚毅气质,只剩下了历史和地理可选。我在童年时期就喜欢国王、王后和总统的历史,喜欢全球各个部分的地图。所以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历史变成不只是一堆名字和日期的堆砌,让历史也能与河流、山脉和城市等有某种联系?历史是否可以用吸引我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方法进行研究?
在读本科第三年的时候,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E.A.瑞格利的《人口与历史》让我发现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它充满了悲怆和戏剧性的事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以以演绎学科的视角来撰写。只是汤普森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散漫、理论含糊和过度好辩的印象。而阅读《人口与历史》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被人口分析的力量所震撼,出生、死亡和婚姻等简单的数据为研究随时间而变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新视角,于是我想,可以将瑞格利的结构主义和汤普森对机构与文化的敏感性结合起来吗?早期曾想将马克思和穆勒相结合的想法也变得更加现实,同时我也试图将汤普森的“主观”英国史与瑞格利的“客观”史结合起来。后来,我终于找到了职业方向,并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从此开始我的历史学研究。
张瑾:您在新著《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与历史想象:19世纪的英国图景》中对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概念有新的诠释吗?
西奥多·库迪切克: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是我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间的连接线,都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霸权的利益所在。对我来说,自由主义的矛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和最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的起源就在19世纪英国。
跨学科研究是史学未来方向
张瑾:据我所知,英国曾在1986年设立了公众科学理解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COPUS),而您也参加了美国的“生命科学:科学和社会”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向大众传播科学。您担任该项目的顾问委员,并参与跨学科研讨会,讨论18、19世纪的进化和科学研究成果。参与该项目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以自然科学家为主,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参与该项目的心得?
西奥多·库迪切克:2008年至2009年,我第一次参与了“生命科学:科学和社会”项目,当时我参与并组织了一次会议,纪念《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以及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后来,与科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在各种会议上的合作给了我很多灵感。这或许成为我常用的活力教学法的来源之一。
我已经就该项目发表了多篇论文,通过这些论文表达了自己在社会科学和社会进化思想史方面的兴趣。去年秋天,我在科学社会史的国际会议上作了题为“赫伯特·斯宾塞的新拉马克主义”的演讲,将我对19世纪进化和种族理论的最新关注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大英帝国的管理联系起来。我对当下社会理论的发展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关注那些已经形成的理论,特别是英美历史专业领域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理论转向中丢失的部分理论。
张瑾:2014年秋季学期,密苏里大学将开设一门关于社会学核心的讨论课,探讨我们怎样塑造自己,从而适应社会,怎样建设一个适合自身的社会。同时这门课会涉及古今很多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的思想和论著,是一个跨时代背景的社会文化史大杂烩。这种双向适应的问题是很合时宜的。中国的课程也需要学习这样的开放性思维。在历史学中引入社会学理论,不仅有意思,还能扩展学生的视野。作为历史学家,您也关注了社会学和科学方面的研究,您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合作有什么心得和建议?
西奥多·库迪切克:我的研究正逐渐倾向于运用跨学科视角,这也是我不同于密苏里大学历史系很多其他老师的地方,所以我在学校其他院系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不管你喜欢与否,跨学科研究是未来的方向。在美国,历史学界对跨学科的挑战应对非常缓慢,这是短视的,不利于学科发展。考古学、古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在以发展的方式来研究过去,历史学也应重视跨学科研究。或许在中国,你们能避免我们所犯的错误。
张瑾:您提到了常用的活力教学法,我觉得您的读书讨论课也很有启发性。每次讨论课的内容都围绕近几年学者的历史作品、半世纪前历史学家的著述或是更早期的文学作品而展开。您会提前给学生提出若干个问题,或让学生自己先提出问题,从而引导他们思考。有的问题是假设性的,比如:如果这本书是在2014年的今天所写,你觉得需要在作品中加入或改变一些章节吗?这类问题能扩展学生的思维。您的读书课启发了学生学习和借鉴历史学家的写作方法和理论。请谈谈您在教学过程中的心得。
西奥多·库迪切克:与生物学或物理学不同,历史不是累积知识而成的科学,“新”历史很容易排挤那些仍有价值的“老”历史。年轻一代的学者需要追求自身发展,打破长辈的旧模式,但如果完全遗忘旧的学术传统,年轻人终将白费力气。作为教师,我要告诉他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历史仍然有用,也要让我自己的头脑保持开放状态,理解为什么在今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占主流的社会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主宰西方史学的文化史所取代。我也很好奇,中国的史学发展是否也有类似的转变,中国史学的发展与西方有何不同。
爱国主义在当代美国染上玩世不恭的色彩
张瑾:您在密苏里大学工作已超过25年,是什么吸引您在这里任职这么久?
西奥多·库迪切克:我来到密苏里大学时,当时的历史系与现在相比,倾向更“左”。住在哥伦比亚有许多优点,出行方便,几乎没有什么拥堵或污染,对养育孩子而言,这里是个好地方。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城市的刺激,但现在发现,我的工作和生活更需要一个放慢脚步和亲近自然的状态。生活在一个保守的州,能让我熟悉今天主宰美国政治的白人中产阶级正统舆论的主体所在。
张瑾: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在国葬典礼中的演说强调了爱国主义,请您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谈谈现代美国爱国主义和民主与古代雅典的异同。
西奥多·库迪切克:现代美国民主和古代雅典民主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我认为,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应急反应证明了美国公民能在边界和生活方式受到直接和实际威胁时,搁置各自利益与分歧,团结起来保卫自己。例如,我希望我会为保护自己的言论权利而斗争,而别人也会为各自的“美国梦”,以及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去斗争。但是以下三点却让我发现,现代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在实践中难以维持。
首先,我们大多数政治领导人擅于利用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推动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内外政策。如果战争的目的在于让一个狭隘的经济精英阶层变得强大,或者实现一小撮人的想法——美国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世界,这样的战争难道值得爱国者支持吗?雅典有一些真正敌对的邻国,但美国却没有必然的敌人。过去70年,美国所有的战争,不是干预那些弱小国家的事务,就是为了统治世界。自伯里克利时代之后,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互联和联合国等跨国机构存在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把自身对“人权”的狭隘定义强加给别国。
其次,与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不同,当代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认同“自由”。首先是对消费自由的认同,这就导致了高度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世界观,与伯里克利所赞美的自我牺牲不同,多数美国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认为只要不花太多的钱,不牺牲自己的孩子,以空投炸弹为主,在下层社会招兵,用机器人或无人机作战就可以。一旦战争需要在人命或金钱上付出高昂的成本,如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人们就开始质疑战争是否真的值得,然后公众此前对战争的支持就会迅速蒸发。
再次,那些年长的、处于中下层或工薪阶层的白人男性,尤其是住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白人男性对爱国主义响应最为积极,也最坚持。但这一阶层通常是一个衰退的阶层,其成员以前在商业或制造业领域有良好的就业机会,现在发现很难复制父母一代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爱国主义”带有怨恨和怀旧之情。由于他们对外国人、少数民族和政治左派怀有恐惧或憎恨心理,因此茶党和共和党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用美国被敌人包围的说法轻易说服了这个群体。而他们也听信了媒体的说教,认为自己每况愈下的生活应该归咎于外国人、少数民族和政治左派,结果却酿成真正的悲剧:这些人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而共和党人在上台后所制定的政策恰恰有损前者的经济利益。我所在的街区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儿子在阿富汗失去了生命,但他们依然在门前的院子里插满美国国旗,因为一旦去除这些旗帜,可能会让他们对儿子的死因产生疑问,他们无法让自己去思考残酷的现实矛盾。
20世纪的美国,尽管阶级不平等依然存在,但当时的美国似乎朝着一个真正的精英管理与平等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政府、企业还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很难相信存在普遍的平等。爱国主义在当代美国染上了玩世不恭的色彩,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
对外开放既是古代雅典的一个强大实力,也是今天美国的最大优势。不是通过派出军队、传教士或经济发展官员的方式来向其他国家的人民施加美国的影响,而是运用最真实的影响力,让其他人到美国实地考察,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但这种自信的爱国主义,还必须伴随着谦卑的精神,我们应该用足够开明的态度向其他国家学习,美国人在这方面应该更努力。
“美国梦”一定程度上已边缘化
张瑾:尽管“美国梦”这一概念在1931年的《美国史诗》中才出现,但自美国建国以来,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深信不疑,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就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您看来,今天的美国社会中,“美国梦”这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存在?
西奥多·库迪切克:“美国梦”就像所有优秀的口号一样,发挥了作用,因为它是模糊的,所以可以容纳多重含义,如果其中一层含义失灵,这个概念仍然能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经典的“美国梦”概念是指人们通过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摆脱贫困和压迫,获得自由和富足。不过,今天这个梦想对许多过去40年来的移民而言仍有意义,但对当地的白人来说却越来越不起作用。
“美国梦”的含义中也包括了创建许多不同种族的“大熔炉”,让各族人民都成为忠实的“美国人”,虽然是以意大利裔美国人或犹太裔美国人等连字符的形式存在。尽管不同梦想间依然相互关联,但总的来说“美国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
作者介绍:
张瑾,1982年生,女,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博士。2009—2010年曾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访问学者。2010—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12年10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世界史研究工作,现为西欧北美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