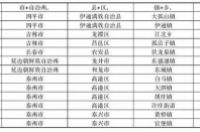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发展不断提速,并在新世纪之初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与市民社会安全感的增强完全同步。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城市(或曰超大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必然遭遇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城市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层面,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和锻造特大城市防范和治理新型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城市既有包括道路、建筑物等人造基础设施以及自然条件在内的物理属性,也有由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归属感及城市文明的社会文化底蕴所构成的文化属性,亦是一个各种生产方式、权力机制以及多元价值追求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的社会。城市始终处在建设更新的过程中,其社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再生产等多重因素之间或协作或冲突的相互作用,会使城市社会的发展变化异常复杂并相应地面临各种阶段性风险。
从城市发展过程来看,公共风险的累积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来源构成。随着城市人口与建设规模的扩张,各种资源、市场、信息等在城市聚集,城市日益面临诸如秩序失衡、人口对环境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压力加大等结构性风险;当城市活力不足,进入相对衰退期时,城市的风险则会系统性地爆发,如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会增加社会的贫困,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住房的紧张会导致公共安全、社会冲突的增长。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以纽约、伦敦、芝加哥、底特律等为代表的欧美大城市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经验教训。反观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许多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空间密度也正逐步接近各种资源承载能力的临界点;而且,由于经济动因与“利润延伸”被长时间地放在城市开发和发展的优先位置,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在规模上滞后、质量上低下、老化的速度过快、更新缓慢,各类新建项目又缺乏基于整体层面的公共安全评估的系统规划;同时,公共安全意识缺乏,面向高度开放的城市中人口异质性所提出的公共安全的多样性教育非常薄弱。这样,如果特大城市不能及时有效地自我更新,不能在制度和政策领域进行系统性的调整和完善,就不得不随时面临各种公共安全事故爆发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危机。
多阶段多类型风险集聚的复杂性认识
作为人口、资源、资本、信息、科技及时尚中心的特大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高度开放使其风险呈现出密集性、流动性和叠加性的特征。相比于西方特大城市从前现代到现代、后现代的漫长发展历程,我国特大城市的扩张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其风险结构也呈现出全球化与本土化、不同社会阶段的特征相互叠加的复杂性。随着特大城市面向未来发展“全球城市”的进程不断加快,与流动性、开放性相联系的各类社会风险也将不断涌现。正如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的,21世纪经合组织国家将面临严重的新兴系统风险,即人类赖以生存的医疗卫生系统、交通运输系统、能源供应系统、食品和水供应系统、信息和通信系统都将遇到威胁。这种伴随深度全球化而来的社会风险和新兴系统风险,还可能首先在各国中心城市传导或转嫁,形成风险在空间上的累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阶梯性、不均衡的特质,不同历史阶段的风险共存于同一时空,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叠加。这种复杂的风险结构使得特大城市即使在遭遇诸如火灾、水患、流行疾病等传统风险时,也可能会因其人口的高流动性和高密度性而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因此,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的叠加聚合效应,是当前我国特大城市治理需要认真应对的重大挑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要求,为特大城市的风险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方向。这也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特大城市风险的叠加与聚合特征及其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比如,上海今年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城市安全任何时候都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为落实这一政策,必须想方设法从传统政府一元主体主导的行政化风险管控体系转型升级为多元化、系统化的风险治理体系。
由于特大城市的风险结构及其破坏性后果的不确定性,需要更科学更系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比如在风险的识别与分析上,形成及时有效的风险信息提取与反馈机制,利用多元渠道把握风险的来源与扩散的路径;在复杂风险与危机的处置上,形成以政府管控为主,多部门、多力量有效协调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在风险的事后管理上,建立严格的考核与评估制度。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认真思考特大城市风险生成的社会与文化根源,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政策安排、机制设计,尽可能地消除各种复杂风险生成的诱因。
更进一步看,以系统治理的思路来应对特大城市的风险,还必须考虑如何确保以科学理性严密编织的风险治理制度网络的有效运行。针对国内各特大城市风险治理制度体系(或预案)存在着的模式化制度安排与复杂化现实的严重脱节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充分发挥各级组织“高位推动”和跨体系动员的组织能力,推动各部门“守土有责”,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制度化责任链条,并将其纳入法规框架,以促进系统治理中跨部门的系统整合与动员;二是合理制定关键决策者的激励机制,修正城市管理者政绩观,降低其决策风险,并围绕风险治理的投入产出比形成新的绩效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