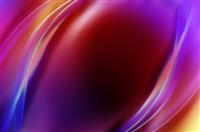城市作为人类生存的区域空间, 本身是与乡村相对应而存在的, 两者的关系复杂而多元。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历经各种变化, 到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 城市最终取得对乡村的支配权。正是在这一时期, 欧洲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和乡村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文明的转型。(1) 城市化 (或称城镇化) 与工业化相伴生, 成为现代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传统农业社会也逐渐被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所谓乡村城镇化, 一方面体现为城市对乡村的“剥夺”, 如原有城市向郊区的扩展, 或乡村人口的外流, 农民变为市民;另一方面也包括乡村自身的发展, 乡村变为城镇, 或乡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城市化和现代化。(2)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 无论是城市化, 还是“乡村城镇化”的表达, 均暗含了以城市为中心的论调, 将乡村看作城市的对立物, 强调乡村对城市的依赖和仿效。(3) 但实际上, 城市化过程本身并不能脱离乡村视角孤立地看待, 有关城市化的探讨亦离不开乡村这一参照物。另外, 乡村社会的变迁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乡村受城市影响, 或为城市所征服的历史, 乡村和城市是在相互的影响与协调中共同发展的。(4) 与19世纪相比, 20世纪下半叶的城市化及其内涵的转变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因此, 对乡村城镇化进程的研究, 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反观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路径及其与城市多重联系的切入点。本文以法国为例, 选取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两个时段, 在考察法国乡村城镇化进程及其特征的基础上, 尝试思考城乡关系在这两个集中城市化时期发生的转变。
一、工业化的冲击
在布罗代尔看来, 直到1914年, 甚至可能到1945年之前, 法国都是一个“古老的、以农立国的法兰西, 即表现为集镇、村庄、村落、分散的住所的法兰西”。更确切地讲, 是一个“城市-集镇-村庄”共同构建的空间体系, “城市与村庄、城市与集镇、城市与城市的众多联系不厌其烦地在编织法兰西的物质生活网, 而城市则在其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作为乡村的寄生者、剥削者, 城市支配着乡村, 但又把乡村的重要性提高到城市之上”。(1) 如何理解布罗代尔这段看似矛盾而又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不妨从他对这一空间体系架构最为形象直观的描述入手:
村庄和集镇的基层居民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在一个集镇的四周, 中间相隔一定的距离, 团团围着几个村庄, 就像一些小行星环绕在太阳四周一样。集镇和村庄加在一起, 通常同我们现今的一个“区”差不多大小。作为集中居住的基本单位, 这些‘区’又环绕在一个相当活跃的城市的四周:由此形成的面积不大的整体, ……称之为‘地方’。这些‘地方’又分别纳入到一个区域、一个省的范围之内, 其成功和顺利的程度取决于中心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向心力。建筑的构架逐渐趋向完善, 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民族市场。(2)
布罗代尔认为, 正是城市、集镇和村庄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将法兰西从分散状态粘合为一个整体, 而其中乡村和集镇在很长时间里构成传统社会的基石。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 整个19世纪, 法国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绝大多数。19世纪上半叶是法国人口增长时期。1811年, 法国乡村人口约为2340万, 占总人口的79%;1841年, 乡村人口增长到2690万;1866年达到3050万, 占总人口 (3800万) 的70%。(3) 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的展开并未迅速改变法国的人口结构。在欧洲早期工业化国家中, 法国的城市化程度远落后于英国和荷兰, 甚至后起之秀德国。根据1866年的统计, 法国共有市镇37548个。(4) 其中乡镇 (即人口少于2000的市镇) 34767个, 2000到10000人的城镇2595个, 人口超过10000的城镇186个, 超过20000的城镇仅有73个。(5) 如果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市化程度, 英国早在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便已过半, 德国是在1891年, 法国则迟至1931年才达到这一标准。(6) 但是到1975年时, 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国人都居住在城市。法国的人口在1851到1975年间增长了1600万, 城市人口增长了4倍以上, 乡村人口反而下降了1050万。(7) 由此可见,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城市化扭转了法国传统的城乡体系, 缓慢而彻底地改变了法兰西古老的空间结构和面貌。正如彼得·克拉克所言, “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消退。城镇经济生活不再像之前一样依附于农村, 而是逐渐由国家和国际势力所主导”。(8)
不过, 尽管相对滞后,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作用, 对历经大革命之后仍执守农业传统的法国乡村社会仍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乡村在“被城镇化”的过程中开始直面现代化。
一些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逐渐发展为工业城镇。里尔东北部的鲁贝是从大乡镇发展为工业城市的成功典型。(1) 在利穆日 (Limoges) 的东南面, 路易十八的前首相德卡兹公爵于1826年建起一座由银行家、贵族和商人共同投资管理的煤矿企业, 到1840年成为法国第四大工业企业。之前小小的德卡兹维尔 (Decazeville) 则发展成一个8000人口的小城镇, “孤零零的”座落在乡村世界中。居民大都是矿工, 住在简易房屋中, 有来自英国的全职工人, 也有来自附近乡村、仍从事农业生产的半熟练工人。(2)
位于城市附近的乡镇随着城市本身的急剧扩展, 也会转变为城郊或工业中心, 纳入城市共同体的范围。离巴黎9公里之遥的阿尔让特伊 (Argenteuil) 直到1840年代仍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 有少数人为巴黎供应石膏, 或经营酒店、塞纳河的摆渡等。到1870年代, 它已被纳入巴黎的城市范围, 成为工业外郊, 这里建起了工厂、船坞和高耸的铁路桥。阿尔让特伊离新建成的圣拉扎尔火车站仅15分钟车程, 很快也成为巴黎人休闲放松之所, 出现了划船俱乐部和供出租的别墅。连大名鼎鼎的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 也为之吸引, 1872至1878年间居住于此。(3) 有些城市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甚至快于城市本身。1836到1856年间, 巴黎、里昂、勒阿弗尔和里尔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在0.4%—1.3%之间, 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则高达3.9%—7%。这些郊区到1870年左右已与城市中心密切联系在一起, 成为城市的一部分。(4)
另一个直观的体现是法国学者所称的“乡村人口外流”。七月王朝时期, 人口增长对乡村资源的压力与日俱增, 出现了乡村人口外流的第一个高峰。1830到1850年间, 每年平均约有4—5万人离开乡村迁往城市。(5) 季节性的人口流动在19世纪中叶则高达50万, 后者是19世纪上半叶农村人口迁移的主体。(6) 不过, 以季节性为主的人口流动“并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城市化运动, 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在传统社会框架内的人口流动”。(7)
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高峰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工商业发展给城市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同时, 以巴黎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的修建, 为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提供了便利。根据莱维·勒布瓦耶的统计, 1841—1851年乡村移民人数为84.9万, 比前一个十年翻了将近一番, 1851—1861年规模继续扩大, 达到126.5万。19世纪50—60年代是乡村人口外流的高峰, 每年约有13万人从乡村流向附近的城镇或巴黎。此后,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乡村人口外流的规模均保持在年均10万人以上, 根据工业发展的节奏略有波动。(8) 到1911年左右, 2000人以上的城镇中居住的人口已从1851年的25.5%增加到44.2%。同期不仅乡村人口的相对比重下降, 绝对数量也有所下降:从1851年的2700万减少到2200万。(9) 虽然季节性移民仍然大量存在, 但永久性移民无疑是19世纪下半叶乡村人口外流最突出的特征, 我们可以将之看作乡村城镇化的一种表现。
二、“走出乡村”
对农民而言, 走出乡村、变为城里人并非易事。背井离乡的理由多种多样, 但去往哪里?从事什么职业?如何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这些才是离乡者面临的挑战。根据保罗-安德鲁·罗森塔尔 (Paul-AndréRosental) 对44534份婚姻登记的样本分析, 在19世纪的人口迁移中, 远距离的跨区流动只占7.5%, 其中20%前往法兰西岛, 而且大都来自北部的诺尔省和巴黎盆地东部省份。布列塔尼、比利牛斯地区和东南部的移民即使跨区流动, 也更多前往较为发达的临近地区。不过, 铁路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远距离流动。1803—1849年, 跨区流动的比重仅为3.9%, 1880—1902年达到12.4%。(10)
乡村人口流动存在地方差异。1881—1891年间, 以1881年人口为基数, 外流人口比重超过10%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区。如西部的阿摩尔滨海省, 西南部的多尔多涅省、科雷兹省、朗德省、阿列日省, 以及南部的阿韦龙省和洛泽尔省等, 这些地区外流人口均占到本省人口的15%以上。比重介于10—15%之间的省份主要位于法国中部一线和中央高原南部。北部的法兰西岛和上诺曼底, 东部的香槟地区, 中部的卢瓦尔河地区, 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以及阿基坦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则是移民流入最多的地区。位于卢瓦尔河沿岸的安德尔-卢瓦尔省 (Indre-et-Loire) 是一个移民接收区, 1906—1911年间移民净流入占人口比重为17.8%, 但这里人口少于2000的乡镇人口净流出高达19.3%;紧邻法兰西岛的马恩省比率分别为2.1%和71.7%, 可见这一地区乡镇中的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
大多数乡村移民都在有限的地理范围流动, 或受雇于乡镇工厂, 或前往临近市镇, 以之为跳板再进入大城市, 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南部尼姆地区的乡村丝织业在1850年之后逐渐衰落, 来自塞汶山区和地中海低地的移民则转而寻找诸如店员或裁缝之类的工作, 或者加入铁路建设的大军。还有些移民会先学点手艺再进入城市谋生。比如来自中央高原的农民会在马尔勒 (Marlhes, 卢瓦尔省) 一类小城镇的纺织工场里工作几年, 再前往圣-埃蒂安 (Saint-魪tienne) 的大工厂。1833年出生于索姆省罗兹耶尔村 (Rosières) 的诺贝尔·特鲁甘 (Norbert Truquin) , 先被父亲送到亚眠当梳毛工学徒, 14岁时前往巴黎, 因卷入1848年革命, 被迫前往阿尔及利亚, 1855年回国后在里昂定居下来, 成为一名丝织工人。1865年出生于多菲内的让娜·布维耶 (Jeanne Bouvier) , 父亲在铁路上工作, 母亲种地。这一地区的葡萄种植受根瘤蚜虫害影响后, 举家被迫迁往里昂南部。让娜11岁时被送入附近的丝织厂当童工。母亲后来在巴黎的一家制刷厂找到工作, 带着让娜前往巴黎。在巴黎, 92%的家仆都来自穷苦的移民家庭。1850年之后, 70%以上的家仆都是女性, 她们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0点, 生存境遇仰赖于主人。(2) 此外,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 住房、工厂、学校、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 建筑行业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3) 生产节奏的加快, 工作机会的增加, 打破了农民季节性流动的节奏,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城镇中定居下来。
但要真正融入城市并不容易, 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在城市中出于自我保护, 往往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交圈和居住区。巴黎的情况最为突出:来自奥弗涅的移民主要居住在11区的罗科特路 (Rue dela Roquette) 附近;来自布列塔尼的移民则集中于14、15区的蒙帕纳斯车站附近;阿尔萨斯的移民以东北部19区的维莱特 (La Villette) 为中心居住。直到第二帝国末期, 利穆赞的移民也并未很好地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社区。(4) 即便如此, 移居者的生活习惯和观念或多或少仍会受到城市的熏陶和影响。
乡村外流人口通过各种途径与村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反过来拉近了乡村与城市的距离, 并推动了乡村社会的转变。尽管研究视角不同, 罗杰·普赖斯和尤金·韦伯都将19世纪下半叶看作法国农业和乡村迈向现代化的重要转折点。普莱斯重点探讨的是交通革命和市场结构的转变如何促使法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5) 韦伯的《农民变成法国人》则聚焦于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政治、文化心态的转变。在他看来, 19世纪下半叶乡村世界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并非来自地方和国家, 而是来自城市, 是一种现代化的冲击。(6) 第二帝国时期, 法国的乡村较之以前更为开放。一方面, 更为通畅的公路和铁路网, 乡村地区学校的增多, 1849年之后“便士邮局”的普及, 使村民可以更便利地接触到外部世界。另一方面, 前往城市的移民会带回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或许带有一些炫耀的成份, 对仍居乡土的村民而言也算一种刺激。
紧邻大城市的地区, 富有的农民开始模仿攀比资产阶级的生活。巴黎盆地参观过1867年和1878年博览会的农民, 把铁炉、汽油灯、衣柜、折叠桌、装饰华丽的床具, 以及礼拜日布尔乔亚们穿的衣服带回村里。他们开始模仿城里人, 早上喝杯咖啡, 晚餐来点葡萄酒, 每周吃好几次新鲜肉。(1) 很多回乡的人会带回接人待物的新风尚, 寄回信件、报纸和各种新奇的玩意, 提倡新的生活品味。有些回乡度假, 或退休后回乡定居的人, 会带回城里的各种观念和时髦:他们开始使用餐盘, 炫耀新自行车, 把房子粉刷一新, 装上电灯。在方言盛行的地方, 会说几句法语也被看作是“城里人”的象征。(2)
这种影响还体现在教育日益受到城市移民和农民的重视。很多移居到城里的农民发现读写和算术不仅对工作有帮助, 还可与家人保持联系。即使自己没有机会再学习, 也会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因此, 19世纪下半叶教育的普及既有乡村本身的需要, 也有政府和教育人士的推动。1881年, 法国中部奥弗涅多姆山省 (Puy-de-D觝me) 的昂贝尔 (Ambert) 教区学校并不多, 但入伍登记册上的签字表明这里文盲很少。当地学校教员解释说, 那些迁往城里谋生的父母只有通过信件才能与家里联系, 因此希望他们的孩子都能读书写字。(3) 对农民而言, 教育无疑是离开穷乡僻壤、前往城市的通行证。南部洛泽尔省 (Lozère) 的蓬-德-蒙特维尔村 (Pont-de-Montvert) 可能是全法国最偏僻的村庄。地方议会在1880年成功申请到资金, 分别为四个人口只有120、66、46和20人的小村子建起学校。中央高原南部一向被看作法国落后地区的典型, 到1880年代, 这里已有至少852所学校, 学生人数达到24464人, 学校与学生比为1:29, 位居全国之首。到1881年, 法国85%的男性和77%的女性已能在结婚证上签名, 一个世纪之前仅为47%和27%。(4)
乡村人口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还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和乡村生存空间造成的压力, 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调整,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彼得·马克菲将1852—1880年看作法国乡村文明的顶峰时期。在他看来, 这30年的时间里, 法国农民安稳而富足, 教育、外出、接收新观念都变得更为容易, 无论是语言、文化、生态, 还是生产方式, “此后法国的乡村再没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人文和自然环境”。(5)农业技术的革新, 面向市场的专业化生产, 农民观念的转变……尽管到19世纪末, 法国的土地占有结构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 仍以小土地所有为主, 但乡村世界已缓缓打开通往现代化的大门。然而, 20世纪上半叶接连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这一进程,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法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才重回正轨。
三、“乡村的复兴”
战后30年是法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也是法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1946年至1980年, 法国人口从4000万左右增长到5300万,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53%提高到75%。(6) 尤其是1954到1968年间, 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 年均增长率从1851—1954年间的0.9%上升到1954—1968年间的2.5%。到1975年, 50%的人口居住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 20%的人口居住在2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六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巴黎地区。(7)
这一时期, 城市向郊区的扩张较19世纪下半叶更为突出, 尤其是为应对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住房、交通、服务设施等供应不足的问题, 城市不断蚕食周围的乡村空间和农业用地, 城郊乡村地带逐渐被纳入城市范围。巴黎城市面积在1962到1968年间扩展了13%, 从1457平方公里增加到1651平方公里。同期, 超过5000居民的城镇总面积从30169平方公里扩展到46687平方公里, 增长幅度为52.2%。(8) 法国南部艾克斯 (Aix) 的城市人口从1954年的4.8万增长到1975年的11.5万。位于城西南6公里的米勒区 (Milles) 原是一个2500居民的村庄, 面积约为3000公顷, 1967年之后逐渐被纳入艾克斯的城郊发展规划区中。到1974年, 已有700公顷土地为市政或投资者所购买, 另有150公顷土地属于城市规划带, 共占该区面积四分之一以上。(9)
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带动了周围土地价格攀升, 城郊农民出售土地的情况非常普遍。奥尔良地区以蔬菜、果园和苗圃种植为主, 供应巴黎的市场。人口增长很快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 新的公路、住宅和超市等配套服务设施向城市周边扩展。1965年之后奥尔良西北的布罗斯耶尔区 (Blossières) 果园彻底消失, 附近15公顷土地上陆续建起1200套住房。东北的阿尔贡 (Argonne) 被规划为“优先城市化区域”, 原本计划在这里建设4000—5000套住房, 以容纳1.5到2万居民, 1966年改在城东南的奥尔良-拉苏尔斯 (Orléans-La Source) 进行。土地价格的上涨促使很多农民出售土地后改行换业。1968年, 包括奥尔良在内农业劳动者所占人口比例为4.5%, 到1975年下降到2.8%;奥尔良郊区的农业劳动者的比例则从8.3%下降到3.9%。(1)
与此同时, 城市工业和人口向郊区地带的转移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郊人口的增长。在弗朗什-孔德的卢埃河上游地区, 一个名叫韦伊拉凡村 (Vuillafans) 的薄板轧制厂在1955年提供上百个岗位;蒙杰索亚村 (Montgesoye) 的家具工厂在1957年雇佣35个工人。这两个村是该地区唯一人口略有增长或保持稳定的村庄。位于城市郊区附近的乡镇, 另一个主要的功能是为工薪阶层提供居所。一些不发展工业企业的乡镇, 工薪阶层的人数也在增长。1956年, 少于2000居民的乡镇中, 在工商企业工作的雇工为89.4万人, 占法国总雇工人数的15%。1962年, 居住在乡镇中的公职人员、雇员和工人多达233.8万人, 分别占乡镇劳动力总数和乡镇人口的33%和13%, 到1968年分别增长到39%和15.7%。(2) 乡镇中水电、住房、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 轨道交通、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提供的便利, 尤其是相比城市更为便宜的房租, 使工薪阶层更愿意住在远离城市或工厂的乡镇, 工作地与居住地相分离。
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工业乡镇和农业乡镇职能的分化, “城市化”这一概念也因此得以扩展。不仅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等术语, 而且城市规划中专门提出了所谓的“工业或城市人口聚居区, 专门用来指代在城市或工厂工作、在乡镇中居住的人群所形成的聚居区。1962年, 有6544个乡镇被包括在此类聚居区范围内, 1968年增加到6608个。在812个范围较为明确的聚居区中, 有479个既包含乡镇也包含城镇, 有84个则完全是乡镇。(3)
20世纪70年代之前, 大多数远离城市聚居区的乡镇人口持续外流, 其年均人口增长率从1954年到1975年保持在负0.8%左右。与此同时, 位于城市聚居区周围的乡镇人口则呈上升趋势, 1954—1962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27%, 1968—1975年提高到1.28%, 1975—1982年达到1.93%。1975—1982年, 超过20万的大城市人口平均下降了5%以上, 郊区人口略有增长, 但速度也有所放缓, 唯有城市周围乡镇的人口增长比率最高。(4)
不过, 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村地区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统计数据显示, 1975—1982年, 远离城市聚居区的乡镇年均人口增长率从此前的负0.8%变为正0.5%。这一时期, 城市年均人口增长率仅为0.2%, 乡村地区则高达1.07%。(5) 部分地区乡村人口的回升出现得更早。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 自1968年起, 除卢瓦尔省之外, 其他几个省乡镇人口增长率均从负增长变为正增长。伊泽尔省和上萨瓦省的乡镇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1.06%和1.55%。(6)
无论是城市近郊工业乡镇人口的增长, 还是较为偏远的农业乡镇人口的缓慢回升, “乡村的复兴”自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普遍现象。(7) “乡村的复兴”包括郊区的城市化, 更多用来指代与“乡村城镇化” (8) 相伴随出现的人口向乡村的回流。(9)
乡村吸引力的增加得益于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法国政府从50、60年代推出一系列农业和乡村改造计划, 并设立“乡村更新区”“山区经济区”, 出台“乡村整治规划”, 主要针对发展较为落后的乡村地区, 着力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 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 尤为注重服务业、住房和旅游业的发展。除道路、交通的改善外, 早在20世纪20年代, 电力便已在法国大部分乡村普及。自来水的普及始于20世纪50年代, 1954年自来水仅惠及41%的乡镇, 1966年达到68%, 1980年左右, 98%以上的乡镇都安装了自来水。(1) 商业、邮电等服务体系也日趋完善。位于法国西北部布雷斯特 (Brest) 附近的吉勒尔村 (Guilers) , 原以农业生产为主。1951年该村有居民2161人, 1968年减少到1849人, 劳动力占全村人口的35% (不满20岁的年轻人占39%) 。1954年有435人从事农业生产, 到1971年仅剩230人, 农业雇工的人数也从77人减少到18人, 大多转向第二产业。1969年, 村委会在原来的老村之外另建起250间新住宅, 形成新的居民区, 并致力于商店、学校、运动场地等配套设施的改善。1969年之后, 该村移民的数量逐渐超过外流人口数量, 人口开始缓慢回升。(2)
乡村生活条件日益便利, 不同于城市的自然空间和田园风貌,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群体前往旅游或定居。1966年, 法国乡村接待游客总数为440万, 1970年达到706.6万。1969—1970年的调查中, 35718个被看作乡镇的村庄, 有17200个左右都接待游客, 也就是说50%左右的村庄都发展旅游业。其中有5000—5500个旅游乡镇接待的季节性游客人数超过其常住人口的50%, 海滨乡镇的这一比例更高。(3) 此外, 越来越多的本国或外国人在乡村中购置房产, 作为退休住所、度假别墅, 或是房产投资, 在法国称为第二居所, 第二居所往往成为乡村旅游业住宿接待的主体。乡村中第二居所的数量在1954年为33万套, 1962年增加到63.8万套, 1968年达到74.6万套, 占乡村住宅总数的13%。(4) 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是仅次于巴黎的法国第二大旅游圣地, 这里第二居所的购置数量自1975年之后20多年的时间翻了一番, 1999年为41.5万套, 占法国第二套住宅比例的16%, 位居全国之首。(5) 一些地处偏僻的村庄也同样受到城里人的青睐。圣伯纳 (St-Bonnet-le-Froid) 是位于中央高原上卢瓦尔省的一个小山村。1968到1990年, 这里的居民人数从145增加到180人。外地人在此购买第二居所的数量增长了45%, 而当地新建民居的数量仅增长了15%。村里建有24家店铺, 其中有3家宾馆, 5家餐厅, 70%的人都从事与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相关的工作。(6)
“乡村复兴”带来诸多结构性的影响。乡村人口的回升, 尤其是定居者的增加和休闲旅游业的发展, 对乡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等配套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促使乡村更为注重保护自身特有的自然和文化景观, 增强吸引力。在1968年, 法国乡村中超过80%的房屋都超过50年历史, 50%的房子甚至超过一百年。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法国农舍”运动, 使大量因人口外流被空置的房屋得以重新利用。这些旧房也成为乡村的建筑遗产, 在不改变外观的基础上对之加以改造。此外, 新的道路、住宅、服务中心和公共活动场所的修建, 在乡村中形成新的居住区。乡村这一曾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空间, 获得了新的商业价值, 日益成为“逆城市化”时代新的居住、消费和休闲的场所。
与此同时, 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较大的转变, 乡镇的功能日趋多样化。农业生产者在大多数乡镇的比例有所下降, 乡村社会结构呈现出多样性。根据1975年的统计数据, 农业劳动者 (含农业雇工) 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1%, 其他职业者占59%, 其中工商业老板15.4%;自由职业者13.6%;雇员13.1%;工人48.7%, 公职人员6.4%。(7) 有些以旅游业为主的乡镇或工业乡镇, 非农人口所占比重更高。根据贝尔纳·凯泽 (Bernard Kayser) 的研究, 法国乡镇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小型的老龄化农业村庄, 居民主体多是老一代的农民和退休人士。二是位于城郊、完全从属于城市的工业乡镇, 主要从事工业生产或提供居住等服务。在这两者之间, 存在一种新型的、与城市有着共生和互动关系的乡村世界:有为市场而生产、农业生产者占主体的农业乡镇;有社会结构多样、非农产业占主体的综合性乡镇;也有以定居或休闲娱乐为主的旅游乡镇。(1) 1996年法国国家统计局专门调整术语, 将法国的市镇区分为城市主导型空间和乡村主导型空间。从这一层面而言, 到20世纪末, 乡村似乎取得了与城市相对等的位置。
余论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是法国乡村城镇化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 在乡村社会经济功能转型的同时, 城乡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19世纪的工业化浪潮, 开启了法国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变迁之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 城市主要以一种“掠夺者”的形象出现。(2) 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张, 不断挤压、蚕食农业生产空间和乡村景观, 同时也将大量农民从乡村中剥离出去, 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掠夺”客观上缓解了乡村人口过剩、土地资源不足的窘况, 也打开了传统乡村社会通往现代化的大门。交通道路的改善、通信工具的日渐普及, 以及外流人口从城市带回的新观念, 将乡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同时, 也带来了乡村生活方式、教育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但究其实质而言, 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乡村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附属空间, 城乡关系体现出一种二元的对立性。
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 法国乡村在历经一个半世纪的人口外流之后, 重新成为现代人定居生活、休闲娱乐的偏爱之地。“乡村的复兴”带来了城乡关系的新变化, 作为“掠夺者”的城市开始“反哺”乡村, 城市和乡村从对立走向互动和互利。过度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病”, 衍生出一种对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观怀旧探幽之情的“思乡病”。“重返乡村”带来了乡村的复兴, 赋予乡村空间以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一方面, 乡村生活方式的日益现代化, 代表着对城市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 乡村也力求保持其不同于城市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特质, 这种独立性正是其魅力之所在。便利快捷的城市生活与休闲放松的乡居时光, 共同构建起现代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图景。
综而观之, 若干世纪以来, 以小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网状布局依然存在, (3) 以之为桥梁, 乡村与城市以更密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两者之间的“鸿沟”似乎趋于消解, 尤其是布罗代尔所说的“乡村的重要性”再度被凸显出来。与此同时, 也要看到这种“复兴”给乡村空间带来的挑战。城市的扩张对农业用地的侵占, 外来者的涌入对乡村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破坏……乡村如何避免再度为消费主义的热潮所“蚕食”?相比于马克菲所说的19世纪下半叶乡村文明的顶峰, 20世纪下半叶法国的乡村社会无疑更为现代化, 但如何保留住他所看重的往昔乡村“丰富多样的人文和自然环境”, 这才是后城市化时代值得深思的问题。
基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欧洲农村城镇化进程及借鉴意义研究” (14JZD038)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