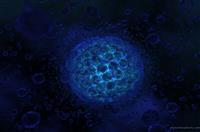
73岁的王永金每天踱步到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同来的同事越来越少,去年,79岁的杨泽民去世了,另一个老头张志林患上脑血栓,卧病在床。
办公室人气渐息,已面临搬迁。只有周杰和姜琦还常来,他们原是沈阳药科大学的党委书记和副校长。
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人工熊胆课题组成员。他们一辈子试图用人工合成中药的方式,替代活熊取胆的药品。
这是一个持续了30年的科研课题,至今悬而未决。当年有一名大学生刚毕业就参与课题组,现在已退休4年,仍未等到药品审批通过,他摇摇头,“很憋屈”。
如果不是眼前这场全社会对活熊取胆行业的质疑浪潮,没有人会知晓他们。一名环保人士感慨,“人工熊胆”如能成功,就能真正对养熊业起到“摧毁性作用”,上万头黑熊的命运也才能扭转。
埋下矛盾的批件
“目前引流熊胆产量已暂满足药材所需,也请开发时综合考虑。”
2月27日上午,王永金翻开4层塑料袋,掏出一个绸缎小盒,岁月已磨损了绸缎面的光泽。里面躺着几支小试管,装着二十多年前的实验样品。借着光线,老人说:“看,琥珀色的,跟真的熊胆一模一样。”
30年前,1980年代初,当时沈阳药科大学还叫沈阳药学院。学校的动物药室主任有一次参加了全国中药材会议,带回一个消息:国家要求研制贵重中药材的代用品,包括牛黄、虎骨、麝香和熊胆等。
那是计划经济和集体利益至上的年代,在一次党支部学习会议上,时任辽宁省医药研究所合成室主任的杨泽民对时任沈阳药学院测试中心主任的王永金说:“现在国家熊胆短缺,我们是党员,要响应国家号召。”两人一合计,开始筹备“人工熊胆”研究。“当时药学院对胆酸类、动物药研究有基础,而且,大型设备的分析力量在全国都属于前列。”王永金回忆说。
1983年8月,“人工熊胆”科研项目正式立题,杨泽民任组长,王永金是副组长,项目由沈阳药学院和辽宁省医药研究所(后改名为辽宁省医药工业研究院)共同承接。
最初的时光是显赫的,“学院投入了顶尖的力量,前前后后有上百名研究人员。”周杰回忆说。耗时6年后,课题组完成了药理、毒性、动物试验等各项前期工作,上报给当时的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当时药品审批权限还在卫生部。1990年,课题组就得到了二期临床试验的批件。
审批结论称,“人工熊胆”在质量标准、长期毒性等方面均已符合药审要求,并认为该药较日本产品近似天然,而且由人工合成制备比人工引流熊胆粉不影响生态平衡。
然而,令专家们耿耿于怀的是最后一句话:“目前引流熊胆产量已暂满足药材所需,也请开发时综合考虑。”“这句话是代表了熊胆粉(指活熊取胆业)的利益。当时很明显分成了两派意见,批件偏向另一边。”王永金事后分析。
这样的揣测并非臆测,自1980年代初中国从朝鲜引入引流取胆技术之后,养熊产业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姜琦依稀记得,1988年引流取胆制备的熊胆粉就开始审批上市。周杰当时还被卫生部邀请去成都参观一处养熊场,同行的有二十多名专家。他看到五百多头被固定在铁笼里的黑熊,身上插着一根导管,不得动弹,只能嚎叫。
如今致力于拯救黑熊工作的亚洲动物基金外事总监张小海也记得另一个细节,1980年代初,四川资阳一个科技局干部养熊二百多头,被作为政府推广的示范点,“当时养熊业就是政府带领农民致富的新途径。”
“在那个时候矛盾就开始产生了。”周杰如今指着1990年的那份已经泛黄的批件感慨道,只是他们并没有料到,还有整整20年受挫的时光在那等着。
13年补充实验仍未定
“听说国家不审批‘人工熊胆’,企业也不想再投入了。”
课题组的专家们反复分析1990年批件,认为这分明是暗示他们停止研究。但专家们不甘心,“我们采取一是不理会,二是有阻力就耐心说明的对策。”王永金说,因为他们相信,引流取胆终不会长久。
课题组迅速在1992年完成并报送了二期临床试验资料。但他们仍未能得到药品生产的批件,上面要求补充临床试验。
“我们认为这是违反新药审批程序的,应该在一期临床就一次性告知。”姜琦说,“不仅是钱的问题,而且反复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没想到的是,原本只需1年零1个月完成的补充试验,却变成了13年的持久战。
当时,“人工熊胆”课题是由东北两家国有药企投资,后来国企改制风潮下,两家药企都被改制,成为私企了。而一个坏消息从投资方传到课题组,“听说国家不审批‘人工熊胆’,企业也不想再投入了。”周杰回忆说。
补充临床试验是在沈阳、上海的3家医院进行,只需8万多元就能拿到临床资料,资金却意外断链了。周杰被迫开始“跑项目”,其间不乏青睐者。“2001年有一个和史玉柱合作搞‘黄金搭档’的人找到我们,想合作,跑到北京咨询,就没了消息。还有两个香港人,也想合作,结果上北京咨询之后也不干了。传回来的消息都是国家不批了。”
最后周杰自己筹钱,到临床试验的医院取资料,按规定需3个病种480例。由于隔的时间太长了,医院已找不到当年的资料,只拿到了100例痔疮资料。
这时审批部门已经改弦更张,由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下称药审中心)负责新药审批。
养熊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熊、棕熊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禁止商业性出口含熊胆制品,不再批准新建养熊取胆场了,一系列黑熊养殖的技术管理规定也陆续出台。一些环保NGO开始了救助黑熊的行动,与各地林业部门合作,淘汰了一些养熊场。“当时一些养熊场都绝望了,觉得办不下去。资阳那家养熊场在2005年也卖掉了黑熊。”张小海回忆说。
课题组的专家们在沈阳的办公室里,目睹着这些变化,一度乐观地以为人工熊胆的时代就要来了。一名沈阳药科大学的毕业生看中了老师们的项目,投资进来,解决了研究经费的燃眉之急。他们决定最后一搏。
“改名就是前功尽弃”
牛黄、虎骨、麝香等贵重中药材,替代制品也都已经上市,独独熊胆远远被落在了后面。
2005年,课题组收到了第二次补充临床资料的通知,此时,距离课题研发,已经22年过去了。
专家们等不及了,“当初二期临床方案就是卫生部自己委派的专家设计,后来这些补充资料中有些都是重复的。”
课题组的不满还来自一场改名风波。2003年,他们收到药审中心通知,“本品(指‘人工熊胆’)与天然熊胆的功能组织相差悬殊,两者不能互相完全替代,名称为人工熊胆不合理。”姜琦复述了通知内容。
这个结论与1990年批件相差甚远,“我们非常吃惊。”姜琦说,专家们反复研究通知内容,最终决定做出强硬回复:不同意改名。“我们认为,‘人工熊胆’的临床方案是同天然熊胆等量等效替代观察的,按天然熊胆的组织功能设计,而且多次经卫生部药审办通过,评价很高,怎么能说相差悬殊!”
姜琦介绍说,以前往来文函都是用“人工熊胆”的名称,而且经过了两届专家审评会通过,“政策必须要有延续性”。
2004年,药审中心再次下文,又一次要求改名。课题组的态度依然强硬。“改名就是前功尽弃。”姜琦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要把项目坚持到底,并向国家药监局提出,可以重新提出病种补充临床方案,如果还不充足,我们可以做第三期。”
2005年的通知文件最终没有再提改名事宜。两年之后,2007年,课题组将第二次补充资料全部递交给药审中心,再度等待。
在这期间,王永金经常跑去北京汇报,还给相关部门写了5封信,都杳无音讯。而他们推测的“对手”,养熊业却在国家的一再规范下再度飞速发展。早期为脱贫的养熊散户慢慢退出了市场,或者转入秘密养殖。各地出现了不少养殖企业,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商业链条:从养熊场到制药企业,再到营销体系。
截至到2010年5月亚洲动物基金统计的数据,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含熊胆药品已有240种。专家们无奈地发现,1980年代初同期开始研制的牛黄、虎骨、麝香等贵重中药材,替代制品也都已经上市,独独熊胆远远被落在了后面。
药效仍存疑?
“他们的研发赶不上申请时的标准。”
主管部门其实并没有置之不理,2008年、2009年,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召开了两次“人工熊胆”专家咨询会。
高益民参加了后一次会议。他是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前3届委员,参与起草了新药审批法规,“人工熊胆”二期临床方案也是他设计的。
当课题组找到他时,高益民已记不清那次临床方案了,他也很吃惊:“我以为都完成上市了,像这种经过3次评审会都还没通过的,绝对很少见。”
“我内心是希望人工熊胆能够成功,来替代天然的,这样可以避免熊受虐待。”高益民说。他觉得,“人工熊胆”研制的难度不会比牛黄、虎骨等难,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当初他设计的临床方案模式是与麝香的一致,很难理解为何会再三被要求重新补充修改。
为什么迟迟不获批?记者始终未获得国家药监局的采访答复,而药审中心当年组织的一些专家接受了记者采访。
74岁的翁维良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3月1日,他告诉记者:“合成以后的药效能否达到最新的国家标准,通不通过,不能光看研究者的说法。真正要达到标准,需要很多次实验和改进,过程非常复杂。”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郭承伟认为是课题组的人工熊胆仍没有达到当时的国家新药的标准。“他们的研发赶不上申请时的标准。”郭承伟解释说,国家这几年新药审批越来越严格,经常修订。而人工熊胆课题组在前一次没有通过后,按照改进意见进行调整,却没有注意到新条例和评审标准的变化,所以还是不能通过。
而课题组专家们坚定认为1990年的批件已经肯定“人工熊胆”的成效,而且,他们已反复根据标准进行补充临床试验,不应当存在与新药标准不符合之处。
对于“人工熊胆”的有效性,他们很自信。2月27日,王永金拿出一叠材料,指着其中的各项图谱和数据说:“我们做出来的图谱和天然熊胆很相近,说明是可以替代天然熊胆的。”
而且,课题组专家们却觉得审评会上并没讨论技术问题,却一再感到来自养熊业的压力。“有专家提了很奇怪的问题,库存的两吨熊胆粉怎么办?”姜琦说。
2009年那场咨询会会场气氛很凝重。高益民记得自己发言谈了两点,强调政策必须有延续性,不能反复修改,也希望双方都能遵照新药审批法规的指导原则。他说得激动时,拉开了椅子。
最终专家意见不一致,药审中心决定性的文件也一直没有下发。一晃2年又过去了,“我们一直在等,是继续修改还是否决了,我们希望有个明白结果。”王永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