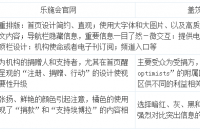Kim 政府能力有限、企业面临信任赤字问题,如何分配公益资源是一项更具战略性价值的事情。公益风险投资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跟其他模式又有什么不同?硅谷社会创投基金(SV2)又是一种怎样的模式?
Lance 公益风险投资能够为个人提供一个以相当系统化的方式去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机会,正常情况下,以个人的力量去创造出巨大的影响力是很难的。这种模式需要的不仅是资金,也需要个人充分调动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人脉资源。SV2把所有相关资源聚合起来,不仅是资金资源,也包括人的智力成果。在这个平台下,好几百名捐赠者每年固定捐赠一定的款额,SV2来决定把这些资金投向哪个民间组织。在硅谷,我们关注的是教育、环境、国际化等问题,我们的捐赠者还各尽所能,提供税务、法律、企业家培训方面的支持。短期来看,资金对于中小型NPO是极其重要的,若以5年期来观察,SV2贡献的人力资源才是改造组织的最宝贵资源。
Nancy 成立一个组织或者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只是第一步,公益风险投资给个人提供的空间是,通过你的毕生所学与所长,把组织发挥其最大效应。当我们把一群捐赠者以及他们所能提供的援助集中投入到某个组织机构这个时候,一些商界的捐赠者会提出:“我们可以通过商业操作手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如果NPO机构能够运用这些商业手段,再加上对社会事业的那股热情,那么结果一定会更好。”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把非盈利事业做成一个商业的盈利模式,才会把它做大做强?
Kim:我们目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单纯把公益事业当做盈利的商业去运作,是不是太过简化了这些问题?毕竟,NPO机构不是纯粹以结果为导向的。
Lance:集体效应(Collective Impact)这个概念在我们所涉及的领域更像是持续性成长 (Continuous Improvement)。即建立起一个NPO的体系,去解决社会问题。举例说,想在加州北部,要播一千颗种子才会长成一棵红杉。平台即土壤,以期NPO组织持续成长。公益风险投资好就好在灵活,可以让参与者选择适合自己的参与模式,以创造尽可能大的效应。
Nancy:公益风险投资的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与刚开始比较严谨、单一的模式对比,现在的模式更加适合个人各式各样的参与。
Kim:在中国,85%的善款来自企业。共同价值也是驱使企业社会责任增长的重要因素。如何影响企业中的个体,让个人也对慈善事业产生“共同价值”,以至于把这种价值融入他们各自的生活中?随着中国人对社会问题越加关注,他们更加需要可靠的平台去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贡献。慈善是一项非常专注本土化的事业,二位却服务于SVPI这么一个国际化的组织。你们觉得公益风险投资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如何把公益风险投资模式引入中国?
Lance:慈善可以说是本土化的事业,但我在SV2一年多却发现,公益风险投资——结合自身能力去做贡献、通过体验式学习去进步——这种模式影响力太大了,因此突破了地域限制。我个人最关注教育,当我专注于社区教育工作时,却发现公益风险投资的模式已经令我融入到整个州层面的教育,甚至是全国乃至世界层面的。
公益风险投资的模式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区已有12年历史,它没有区域限制,是一种能释放人类潜力的工具,虽说中国的慈善事业以企业做慈善为主,但这并不代表公益风险投资不适用于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在社会领域不停尝试各种模式,旨在将更多人才引进社会创新领域,产生良性的社会效应。目前美国有一个针对大学生的项目,允许大学毕业生通过1年的Gap Year参与公益项目。一些大企业会短期(3-12个月)与NPO机构联手合作,企业提供专家咨询、财务分析等支持。此外,美国有不少准备退休但仍想继续做一些有意义事情的人,他们会参与到NPO机构的工作中,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总的来讲,不同的人群,包括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已经在社会上工作过并积累了一定知识技能的毕业生,以及那些即将退休但仍有精力做事的人群,都是值得挖掘潜能的人,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向美国汲取经验,将这些人力资源都引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Kim: 从公益风险投资角度来看,是什么因素能使NPO机构发展成具有高增长空间的组织?什么因素让NPO机构从内部组织上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不断创新的动力?
Lance: 在整个体系下,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能够创造的核心价值。就我个人而言,我以前是经商的,因此我的思维会偏向于通过系统性的方式为机构带来颠覆性的变革与创新,可以说我的核心价值就是创造影响力,为了做到这点,我必须持有开放、大胆尝试的态度。我对某个NPO机构产生兴趣,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机构有一位相当优秀的领导者;可能因为这个机构有相当好的一个项目,比如说Reading Partners,旨在帮助学生读书识字,比很多大型盈利教育培训机构做的还好;又或者是因为这个机构有很好的财务收支模式,在美国很多非盈利机构的收入纯粹来自于慈善捐赠,但是还要其他一些有意思的模式,比如一些教育性NPO机构可以从学校、政府等地方获得援助,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NPO机构会有更大的空间去扩大影响力,解决其关注的社会问题。回答你的问题,看这个机构:一、能聚合哪些人才、人力资源;二、能获取的资金支持有哪些;三、是否具备系统性的发展模式,不管是仅服务于一个社区,还是影响力可以扩散至整个国家。
Nancy:我想以资助儿童行动组(Foster Youth Action Network)为案例,在SV2看来,Foster Care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从某个社区启动,在全国范围广为采纳。这个项目的特色在于,寄养儿童长大成才后,许多还会选择从事与Foster Care相关的工作,帮助更多像他们这样需要资助的儿童。SV2为这个项目带来的并非只是捐款,也不只关注是否这笔款额可以让这个项目维持接下来一年的支出,而是帮助项目建立一种使其持续发展的体系。比如SV2给Foster Care提供教育人才帮助儿童读书学习等。每年SV2在各地举办的会议上也为Foster Care创造了很大的影响力。大多数慈善机构实行1年制捐赠,每年对捐赠对象进行评估。SV2实行的是3年制,我们认为三年才能支撑机构发展,三年间SV2不会严格审查捐赠款项被用于何处,但会经常性的聚合人才帮助机构发展。三年之后的退出是为了要求被资助机构在3年期间学会如何去开辟新的收入路径,形成自身的、系统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Lance: SV2的捐赠虽说是三年期,但并非三年之后与机构脱离关系,他们依然属于SV2体系下。比如Reading Partners和Teaching Center这两个机构,过去5年都没直接从SV2获取资金,但却从SV2广阔的捐赠人网络中获取了上千万美元的款额。SV2对这些机构而言更多的是起催化效应。
Kim:如何看待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和公益风险投资?中美两国在这方面有没有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Lance:我认为从影响力投资到公益风险投资是一种慈善事业的衍化、升级。一百年前卡耐基跟洛克菲勒时代的慈善事业都是以纯粹的资金捐赠为主。随着时代的变迁,尽管现在美国的慈善募资已达到3000亿美金,但增长规模并不值得一提。公益风险投资应运而生,这种模式不仅关注募资,更参与者如何发挥个人才能去推动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慈善事业需要风险资本的投入才能走出第一步,接下来才会有第二步,也就是考虑如何把人力资本融入其中,创造更持续的价值。
Nancy:中国的影响力投资要做起来,必须要有明晰的标准,要有一套准则可以供那些新兴的草根NPO机构参考,让它们对自身的使命、目标、运作模式有一个完整的想法。中国可以向美国汲取很多经验,避免出现美国曾经面临的效率不高的问题。
Kim:中国的社会事业比起美国还有一个突出的不同,就是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协作非常频繁,政府、企业、个体之间等等。它们之间的交界似乎是一种常态,有助于帮助NPO机构更好的去创造社会影响力。在美国,政府与民间团体之间基本是没有交界的,没有形成“集体效应”和“共同价值”。
21世纪:你印象最深的中国社会企业是哪家?在美国有没有与之相似的社会企业?
Lance: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家政假期培训学校,开始我以为他们只是为农村妇女提供假期缝纫、烹饪或清洁这种无关紧要的课程,结果我发现这所学校实际创造了一整个产业,为她们开设银行账户定期汇入工资,鼓励雇主为她们办理医保乃至教育雇主要尊重她们的劳动和人格。
Nancy:西雅图有一家残疾人培训学校为波音公司定向培训雇员。残疾学生接受技能培训后会在模拟工作环境的工作室实习,然后被波音公司雇佣。他们也会随时回到学校再深造并考取更高的职称。
Kim:请两位嘉宾寄语中国公益事业。
Lance: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从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到普通人对此都抱以极大的热情和期望,而人,是公益风险投资最大的宝藏。社会影响力投资与公益事业的结合将来会为中国第三部门带来令人炫目的高速发展。
Nancy:这次中国之行我看到中国人对新型公益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开放性和好奇心,所有社会部门之间正在建立的互相信任的机制,比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看到的都要令人激动。我认为中国已经站在了飞跃式发展的临界点。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什么是社会企业,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尤努斯的定义是一个企业有老板,有投资人,但是不分红。还有一种定义就是收益很低的,不是追求高收益而是追求社会功能的企业。我不完全同意这两个说法,第一,它一定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公益组织,也不是政府机构,但是他做的事情对社会公益有贡献。所以他是企业就必须要创造财富,他必须赚钱,既然是企业就必须得赚钱。所有的企业都赚钱,社会企业跟其他企业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正的外部性,对第三方产生好的影响,比如说办教育,比如说做低价太阳能热水器,节约燃料就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企业是做买卖的,买卖就有供给方和需求方,你这个企业的供给方或者需求方,有一方是弱势群体,这就是社会企业。
蔡史印(黑暗中对话中国负责人):我们在德国总部公司名字就叫“对话社会企业”,我同意您的观点,如果不能赚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靠一种自负盈亏的方式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但是,赚钱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商业企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我们以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成果作为最终目的。
茅于轼:我问你一个问题,老板能不能分赚得的钱?
蔡史印:我们是全球连锁,每个加盟企业有自己分配方式,现在中国大陆区是3:3:4,也就是说30%是留在企业内部自我发展,30%进入视障人员教育基金,40%分红。
茅于轼:我很赞成可以分红,投资人可以从社会企业分红。你给做社会有益事情的人回报,这对于社会企业的繁荣是有好处的。
王崇颖(南开大学行为医学中心主任):我很同意,我首先是教师,然后才是社会企业家。作为科研工作者,做社会企业最大意义在于我希望把那些比较成熟的科研成果尽快的让这些家庭和自闭症孩子受益。对于我来说做社会企业更多的是责任,除了企业本身性质之外就是责任。
茅于轼: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为需要帮助的人做工作,这是符合社会企业的一条,但是还有一条,你是不是赚钱的?
王崇颖:是赚钱的,不然生存就有问题,首先要自己生存没有问题才能帮助别人。
茅于轼:还有一个需要重点区别——慈善事业与社会企业。企业没有权力向社会募捐,社会把钱捐给你了,结果你分红给了老板了。社会企业是企业,是企业就一定要赚钱,而且要能够分红给老板,投资人可以得到回报。企业是不可以募捐的,如果是慈善机构就要募捐,这是不同的东西。我们社会有一个毛病,拿自己的钱做慈善大家说好,如果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还赚了钱,就认为你不好了。这个说明我们评价标准有问题,损己利人很好,但是利己利人不是更好吗?社会企业做的就是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