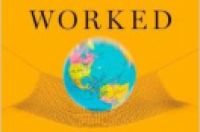随着美国国会选举的临近,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健康及其全球领导力未来的争论日嚣尘上,一些人拿党派僵局作为美国衰落的证据。但情况真的这么糟糕吗?
根据政治学家萨拉·宾德(Sarah Binder)的看法,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两大政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从未向现在那么大。但是,尽管面临着僵局,但第111届国会仍通过了大型财政刺激、医疗改革、金融监管、一项武器控制条约以及军队同性恋政策修改。显然,美国政治制度不会衰亡(特别是在党派僵局具有周期性特征的情况下)。
尽管如此,今天的国会仍饱受立法能力不足的困扰。尽管意识形态一致性在过去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倍,从占公众的10%升高到21%,但大部分美国人并非一边倒的保守派或自由派,他们希望他们的代表保守和自由兼而有之。但是,政党的意识形态一致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增长。
这并不是美国的新问题,美国宪法的基础是十八世纪自由观——控制权力最好的办法是分散化和对抗性制衡,迫使总统和国会为控制外交政策等领域而斗争。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是以低效为目的设计的,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轻易威胁公民的自由。
这一低效率或许是对美国制度信心下降的原因。如今,不到五分之一的公众相信联邦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做着正确的事,而1964年的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三。当然,这些数字偶尔会在某个时期出现飙升,比如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就是如此;但总体而言下降趋势相当明显。
联邦政府在这方面不是孤家寡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对许多高影响力机构的公众信心出现了暴降。从1964年到1997年,信任大学的美国人比例从61%降低到30%,而信任大公司的美国人比例从55%减少到21%。信任医疗机构者从73%下降到29%,信任新闻者从29%下降到14%。在过去十年中,对教育机构和军队的信心有所恢复,但对华尔街和大公司的信任仍在继续下降。
但这些表面上引人警觉的数字可能具有误导性。事实上,82%的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适合生活的地方,90%的美国人喜欢政府的民主制度。美国人或许对他们的领导人不是完全满意,但这个国家显然没有走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革命的边缘。
此外,尽管党派政治在近几十年来日益极化,但此趋势的起点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当时,从大萧条中走出并在二战中获胜使得美国人对美国制度的信心空前高涨。事实上,对政府的公共信任的最剧烈降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此外,对政府的信任的下降并未伴随着公民行为的重大变化。比如,美国国税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是公众熊欣欣最低的政府机构之一;但偷漏税情况并没有出现剧烈增加。从控制腐败的角度看,美国仍比九成的国家强。而尽管二十世纪下半叶总统选举投票率从62%下降到50%,但在2000年实现了企稳,并于2012年回升至58%。
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下降也许植根于人们对个人主义的态度的更深层次的变化。对个人主义的态度的变化导致了对权威的顺从程度有所下降。事实上,类似的过程是大部分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拜美国的分散化联邦制所赐,这一社会变迁可能不会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影响美国制度的效率。事实上,华盛顿的僵局通常伴随着州和市政层面的政治合作和创新,让公民对州和地方政府——以及许多政府机构——刮目相看,给出远高于联邦政府的评价。
这一治国之道对美国人民的心态具有深远影响。一份2002年的研究指出,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与社区息息相关,并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属于优良之列,近一半的成年人参与公民团体或活动。
对美国来说,这是好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领导人可以继续无视美国政治制度的短处,如众议院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而出现的“稳得议席”以及参议院臃肿碍事的流程。这些形成僵局的原因是否能克服还有待观察。此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因为主要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
但是,如保守派作家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所指出的,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经历了犯罪率、交通事故数、酒精和烟草消费以及二氧化硫和一氧化氮(它们会造成酸雨)排放的快速下降——还引领了一场互联网革命。基于此,将美国与(比如)罗马帝国的衰亡相提并论完全是无稽之谈。